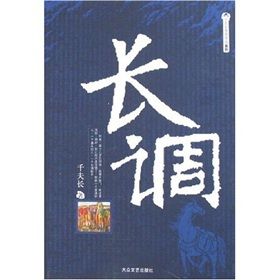作者簡介
千夫長,屬虎,獅子座,蒙古人。1962年7月28日出生於內蒙古科爾沁草原。出版著作:專欄作品集《野腔野調》、長篇小說《紅馬》、《中年英雄》、中國首部手機簡訊小說《城外》。廣東文學院簽約作家,新作定為深圳市重點文學創作項目。現居深圳。目錄
第一部旗鎮第二部牧場
第三部阿茹
精彩書摘
第一部:旗鎮第一節
天還是黑的,阿媽就喊醒了我。阿媽起得更早,她已為我煮熟了滾燙的羊雜湯。我喝了一身熱汗,熱呼呼地就出了家門。阿媽為我找好進旗鎮的馬車,已等候在院子的大門外。趕車人在門口走來走去,把馬鞭子甩得啪啪作響,醉意十足。每匹馬的籠頭上,都佩戴著九隻黃銅鑄的虎頭鈴鐺。每隻金黃的虎頭銅鈴鐺,都張嘴含著硃砂色的鐵珠,晃動起來清脆悠揚,氣勢威猛。四匹馬個個精神抖擻,駕轅的紅馬和左套的青花馬,比賽似地各自翹起尾巴,屙出了一堆糞便。大便的同時,馬兒也開始撒尿。紅馬是騸過的騍馬,一時,在滾圓的屁股上,瀑布般地屎尿俱下,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青花馬是公馬,撒尿就像肚子底下,吊起了一隻黑色的粗水管子在噴水,稀里嘩啦,煞是壯觀。看來它們確實是吃飽了夜草。
家裡的狗也都被驚動起來,叫了一陣,在阿媽的勸阻下,好像搞明白了來者的用意,也就不吭聲了,但還是警惕地守候在大門口。
我背著阿媽為我準備帶的東西,裝了半個麻袋,用牛皮繩捆得緊緊的。阿媽和懷孕的黃母狗跟在後面送我。
我走出家門,感覺到好多眼睛都在看我,有些不知所措。狗的眼睛在看我,馬的眼睛在看我,圈裡的牛羊在看我,趕車人也在看我,天上的星星也睜著睏乏了一夜的眼睛,在惺忪地看我。還有朦朧的早晨,空氣中各種眼睛似隱似現,都在看我,羊圈、牛圈,家中大小房屋的門窗,也好像在睜開眼睛看我。就連腳下的土地凍成的一條條裂縫,都像脒著的傲慢的眼睛。我有些膽怯地和這些眼睛們打著招呼,驚恐地看著這些眼睛,也盡力地迴避著這些眼睛。我覺得渾身不自在,就低下頭,看由熱轉冷,正在凝結成凍的馬的糞尿。
我感覺垂在褲兜邊的手,被一個柔軟的東西熱乎乎地舔了一下,低頭,發現是老得掉了毛的老黑狗雙喜也起來了。老雙喜很憂傷,沉悶不語,步履蹣跚。它昏花的目光很慈祥,是唯一讓我感到心安的眼神。雙喜已經太老了,它的年齡比我大,是阿爸還俗從查乾廟裡帶回來的伴侶。我阿爸是查乾廟還俗的五世尼瑪活佛,他兩歲半坐床成為活佛,在十三歲的時候還俗回家。十四歲娶了我十八歲的阿媽,十五歲時,我出生,他就離開家去了旗鎮的歌舞團,就是原來的查乾廟,當長調歌手。阿爸多年不回家,一直到今年,我已經長到了十三歲,阿媽讓我今天早晨上路,去旗鎮尋找阿爸。
狗的年齡真是不可思議,據阿媽說雙喜只比我大兩歲,我剛是翩翩少年,它就已經老態龍鍾了。雙喜本來是純黑色的牧羊犬,現在身上很多地方的毛已經脫落,露出的皮膚粗燥不堪,像曬乾的老榆樹皮。有毛的地方,黑毛也已老成了灰毛和白毛。
據說它叫雙喜這個名字,還是阿爸還俗回來之後才取的。政府說尼瑪活佛還俗,成為社會主義新公民是一喜,和阿媽結婚是二喜,一共雙喜臨門。我阿爸說,那為了紀念就給這條叫馬弁的黑狗改名叫雙喜吧。雙喜早年為我們家牧羊護院,曾經立下過汗馬功勞,它老了,已經兩年不管家事,平時這個時辰趴在狗窩,兔子跑到嘴邊它都懶得去理。我們家照樣養護它,從來沒把它當狗,像老爺子一樣照顧。雙喜今早卻起來送我,怪不得阿媽說它最通人性。我感到很有面子,馬上就覺得自己來了精神。
黃狗的乳房已經一隻一隻脹了起來,連綿起伏,一共九隻,按照常識這窩應該出生九隻狗崽。黃狗體質很強壯,這是第一胎,我想小狗出生一定會有充足的奶水。我蹲下摸它飽滿的乳房,它的目光還很羞澀,不好意思地把頭扭過一邊,然後乳房朝天趴在了地上,很溫柔的樣子。我感覺黃狗肚子裡有十八隻迷朦的眼睛,在幼稚地看著我。我就沒了興致,搬著黃狗的腰,讓它站了起來。
阿媽顯得很莊重,她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穿了一套洗得乾乾淨淨的衣服來送我,腳上還穿了一雙很少上腳的新鞋,好像要出遠門的是她。我感覺讓我去見阿爸,是替阿媽去向阿爸遞交一份關於我長大成人的答卷。阿媽的目光,戀戀不捨地在我身上掃來掃去,我看她時,她又會把目光從我的身上移開,假裝在看套在車上的紅馬。
趕車人,是我們花燈牧場牧業隊的馬車隊長色音巴雅爾,牧民們都叫他色隊長。阿媽請求色隊長一定要把我送到旗鎮歌舞團,不要丟在半路,給凍死或者讓狼吃掉。我的孩子沒有出過遠門,她不放心地對色隊長說。回頭又囑咐我不要在車上凍壞了腳,路上要下車去勤跑一跑。阿媽把我頭上戴的狐狸皮帽子,身上穿的羊皮襖又都繫緊了一遍。要勒緊一點,別讓冷風進去。阿媽說著又拉過我的手,你的手是熱的,放在兜里暖著,手涼人就冷了。阿媽的手很涼,我心裡就有些難過,我沒有離開過家,也沒離開過阿媽。要進旗鎮去找阿爸,我很興奮,也很猶豫。旗鎮和阿爸對我都是陌生的,就像牛羊沒去過吃過草的草原,有些膽怯。剛才摸到阿媽冰涼的手,難道阿媽的心是冷的嗎?我從來在阿媽的臉上看不明白喜怒,也不懂她內心的哀愁。她太平靜了,我和阿媽的生活,可以說沒有什么波瀾。
色隊長把扎著漂亮紅纓的馬鞭子,插到車轅子的黑鐵鞭座上,榆木鞭乾和狗皮鞭子上的紅纓,迎風飄揚。紅纓是用白馬的馬鬃染成鮮紅,很好看。他眯著醉眼,漲紅臉膛,滿嘴酒氣拍著車上拉的羊皮說:這是一百多張羊皮,比家裡的被窩都暖合,你就放心吧,我的佛娘。色隊長是一個脾氣暴躁,沒有耐心的人,但是對我阿媽還是很尊敬。其實全牧村的人對我阿媽都很尊敬,都叫她佛娘。他回頭見我還站在地上,和阿媽戀戀不捨的樣子,就睜開眼睛喊:小子,快上車呀,你不想去了嗎?
我蹲下身子,親熱地抱了一下雙喜,它那淌著涎水的老嘴,又伸出柔軟、熱乎乎的舌頭,很慈祥地親兩下我的手,把我的手弄得粘糊糊的。我戀戀不捨地站起來,黃母狗也要跑過來親我,被阿媽攔住了。我從左側向馬車走去,路過青花馬的身邊,它很不友好地用後蹄刨了一下地,好像是對我的恐嚇。這是馬的一貫伎倆,見到陌生人都想殺殺人的威風,結果都是人把馬馴服。我走進了青花馬的眼睛裡,馬眼看人低,馬眼裡,我看見我的臉膛和身體顯得很矮小,也很醜陋變形。青花馬蔑視地昂揚起頭,閉了一下眼睛,我感覺被擠得全身骨頭都痛。
我上了車,色隊長在羊皮垛中間,給我留出了一個位置,搭了一個窩,坐進去四面都是粗麻繩勒緊的羊皮。又安全、又暖和,凍不著了,我滿意地對阿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