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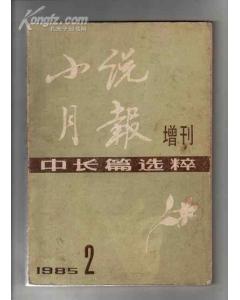 《凝眸》發表刊物
《凝眸》發表刊物中篇《凝眸》,小說在敘事外形上有著嚴密的對稱結構,一切場所、景物、人物與事件都被工整地一分為二:兩座緊挨著的小島,我方占據著鯊尾嶼,敵方占據著鯊頭嶼;鯊頭嶼成為我方的偵察對象,鯊尾嶼成為敵方的偵察對象;這一天,“我”到了鯊尾嶼,而“三十三號”上了鯊頭嶼……小說中的這些對稱,既製造著森然的對立,又暗中滋長出對應——每日每夜雙方都緊張地對峙著,又通過觀察鏡相互觀察、猜測、試圖進入對方的內心世界。
作者簡介
 朱蘇進
朱蘇進朱蘇進,1953年7月出生於南京某部隊一軍醫之家。1959年隨家遷在福州入學,讀至國小五年級,因病停學數年。病癒後適逢“文化大革命”開始,無法再正常學習,便從許多待焚的書籍中挑來一些閱讀,從此開始熱愛文學。父親是一位醫生,受其影響,也深深憎惡折磨人類的一切病痛。1969年10月參軍,曾有志學醫,不成,被分配到廈門某部當一名炮手,歷任瞄準手、計算員、偵察班副班長、班長、排長、代理副指導員等職。1971年在軍區報紙上發表處女作《第一課》,從此開始業餘文學創作,後又連續發表了一些小說和散文。1976年調入福州軍區政治部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1978年與魯延合作出版了長篇小說《懲罰》。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福建分會,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5年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江蘇省分會常務理事。1985年調入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現任創作室主事。主要作品有:《在一個夏令營里》(長篇小說,曾獲全國“少兒讀物優秀作品”獎)、《射天狼》(中篇小說,曾獲全國第二屆[1981—198]優秀中篇小說獎)、《引而不發》(中篇小說)、《凝眸》(中篇小說,曾獲全國第三屆[1983—1984]優秀中篇小說獎)、《戰後就結婚》(中篇小說)、《第三隻眼》(中篇小說)、《炮群》(長篇小說)等。
評價
“寫軍人難,寫軍營里的當代軍人尤難。”有評論曾經指出:《射天狼》、《引而不發》到《凝眸》,是朱蘇進創作上騰躍的三級跳,這也許是對的,在《凝眸》中,作者對軍營生活的觀察更加細緻入微,視野也更加開闊。他已不單靠眼睛,而且“動員起眼、耳、鼻、舌、腦等合副的藝術感官,去感受、體驗、分析、研究。
小說中關於古沉星上海島到參加觀察值班的大量細節描寫,便可當做這種“五官開放”式的藝術感受的實例來讀。那些沒有知覺、沒有生命的石頭、海風、浪涌、海對面的島嶼、觀察器材等等,在一個感覺銳敏、思想開放的偵察兵的主觀印象中,全都變‘活’了,流瀉著靈氣。敵我鬥爭的法則,像一柄劍把相互仇視的島嶼各分成兩半:正面與背面。
雙方都把島子的正面收拾得很莊嚴,一切不便見人的東西,都擱在島子後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僅僅能用四十倍觀察鏡去辨清島子正面的表面現象還不算什麼大能耐,更必須能從霧中傳來的一聲爆炸、海里落下的一隻球、受到責罰的士兵的時隱時現中尋蹤察跡看出彼岸軍人們在島子背後的許多活動,破譯出他們深藏內心的種種密碼信息,連綴起被撕碎的歷史碎片,方見出與精到的觀察相聯繫的分析、研究、思考和判斷的真功夫。正是藉助於這樣的功夫,作家方有這樣的慧眼:能從軍營一隅看到大千世界的種種人情世態,從暴露在生活表層的看得見的事實裡面探測出隱藏在‘事實背後的事實’,從別人認為平淡無奇的地方發掘出無窮的奧秘。”
戲劇性
 朱蘇進
朱蘇進在這篇小說里,新與舊的鬥爭在古沉星的同輩軍人及父子兩代軍人之間以一種更富戲劇性的樣式表現出來。古樸將軍同國民黨的那個綴滿勳章的老上尉,他們分別是兩個對峙海島的一長段歷史的象徵和代表,時代的潮流在沖刷和叩擊著兩個對峙的島嶼,而盤桓於當代軍人腦中的傳統觀念卻不會輕易消逝……而視野開闊、感覺銳敏、思想解放的古沉星則不然,一切他都自己看自己思索,所以他能得到比較客觀的判斷,敢於說出要呼喚台灣歸來的心聲。這可以說是從橫向的比較來寫我們的新人。與此交叉的,是古樸——古沉星父子和上尉—— 三十三號父子的意味深長的縱向對比。“在這一比較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對敵方描寫的真實。”不因描寫的對象是敵方的軍人,便恣意塗黑、醜化,這也是朱蘇進的性格描寫能達到傾向性與真實性相統一的基本點。
無論從哪方面看,上尉都是一個效忠台灣當局井立有汗馬功勞的角色,對於軍人一點‘微笑’的表示,也逆潮流地斷然回絕。但是作者仍如實地寫出這個瘦小的老軍人身上的許多為一般人所料不到的勁道,他有堅持他的政治立場的堅定性,有履行軍人職責的頑強精神,對唯一的親兒子也不講任何寬容。他最後倚醉鞭打自己的勳章,是否意味著否定自己既往的一切也很難說。變是要變的,時代潮流在變,他的兒子已經變了,他的兒子不過是在集郵冊上收集有幾張違禁品,而老上尉的軍閥式的威壓竟直逼得兒子踢雷自盡。這場父子衝突的客觀描述,準確地傳遞出國民黨軍人內部新舊鬥爭的社會信息,對幫助讀者瞭望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前途和趨勢,無疑也是很有幫助的。
意義
從整部小說來看,“對應”努力嘗試擺脫製造著間距、隔閡的“對立”,具體地說,就是擺脫父輩們留下的歷史仇恨,擺脫“我”與“三十三號”這一代人自幼接受的意識形態教育以及長期對峙中產生的相互廝殺的衝動。而最終將小說意蘊推向頂峰的,正是心靈互感的對應,小說最後“我”為敵軍戰士“三十三號”的死亡降旗誌哀,這是人性自身向反人性的戰爭及其造成的隔膜的抗議。
作為軍人,假如沒有戰爭和敵人似乎就喪失了主要價值;同樣,傳統的軍事文學一般也用二元對立的衝突方式來推動情節發展。《凝眸》從“四面布滿威脅”的兩軍對壘中拉開序幕,最終卻完成了從對峙到凝眸的跨越與升華。這一升華,不僅僅褪盡軍事和意識形態衝突,甚至不僅僅是在海峽兩岸父輩的仇恨之後閃現出和解的希望之光,更是在更高層次上追求人類的溝通、理解,以及生命形態的圓融和諧。這樣的小說可以撐破上文提到的作家對天才與碌碌世人之間關係的畫地為牢般的界說。
還可以提到的是,因為人類彼此的“凝眸”這一情景中濃縮著豐富的意味,它自身構成了悠久的文學表現傳統。遠的不說,就以卞之琳耳熟能詳的《斷章》為例,這首詩中的“凝眸”意象、情境可以簡化為?押人你風景,明月你人。“你”站在橋上看風景,“你”是主體,風景是被看的客體,同時在樓上人的注目下,“看風景人”成為主體,“你”成了作為客體的風景之一。第二節同然,“你”是畫中主體,明月作為裝飾物是服務於“你”的客體,然而“你”又進入“別人”的夢,做著夢的“別人”是主體,“你”是夢中裝飾,變成客體。這裡主語/賓語、主體/客體的互換,在藝術形式上構造出不斷破除定位視點、自由流動的審美空間;在主題意蘊上更是抒發著萬物相對又互為關聯的哲理。《斷章》寫於1930年代中期,越是在風雨如晦的現實中,越是在人們被人為的對峙、隔閡所切割的非凡境遇中,就越能傾聽到“表現相對相親、相通相應”的詩。朱蘇進的《凝眸》正可歸入這一類結構精巧而意境深遠的文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