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阿袁 ,原名陳忠遠,溫州永嘉人;中國當代著名青年學者,格律詩人,文學家,書畫家,魯迅學家,百度百科學術委員會成員 。阿袁生於浙江永嘉,曾先後出任溫州市主流媒體暨北京國家級媒體記者、編輯,北京國家級出版社編、國學部主任以及北京一國家級畫報總編輯,兼任特聘教授等。他著有《又新集》、《詩詞正韻》、《唐詩故事》、《宋詞故事》、《魯迅詩編年箋證》和《魯迅先生的心裡話》等20餘部,約1000餘萬字。
辛卯春間,阿袁《魯迅詩編年箋證》一書研討會由人民出版社、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中國人民大學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共同召開,其專精的學術成就受到了有識之專家的一致讚嘆。據了解,該書發現並糾正了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版《魯迅全集》和“魯研界”歷來研究中的大量訛誤,被稱為是魯迅詩研究的集大成者 。
此外,在學術研究過程中,阿袁(即陳忠遠)先生還發現並糾正了《辭源》、《辭海》、《文選》、《全唐詩》、《全宋詩》、《康熙字典》、《幼學瓊林》、《詩韻合璧》、《淵鑒類函》、《四庫全書》(其中一部分)以及多種版本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等權威書籍中為數眾多的錯訛。與此同時,阿袁的學術經歷被多種大型辭書或名典收錄。
人物簡介
阿袁,原名陳忠遠,字定之,號藥愚居士,筆名阿袁、中元等;溫州永嘉人;中國當代著名青年學者,格律詩人,文學家,書畫家, 魯迅學家。阿袁曾先後出任溫州市主流媒體暨北京國家級媒體記者、編輯,北京國家級出版社編輯、國學部主任以及北京一國家級畫報總編輯,兼任特聘教授等。近年來,他多以“阿袁”為名發文和出書。就在在校求學時,陳忠遠(即阿袁)便已加入了全國性的詩詞組織中華詩詞學會,並深受著名詩人霍松林、袁第銳、林從龍等前輩詩人的大力稱賞。此後,他在就讀大學期間,還拜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詩詞組組長孔凡章先生為師,其詩詞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其間所結集的詩詞曲輯錄《又新集》就是大為海內詩人詞家讚賞不已,從而紛紛飛書染翰為之評點的。
著述名錄
 阿袁(即陳忠遠)《唐詩故事》
阿袁(即陳忠遠)《唐詩故事》阿袁目前撰著有《唐詩故事》、《宋詞故事》、《唐代名流詩文公案直判》、《唐詩三百首本事》、《宋詞三百首本事》、《又新集》、《名家評點<又新集>三百首》、《詩祖陳子昂與女皇武則天》、《魯迅詩編年箋證》、《魯迅先生的心裡話》、《裸眼》、《詩詞正韻》、《藥愚對韻》、《五斗門人詩話》、《魯迅獨具隻眼看帝王》等二十餘部作品,約1000餘萬字。最近,阿袁(即陳忠遠)先生還首次從“編注”的角度對古籍進行了他本源於明代文化大家馮夢龍先生的經學專著《四書指月》而纂成的全新兩書《論語指月》與《孟子指月》(為“馮夢龍經學選集”中的兩種) ,則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研究方向
 阿袁(即陳忠遠)《宋詞故事》
阿袁(即陳忠遠)《宋詞故事》阿袁目前所著這些書的內容主要涉及唐詩、宋詞、唐史、魯迅學和長篇章回體小說、報告文學等多個領域;阿袁既做研究,亦搞創作,其成果頗豐。在各個領域裡,阿袁取得了以往學者所未能取得的成果。如在對唐詩宋詞的研究,注重其可讀性、趣味性、知識性、學術性和生活性的有機結合,從而在同類書中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確實不同凡響。而今年春間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舉行的《魯迅詩編年箋證》(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研討會,該書以其廣博的知識容量和精準的學術斷語贏得了與會的“魯學”專家的讚揚。因為書中不但糾正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最新版本《魯迅全集》注釋中的大量錯誤,而且也糾正了為數不少的魯迅自身的筆誤但卻從未得到有效糾正者。此外,阿袁在書法藝術方面也有其獨到的見解。以上諸書,大多由人民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九州出版社等出版發行。
社會評價
關於阿袁目前已由人民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等出版發行的《唐詩故事》、《宋詞故事》、《魯迅詩編年箋證》、《魯迅先生的心裡話》等書,阿袁由於詩學功力紮實,而其書尤可稱娓娓可讀,是目前所見的《唐詩故事》《宋詞故事》同類書中是能夠把學術性、可讀性、知識性、趣味性和生活性結合得最好的唐詩宋詞故事類普及讀物。其中,著名學者和作家李國文即以為《唐詩故事》是一本“這固然是需要學識和見解的書,也是一部見思想、見性情的書”。這《唐詩故事》、《宋詞故事》二書,還在當時網路“詩歌散文排行榜”上分別榮膺其中的第四名和第七名。按,其中前三名依次為《余秋雨人生哲言》、《朱自清散文》、《李敖語錄》;又,在同批次的排行中,《魯迅雜文精編》第六,《魯迅小說全編》第八,《魯迅散文全編》第九;此外前十名中,其他人皆僅以一書入選。對此,《人民日報(海外版)》、《溫州都市報》等報刊均曾以專版的形式予以報導,其中有標題稱作者阿袁是“活在當代的‘古人’”等。新華社資深學者和詩人蘇仲湘研究員也認為阿袁的《唐詩故事》《宋詞故事》資料豐富,寫法新穎和考證詳實,是近年來僅見的唐詩研究碩果,非常值得推廣。
而關於《魯迅詩編年箋證》等書,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教授就在他所寫的序言中認為自己“偶然認識阿袁先生,知道他是舊詩的專家,也是舊體詩的寫作者。他的詩有古風,很有舊文氣。讀過他關於古代詩歌研究的文章,有著綿綿的情思在。這樣的文字我自己是寫不來的。近來才曉得他還是魯迅詩歌的研究者,對此傾注了許多心血。看到他研究魯迅詩文的書稿,知道下了很大功夫。詩無達詁,每個人對此都有不同的心解。阿袁潛心在對象世界裡,走在他自己喜歡的路上。我相信會有許多人會漸漸關注到他。”文後還論斷:“阿袁注重考釋,喜歡探究原委,又能蒐集後人成果,把相關的資料集結起來,對比中也能看出作者的異同。他自己的看法也埋在其間,發現了許多問題。提出別樣的觀點,供世人一閱。注釋魯迅的詩,不僅涉及本事與內意,還有人際關係網路圖,以及與時代之關係。歷史留下的資料,有的未必準確,有的含混不清,所以讀解之中,辨析與發現,都很重要。這一本書,提供了多樣的視角,前人與今人的觀點擷英於此,互為參照。”(見孫郁《解詩與注詩——阿袁作《魯迅詩編年箋證》序》)
至於江西省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員熊盛元則對於阿袁的新著《魯迅詩編年箋證》,在其所寫的序言中聲稱:“余初讀一過,覺博雅可方李善之注《文選》,任淵之注《山谷》,迅翁詩中之典故來歷,皆沿波討源,一一指出,較我最喜之倪氏《探解》,更為詳盡而精準。不惟此也,阿袁於迅翁詩之體式與音韻,亦獨具隻眼,如《題〈吶喊〉》‘弄文罹文網,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諸家皆僅注辭句,而阿袁則加按語曰:‘此為五言古絕,而非正格之近體五絕也。一二句對起,蓋所謂“掉字對”也。”雖只寥寥數語,而慧心畢見。又如《庚子送灶即事》‘只雞膠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無長物,豈獨少黃羊’,阿袁解析曰:‘魯迅此詩為標準之近體“五絕”,但某些喜寫近體詩者將感不解,除上述箋釋“膠牙餳”之“膠”可讀仄聲外,對首句第二字“雞”為平聲而乖違格律疑兀不已;其實,此為古人寫詩時之一種約定俗成作法,亦即所謂“專有名詞可不計平仄”是也。夫如是,全詩則完全合乎格律矣;又,第二句屬“句中自調平仄以諧律”格,故周作人日記稱“大哥作一絕”,所言良確,亦即此為一首近體五絕,而非五言古絕也。’非精於詩道者,焉能如此切中肯綮耶?尤令人稱道者,《題三義塔》一詩,各本首句均作‘奔霆飛熛’,阿袁據迅翁1933年6月21日之日記,斷定‘熛’當作‘焰’,蓋‘熛’讀‘補遙切’,平聲,古人從無讀仄聲者,即此可知其治學之審慎嚴謹矣。抑更有言者,迅翁之詩,遠承楚騷之餘緒,近嗣定庵之風神,而又獨具自家之面目,蓋其不惟源溯前古,且能睇眄西方,創摩羅詩力之說,擎反抗挑戰之旗,直面人生,紮根荒漠,橫戈吶喊,荷戟彷徨,是以其詩雖不若散原、弢庵等深晦,而所詣之境,則超軼傳統之外。如此篇什,倘僅用李善、任淵箋注之法,恐難得其真髓也。是以阿袁之《箋證》,於每首詩後,均蒐集魯迅及其親友相關之語,以內證、旁證之法,由表及里,剝繭抽絲,揭示背景,探取詩心,直欲與迅翁相視一笑,莫逆於心矣!”(見熊盛元《魯迅詩編年箋證序》 )
 孫郁院長向與會學者介紹阿袁魯迅詩箋證歷程
孫郁院長向與會學者介紹阿袁魯迅詩箋證歷程此外,2011年春,由人民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和北京魯迅博物館三家聯合舉辦的《魯迅詩編年箋證》研討會在中國人大召開,著者專精深厚的詩學素養和嚴謹客觀的考據工夫獲得了與會專家的一致稱讚。
工夫紮實
由人民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魯迅博物館共同舉辦的《魯迅詩編年箋證》首發式暨研討會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有專家認為,《魯迅詩編年箋證》在魯迅詩歌的研究領域創辟出一個令人讚賞的境界,與會學者對於該書箋證者阿袁所下的工夫均表示讚許。
關於魯迅詩歌,80餘年來,國內外曾先後出版過為數不少的各種形式的註解或賞析著述,但由於各種原因,存在不少文字資料的錯訛顢頇及對詩意理解的紛亂乖謬。據悉,《魯迅詩編年箋證》(人民出版社)是目前收詩最齊全,箋證最詳確,同時也應是最為可靠的魯迅詩歌讀本。該書以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的《魯迅散文詩歌全編》中的“詩歌全編”為箋證底本,阿袁以其深厚的詩學功力,斷定並刪削了其中並非屬於“詩”者,從相關書籍中增列詩歌予以說明並箋證之。他還糾正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最新版本《魯迅全集》中對魯迅詩注釋的錯誤,如事實認知之誤,典故引用之誤,作品系年之誤,文本出處之誤,書名引署之誤。
阿袁堅持認為,“只要真正明白魯迅先生詩中語詞的淵源所自,同時也了解了作者寫詩時的心境、生活狀況以及歷史背景,就可以得出比較肯定的結論。”為《魯迅詩編年箋證》作序的原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先生稱,《箋證》確實是魯迅詩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謂名實攸歸。
集唐詩聯
唐詩是我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公認的瑰寶,其語句的優美和意境的圓融,歷來使得眾多文人學士為之傾倒不已。而像大詩人王安石、蘇軾等人卻居然用唐詩成句集成對聯甚乃詩詞的,其優美或深刻的程度往往有出人意表之致。而這,毋庸置疑就更使人為之拍案稱其稱奇叫好了。其實,當代著名青年詩人、學者、文學家和魯迅學家阿袁(亦即陳忠遠)先生,固然亦雅擅此道。他不但拿唐詩來作對,而且還以之入詩,寫出了別樣的境界,令人激賞和嘆佩不置。這裡,筆者試擷取一二,以供讀者欣賞與玩味。
例一:
 阿袁《魯迅詩編年箋證》(人民出版社版)
阿袁《魯迅詩編年箋證》(人民出版社版)(出句) 家醞滿瓶書滿架(唐人白居易《香山寺》);
(對句一)山花如繡草如茵(唐人許渾《寄桐江隱者》)。
兩者不但對仗工穩(使用的是當句對和掉字對的寫作技巧),音律諧美,而且意境幽深,辭藻淳美,令人嘆服。
不僅如此,阿袁還拿唐人崔櫓《華清宮二首》中的句子來對其出句,道是:
(對句二)濕雲如夢雨如塵。
這一樣可見出集聯者阿袁先生敏捷的才思和廣博的唐詩學功力。此外,詩思縱橫捭闔的他居然還拿唐人熊孺登《湘江夜泛》中的佳句來對白居易的出句,同樣也令人嘆為觀止的;道是:
(對句三)江流如箭月如弓。
不難看出,以上的出句僅是一句唐詩,而阿袁先生一忽兒便對以三句不同唐人的詩句,而且各擅勝場,難分軒輊,不能不嘆服其實在精熟於唐詩而能運用自如者也。
例二:
其實,陳忠遠先生在中學時期便已集唐詩成多首全新的七律,其中的對偶句(亦即頷聯和頸聯)就極為工穩而令人再三稱嘆不置,一如當年孔子轉述季札的話時所說的那樣——“觀止矣,若有他樂,我不敢請已”(具見《左傳》)了的!其所集唐詩中就有中間兩聯,亦即該七律之頷聯與頸聯云:
幽淚欲乾殘菊露(李商隱),亂流長響石樓風(武元衡)。
恩勞未盡情先盡(張祜),琴曲雖同調不同(白居易)。
如果說,集唐成聯尚且不為至難的話,那么,我們從他集唐人詩句為七律的手段,不能不驚服其淵博的學識和敏捷的思維及深厚的遣詞造句之功夫了。我們熱望阿袁先生能夠多多集出些精品,以繁榮目前日漸衰頹的詩壇,是則為我國詩壇的盛事乃至至幸了!
集秦觀詞
很多人知道詩人陳忠遠(即阿袁)先生善於集唐詩成詩聯,其實,曾一同撰寫出版《唐詩故事》《宋詞故事》(均為九州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陳先生,他固然也是深擅宋詞的,只不過是他為人極不張揚,以致很少在一些場合表現而不大使人知道罷了。要知道,集詞成詞比集詩成詩的難度不知更要難上幾倍的。因為他不但需要對詞牌的熟練程度,而且對所及宋詞的諳熟,以及對語言藝術的深切把握。許多業內專家誦讀陳先生的集詞成詞後,都不由得感嘆:觀止矣,要知道,這可是要比原作還更具韻味的啊!為了讀者能夠真切地領悟和欣賞,現在,筆者特將所能收集到的陳忠遠先生關於宋代大詞人秦觀的集詞成詞的佳作作一集納,使讀者能在其別開生面的優美詞境中得以薰陶和淨化。
虞美人·感舊集秦淮海句
碧紗影弄東風曉(虞美人影·碧紗),寶篆沉煙裊(海棠春)。畫橋南北翠煙中(望海潮·廣陵懷古),紫府碧云為路(一落索)、碧雲重(江城子·南來)。 醉鞭拂面歸來晚(夢揚州),秪恨離人遠(虞美人·高城)。誰將彩筆弄雌雄(憶秦娥·楚颱風並詩),春入柳條將半(憶仙姿·樓外)、倚東風(行香子)。
前調
 孫郁院長向參會學者介紹阿袁魯迅詩箋證歷程
孫郁院長向參會學者介紹阿袁魯迅詩箋證歷程秋光老盡芙蓉院(玉樓春),花影和簾卷(生查子)。月高風定露華清(臨江仙),多少蓬萊舊事(滿庭芳·山抹)、正銷凝(八六子)。 醉鞭拂面歸來晚(夢揚州),煙水秋平岸(虞美人·行行)。韶華不為少年留(江城子·西城),又是一鉤新月(南歌子·香墨)、送歸舟(虞美人·高城)。
前調
流鶯窗外啼聲巧(海棠春),妝點知多少(虞美人影· 碧紗)。南來飛燕北歸鴻(江城子· 南來),豆蔻梢頭舊恨(滿庭芳· 曉色)、恨無窮(阮郎歸· 宮腰)。 慿君礙斷春歸路(蝶戀花),不見聯驂處(虞美人· 高城)。薴蘿煙冷起閒愁(望海潮· 越州懷古),天外一鉤殘月(南歌子· 玉漏)、幾時休(江城子· 西城)。
鷓鴣天·集秦少游句題舊日黎君見贈寫真
誰記當年翠黛顰(南鄉子),揉藍衫子杏黃裙(南歌子· 香墨)。夜來酒醒清無夢(採桑子),雨打梨花深閉門(鷓鴣天)。 人不見(江城子/千秋歲),雁先聞(木蘭花慢)。亂山何處鎖行雲(南歌子)。謝郎巧思詩裁剪(調笑令),水剪雙眸點絳唇(南鄉子)。
添字採桑子·憶昔集秦淮海句
高城望斷塵如霧(虞美人· 高城),霧失樓台(踏莎行)。霧失樓台(踏莎行),煙水茫茫(點絳唇),白露點蒼苔(滿庭芳· 碧水)。 金鳳簌簌驚黃葉(菩薩蠻),曉色雲開(滿庭芳· 曉色)。曉色雲開(滿庭芳· 曉色),山抹微雲(滿庭芳· 山抹),疑是故人來(滿庭芳· 碧水)。
虞美人·續集秦淮海句 佳人別後音塵悄(採桑子),寶篆沉煙裊(海棠春)。無端銀燭隕春風(阮郎歸· 宮腰),遙夜月明如水(憶仙姿· 遙夜)、不言中(江城子· 南來)。 亂花叢裏曾攜手(鼓笛慢),行待痴心守(滿園花)。淡煙流水畫屏幽(浣溪沙· 漠漠),爭奈無情江水(虞美人· 高城)、水空流(虞美人· 西城)。
經學成就
緣起·挖掘視角獨特的經學選題
在如今人們的印象中,四書五經所呈現的聖賢形象跟我們似乎有些距離。但我們一旦真正深入進去,跟古聖古賢們做一番親切的晤談,則不難發現,古聖古賢距離我們其實並不遙遠。明代通俗文化大家馮夢龍以其特有的經學素養為我們親切講解,使我們可以更加從容地觀照古聖古賢們的為人處事,以及他們給我們現如今的教育意義和親炙涵容力。
然而,現在人們知道馮夢龍先生的大名,似乎大多由於看過所謂“三言兩拍”的緣故;其實,這“兩拍”的著作權卻是另有所屬的。而馮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學的成就殊顯突出之外,比如經學,比如史學,比如筆記雜綴等等,固然也不可等閒視之。而經學方面的著作,則委實是馮氏畢生孜孜矻矻地從事乃至殫精竭慮撰成的;對此,馮氏自己似也頗為欣賞其勝義。另一方面,馮氏這些經學著作,也為他贏得不菲的社會影響和一定的經濟收入;因為根據有關書籍記載,馮氏這些經學著述在當時的讀者群尤其眾多科舉生員中是成了“暢銷書”的。
據資料所考,馮氏留存至今的有關經學方面的著作,大抵還有《四書指月》《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等,共約二三百萬言;這真可謂犖犖大端了。但由於各種原因,跟馮氏諸如《智囊》《情史》等著名手筆相比,他這些頗費精力撰著的經學著作竟不大為人所知。去年年底,我跟出版社領導談起馮夢龍著作的開發情況,如《智囊》《情史》《東周列國志》等較為通俗的讀物,各大出版社都爭相去做;而我們則決定邀請有關這方面的專家學者從事點校、編注等工作。但頗為遺憾的,許多學者要么所涉領域並非經學,要么對宋明時期的經學情況不大了解,要不就是時間太緊張,所以應者寥寥。於是乎,除馮氏《春秋衡庫》已得一教授等允諾點校外,我便只得自行點校與編著《論語指月》《孟子指月》(因《四書指月》中並不具備《論語》《孟子》原文等事由)了。而這,對經學領域原本也鮮所涉獵的我來說,要短期內做好它們,固然不是一樁輕鬆之事。但我既然準備著手去做,那就只有努力去奮鬥著了。不然,對不起廣大讀者不說,而且也對不起出版社的確切信任和鼎力支持。
馮氏經解“四書”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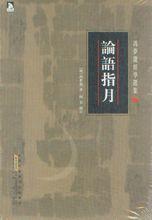 阿袁編著《論語指月》
阿袁編著《論語指月》事實上,馮氏《馮夢龍全集》中的《四書指月》一書,它只是馮氏對《論語》和《孟子》兩書的解說,並沒有對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學》的說解,一如朱熹《四書集注》那樣名副其實地收羅“四書”。因此,這次整理編輯出版,我就把馮氏的《四書指月》析為《論語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冊,獨立出版。
我們知道,《論語》《孟子》中的語句固為經典,而馮氏說解對之亦頗多闡發。蓋馮氏博通經史,在解讀《論語》《孟子》時委實頗多勝義,其中的現實警示意義不唯在當時有其特殊價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稱得上是足以指導和糾正人們言行的上上箴言。如《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說的“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確是千古哲言;對此,馮氏即進一步講解道:“君子會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全向人討生活。”這分明將《論語》中孔子的原話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其勵志處委實令人激賞。又如講解所涉啟發式教育和“舉一反三”這一語典時,馮氏即進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故不啟發者,正以進之啟發;‘不復’者,正以進之能‘反’。重學者身上理會。”(具見《述而篇·子曰不憤章》)
而馮氏對於《孟子》的見解亦復如是。如在《孟子曰子路人告章》說到孟子“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這千古哲言時,馮氏即進一步講解道:“‘樂取諸人’,舜忘人也;即此是‘與人為善’,則人也相忘於舜矣。人己兩忘,樂之至也,同之極也,到此地位,才復得此善原初無礙之本體,故曰‘莫大’。”這解說可謂精到透闢,要言不煩,而語語中的。此外,馮氏在解說《公孫丑·孟子致為臣章》中,剖析孟子離開齊王時,對兩人一番應對間的話外音頗能挖掘其深意,亦即對兩人的心事可謂足以透徹掌握。因為齊王是為了貪圖禮賢下士的虛名,而孟子則為了獲取足以實施抱負的實職,馮氏因對當事人的內心體貼親切,故能說得淋漓盡致。而馮氏一句“直是借他人話,表自己心”,這若非目光如炬,何能洞幽燭微若是!?至於如《離婁·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等所說“父兄在家庭間,觀感最近,故人於父兄處最得力”,也是涵泳有味的話頭;此外,書中如此之類所在多有,限於篇幅,這裡不復贅舉,相信讀者自能從容尋繹。
馮氏對經文斷句的成就
馮氏說解對深入理解《論語》《孟子》原文大有幫助,其主要大抵體現在對《論語》《孟子》原文的準確斷句上。因為歷來經學家們如朱熹等固然是以其自身所是而斷句,即便是錯誤的句讀,後人也大多不敢提出不同的見解。而馮氏則似乎不是如此,他既有對朱氏的肯定,如其行文中所說的“朱子說是”之類,但主要還是以其自身學者的體悟作出頗為可信的句讀,實為難能可貴。
如諸書對《論語·陽貨篇·陽貨章》的斷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見紛紜;至於人們讀後也確實覺得雲山霧罩,不得要領。但馮氏說解中僅一句“記者於此方著個‘孔子曰’”云云,即可解決問題,因為這種正確的句讀立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對《憲問篇·南宮适問章》關於南宮适問孔子語時的解說,亦即馮氏對通行本句讀“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說時,以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詞;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當屬‘禹、稷’句,乃轉下落重語”;我們知道,馮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論語·先進》,跟這裡的用法確實有異,可見馮氏這別出心裁的說解因不襲舊說而別有新見,這就令人涵泳不盡了。而馮氏此等說法對理解《論語》原文確有如湯沃雪之功,類似勝義在書中可謂俯拾即是。
毫無疑問,馮氏在解釋《孟子》時庶幾不遜於此。如諸書對《孟子·盡心篇·齊飢陳臻曰章》(按著名成語“馮婦重來”即出於此章)的斷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見紛出而又莫衷一是,但馮氏說解中補充一句“一說‘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眾逐虎’句;‘士則之’與‘士笑之’正相應——較勝”云云,即可使我們得到確切的解答,因為文從字順嘛。誠然,馮氏的說法卻也並非最早,蓋宋人劉昌詩《蘆浦筆記·馮婦》就是如此斷句的;而八十年前魯迅先生也曾論說過這事兒(具見《花邊文學·點句的難》等)。所以我在點校時,既照顧到歷史著名版本的斷句,同時也參考馮氏的說解;誠然,其中還須參以己意而作出的標點,固然也就與通常版本如朱熹等人的頗為不同了。而這,順便在此附帶說明一下。又如在對《滕文公·滕定公章》中的通行本句讀“曰:‘吾有所受之也。’”確乎難以句解;朱熹注中則作連上文讀,亦頗覺意旨難明;而今北京大學出版社版《孟子索引》乃作其父兄之言處理,尤屬扞格難通。而馮氏以為“此乃世子答父兄之語,因他說宜從先祖”云云,則上下文脈自可豁然貫通了。又如《告子·孟子曰牛山章》,由於語句頗長,若非馮氏指點說明,則易籠統讀之,不但不易解會其文旨,更不易徹悟原文之妙的;而馮氏指明“看首二節,各有‘人見其’三句,不是慨嘆口氣,……通章三‘存’字最緊要”云云,此真金針度人者!至於其中分析切中肯綮處,詳盡而準確。因為馮氏的國學素養極為深厚,這並不是當今某些學者所能望其項背的。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時代環境和個人境遇早已大為不同。如此之類甚多,不煩贅舉。
馮氏徵引他人說法不拘成見
任何一位學者,在做學問時難免都會涉及對他人已有成果的徵引。對此,與當下某些所謂學人任意剽用他人成果卻不吱聲不承認很為不同的,馮氏往往真名實姓地標明這是誰的見解,那是某的高見,三百年前的人能嚴謹地做到這點,確乎不易。事實上,馮氏說解所徵引前人與時人的說法頗多,只要是有助於理解《論語》《孟子》原文的就收錄,而並不以說話者的聲望來取捨,所以書中除引錄一些學術權威的說法外,還使得許多現在名不見經傳者那頗具見地的解說得以保留;這種治學方法頗為可取。
尤為可說者,馮氏對當時業已被尊為聖人的朱熹之說(蓋指朱氏《四書集注》一書)亦敢多所訾議,但這是出於做學問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當甚乃錯誤的解說了。如講解《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章》中為孔子所稱“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時,便指出“雅與鄭聲,皆其聲調,非指其詞。朱子認作男女淫奔,而輕改《鄭風》之序,冤哉!”頗具見地。又如對《季氏篇·季氏將伐章》講解時,文末斷定“朱子分作兩節,便沒分曉”,所說頗合事實而不唯名人之言為是。而對於《孟子》的說解,馮氏亦復如是。如他往往說“朱《注》不用”等語,也就是說,馮氏對朱氏註解不妥處是不會苟同的(如《公孫丑·孟子去齊充虞章》等)。誠然,馮氏亦並不全跟朱子唱反調,比如《滕文公·景春曰章》時就曾客觀地指出:“愚按朱子仁、義、禮三字,雖不可用,然小注‘廣居’,以居心言;‘正位’,以立身言;‘大道’,以制行言,卻說得好。”對此,馮氏自述“亦非定與相左,只是虛心觀理”(具見《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眾惡章》解說語)。總之,馮氏講述時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為我們最終確切理解《論語》《孟子》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這,無疑是令人嘆賞不置的。
誠然,馮氏說解中多用明代口語,其明白淺顯處與現今所用語言幾乎沒有什麼大異。因為書中除了當時的常用字“之乎者也”外,還使用了為數不少的“的了嗎呢”,一如當今白話文所用者然。但也正是由於馮氏所用詞語不時有當時的熟語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沒有了隔膜的;而這,還得請讀者多多明察。此外,馮氏解說也並非全無可商榷的。如對《論語·泰伯篇·太宰問章》中解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時,以為“夫子以‘多能’為‘鄙事’”云云,與《論語》原意似乎就有些游離甚乃誤會了。
馮氏解說多涉文法技巧
眾所周知,明清文學批評家們(倘說大多是評點家或曰鑑賞家,似乎更為確切)對名著詳加評點,可謂一時風氣,而且也取得了很多實績和經驗。如人們所熟知的金聖歎評點《水滸傳》《西廂記》等,毛宗岡父子批點《三國演義》,張竹坡氏評點《金瓶梅》以及李卓吾評點《西遊記》等等,可謂兩代文事風氣使然;這對建立後世的文藝批評學無疑大有裨益。
馮氏生活在明清之交,自然頗受這種文藝思潮的薰染與影響。他本人自是嗜好這種文藝評鑑模式,所以在他別的書中亦多有其評點印記。《情史》是如此,《智囊》亦復如是,而於《四書指月》自然也就不例外了的。其實,我們閱讀馮氏這些評點,對洞徹《論語》《孟子》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處委實大有助益。因為除了對原文重出者不予說解外,馮氏幾乎對《論語》《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確評,而且必使達到原文蘊涵無餘剩而後已的程度;這種著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賞析的境界確乎使人讀後頗覺痛快淋漓。至於他扼要論說《論語》《孟子》原文中那巧妙的筆法,尤其有利於初學習文者;而對於行文老手來說,它其實亦不是沒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如在《衛靈公篇·子曰君子義章》所批點“首尾兩‘君子’正相呼應”等等,即是。又如“此文字暗藏機軸處”(具見《梁惠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章》)、“此文字針線處”、“此文字細密處”(以上均見《滕文公·有為神農章》)、“……此虛實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之;而猶益之於夏,又借主形客,盡文之變。”(具見《萬章·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章》)等等即是。兩書所涉此類寫作技巧者,真可謂觸目即見;而這,對現在人們有志寫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時時饒有醍醐灌頂之樂。
贅餘·編注者必做的相關事
如前所述,本編《論語指月》《孟子指月》二書,其實就是從馮氏《四書指月》析分出來的。而《四書指月》固然是以現今國家圖書館所藏《四書指月》殘存明寫本的影印本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該影印本原書不知卷數,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僅存《論語》六卷,其中尚有缺頁。該書按章分節疏講二書,將馮氏的知識、見解融匯其中,對讀者頗具輔導效用。
由於底本《四書指月》並不同具《論語》《孟子》原文,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或許不成問題,但現在卻恐就不一樣了,因為當今絕大多數讀者遠沒有達到“飽讀四書五經”的程度;故此,若沒有《論語》《孟子》原文對看,那就勢必對深入理解和確切掌握《論語》《孟子》精義是個障礙,而且這還不僅僅是“閱讀不便”而已。舉個例子來說,如《顏淵篇·子張問士章》中的“夫達節”,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訛為“天達節”,致使後來諸多古籍出版社點校本亦多沿襲其誤;如此之類,其他地方尚多,恕不贅舉。因此,若不照錄《論語》原文,則多數讀者勢必難以理解馮氏文中的所謂“天達”究為何所指,那就更別奢望能夠立刻明白馮氏原本精闢的論述意義何在了。於是編者取坊間權威的《論語》版本並移錄在馮氏說解之前,以便讀者能夠從容真切玩味;唯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頗多不同者,則擇善而從,且於文後略作按語以供讀者採擇。昔人有所謂備此一書,即不必更求《論語》其他版本的說法;信夫!而《孟子》的情況自是與此相類,不須贅述。
此外,由於《論語》《孟子》(尤其是前者)原文前後頗多重出,故馮氏對後出的語段就不予解說了。但本編為使《論語》《孟子》原文完整起見,特行取錄,以便使之成為完璧。唯本編句讀有與通行版本頗有不同處,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當同者不得不同,當異者不得不異”的原則進行的,“雖一時或駭里耳,後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見馮氏《〈麟經指月〉發凡》);對此,誠可謂“於我心有戚戚焉”(具見《孟子·梁惠王上》)。
誠然,底本《四書指月》有字跡漫漶,一時不可辨識者,亦有前後錯字而不可卒讀者,今以文意貫串之,並略作校注與按語,以便於讀者省覽云爾。誠然,編者也有明知其不確者,但因沒有相應的對校資料或一時疏慵,只得姑且一仍其舊,還請讀者鑑諒。
而在研究《四書指月》的過程中,鄙人曾見一古籍版的馮書點校,其間句讀的訛誤觸目即是,令人不堪卒讀。魯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寫過多篇關於“點句的難”的文章(具見《花邊文學》和《熱風》等集子),現在看來,這種令人憂慮的現象依然還沒能有效解決。因為不當的校點非但不能成為馮夢龍的功臣,反而欲使之湮滅了的。誠然,馮氏學識淵博,所涉經史子集的內容甚廣,其校點難度確乎不小,亦自是實情,但有些似乎頗為明白的居然也斷句有誤,那恐怕就說不過去了。至於筆者自知學識譾陋,雖勉為校點,然不敢遽稱處處標點皆能允當無憾,尚祈世之博雅君子有以匡我未逮,則幸甚!
但總之一句話,讀者若能時時跟聖賢們近距離對話,並深研經典字義的蘊涵,那么達到明事理,會讀書,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領導等等境界,是當可深信不疑的了。而宋代開國宰相趙普所謂“半部《論語》打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語本《鶴林玉露》卷七;而實則《孟子》又何獨不然?),這或許就是對上述見解的最簡括性闡述吧?
2012年11月25日,歲次壬辰陽月穀旦於都門城南藉齋,阿袁記 。
緒言
現在人們知道明代文化大家馮夢龍先生的大名,似乎大多由於看過所謂“三言兩拍”的緣故;其實,這“兩拍”的著作權卻是另有所屬的。而馮氏除“三言”等通俗文學的成就殊顯突出之外,比如經學,比如史學,比如筆記雜綴等等,固然也不可等閒視之。而經學方面的著作,則委實是馮氏畢生孜孜矻矻地從事乃至殫精竭慮撰成的;對此,馮氏自己似也頗為欣賞其勝義。另一方面,馮氏這些經學著作,也為他贏得不菲的社會影響和一定的經濟收入;因為根據有關書籍記載,馮氏這些經學著述在當時的讀者群尤其眾多科舉生員中是成了“暢銷書”的。 而馮氏留存至今的有關經學方面的著作,大抵有《四書指月》、《麟經指月》、《春秋衡庫》、《春秋定旨參新》等,共約二三百萬言;這真可謂犖犖大端了。至於其中《四書指月》一書,其實只是馮氏對《論語》和《孟子》兩書的解說,並沒有對另外二部《中庸》和《大學》的說解,一如朱熹《四書集注》那樣名副其實地收羅“四書”。因此,這次整理編輯出版,本人就把馮氏的《四書指月》析為《論語指月》和《孟子指月》二冊,獨立出版。茲就《論語指月》編注過程中所想到的向讀者諸君做個簡括的說明,或許對讀者通過馮夢龍那別具匠心的解說進一步深入理解《論語》這千古經典有所幫助,從而真正洞悉古人所明告我們——《論語指月》一書是足可以明事理,會讀書,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領導了的。
一、兩千年來,《論語》不但是我國歷代讀書人的經典,也是一切國人的經典。其中所展現出來的建功立業、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等行為規範,影響世人至深。但自從上世紀初葉,在所謂“打倒孔家店”後,一些國人竟不由自主地捐棄了優秀的傳統文化,使得原本優良的傳統道德亦跟著頓失依歸;放眼現在某些國人道德淪喪這極為嚴峻的現狀,有識之士都為之深思,進而迫切熱望要讓優良的傳統道德回歸。故此,重讀諸如《論語》等傳統經典,固然是一樁亟不可緩的事兒;相信學習、研讀和運用《論語》等經典,正是人們為提高傳統道德自律和自身綜合素養的可行法門之一。而文化大家馮夢龍的《論語指月》對《論語》的獨特解說,必將會使讀者獲取相當滿意的答案。
二、《論語》語句固為經典,而馮氏說解對之亦頗多闡發。蓋馮氏博通經史,在解讀《論語》時委實頗多勝義,其中的現實警示意義不唯在當時有其特殊價值,就是如今也依然稱得上是足以指導和糾正人們言行的上上箴言。如《子曰君子求章》中孔子所說的“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確是千古哲言;對此,馮氏即進一步講解道:“君子會得己真,看得己大,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諸己;小人看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全向人討生活。”這分明將《論語》中孔子的原話做了進一步的闡發,其勵志處委實令人激賞。又如講解所涉啟發式教育和“舉一反三”這一語典時,馮氏即進而引申道:“教人之法,最忌說盡。依我作解,障彼悟門,此大病也。故不啟發者,正以進之啟發;‘不復’者,正以進之能‘反’。重學者身上理會。”(具見《述而篇·子曰不憤章》)如此之類所在多有,限於篇幅,這裡不復贅舉,相信讀者自能從容尋繹。
三、馮氏說解對深入理解《論語》原文大有幫助。如諸書對《陽貨篇·陽貨章》的斷句各行其是,以致歧見紛出而又莫衷一是;至於人們讀後也確實覺得雲山霧罩,不得要領。但馮氏說解中僅一句“記者於此方著個‘孔子曰’” 云云,即可解決問題,因為這種正確的句讀立馬使人憬悟孰是孰非。又如在對《憲問篇·南宮适問章》關於南宮适問孔子語時的解說,亦即馮氏對通行本句讀“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作解說時,以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未定之詞;羿、奡是已然事,故‘然’字當屬‘禹、稷’句,乃轉下落重語”;我們知道,馮氏所引“若由也”句,源出《論語·先進》,跟這裡的用法確實有異,可見馮氏這別出心裁的說解因不襲舊說而別有新見,這就令人涵泳不盡了。而馮氏此等說法對理解《論語》原文確有如湯沃雪之功,類似勝義在書中可謂俯拾即是。因為馮氏的國學素養極為深厚,這並不是當今某些學者所能望其項背的。其實,這也不難理解,因為時代環境和個人境遇早已大為不同。
四、馮氏說解所徵引前人與時人的說法頗多,只要是有助於理解《論語》原文的就收錄,而並不以說話者的聲望來取捨,所以書中除引錄一些學術權威的說法外,還使得許多現在名不見經傳者那頗具見地的解說得以保留;這種治學方法頗為可取。尤為可說者,馮氏對當時業已被尊為聖人的朱熹之說(蓋指朱氏《四書集注》一書)亦敢多所訾議,但這是出於做學問的公心,因此也就多所匡正朱氏不當甚乃錯誤的解說了。如講解《衛靈公篇·顏淵問為邦章》中為孔子所稱“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時,便指出“雅與鄭聲,皆其聲調,非指其詞。朱子認作男女淫奔,而輕改《鄭風》之序,冤哉!”頗具見地。又如對《季氏將伐章》講解時,文末斷定“朱子分作兩節,便沒分曉”,所說頗合事實而不唯名人之言為是。誠然,馮氏亦並不全跟朱子唱反調的,比如他講《子貢問曰有一言章》時即稱“朱注甚明”。對此,馮氏自述“亦非定與相左,只是虛心觀理”(具見《子曰眾惡章》解說語)。總之,馮氏講述時這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為我們最終確切理解《論語》提供了良好的版本;而這,無疑是令人嘆賞不置的。
五、閱讀馮氏的說解,對我們洞徹《論語》行文中的文法高妙之處大有幫助。除了對原文重出者不予說解,馮氏幾乎對《論語》原文做到字字精研,句句確評,而且必使原文蘊涵無餘剩而後已的程度;這種著意深入研究和真切賞析的境界確乎使人讀後頗覺痛快淋漓。至於他扼要論說《論語》原文中那巧妙的筆法,尤其有利於初學習文者;而對於行文老手來說,它其實亦不是沒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如在《衛靈公篇·子曰君子義章》所批點“首尾兩‘君子’正相呼應”等等,即是。而全書所涉此類寫作技巧者,真可謂觸目即見;而這,對現在人們有志寫好文章和洞明古人行文用意者自是大有裨益,而且時時饒有醍醐灌頂之樂。
六、由於《論語》原文前後頗多重出,故馮氏對後出的語段就不予解說了。但本編為使《論語》原文完整起見,特行取錄,以便使之成為完璧。唯本編句讀有與通行版本頗有不同處,這是按照古人所指明的“當同者不得不同,當異者不得不異”的原則進行的,“雖一時或駭里耳,後世不乏子云,必有玄吾玄者矣”(具見馮氏《〈麟經指月〉發凡》);對此,誠可謂“於我心有戚戚焉”(具見《孟子·梁惠王上》)。
七、在校閱過程中,本編特行增錄《論語》原文以便利讀者。由於底本《四書指月》並不同具《論語》原文,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或許不成問題,但現在卻恐怕就不一樣了,因為當今絕大多數讀者遠沒有達到“飽讀四書五經”的程度;故此,若沒有《論語》原文對看,那就勢必對深入理解和確切掌握《論語》精義是個障礙,而且這還不僅僅是“閱讀不便”而已。舉個例子來說,如《顏淵篇·子張問士章》中的“夫達節”,底本和其他刻本原多訛為“天達節”,致使後來諸多古籍出版社點校本亦多沿襲其誤;如此之類,其他地方尚多,恕不贅舉。因此,若不照錄《論語》原文,則多數讀者勢必難以理解馮氏文中的所謂“天達”究為何所指,那就更別奢望能夠立刻明白馮氏原本精闢的論述意義何在了。於是編者取坊間權威的《論語》版本並移錄在馮氏說解之前,以便讀者能夠從容真切玩味;唯其中文字因版本之故而頗多不同者,則擇善而從,且於文後略作按語以供讀者採擇。昔人有所謂備此一書,即不必更求《論語》其他版本的說法;信夫!
八、底本有字跡漫漶,一時不可辨識者,亦有前後錯字而不可卒讀者,今以文意貫串之,並略作校注與按語,以便於讀者省覽云爾。誠然,編者也有明知其不確者,但因沒有相應的對校資料或一時疏慵,只得姑且一仍其舊,還請讀者鑑諒。
九、馮氏說解中多用明代口語,其明白淺顯處與現今所用語言幾乎沒有什麼大異。因為書中除了當時的常用字“之乎者也”外,還使用了為數不少的“的了嗎呢”,一如當今白話文所用者然。但也正是由於馮氏所用詞語不時有當時的熟語或方言,反而使得今人未必就沒有了隔膜的;而這,還得請讀者多多明察。此外,馮氏解說也並非全無可商榷的。如對《泰伯篇·太宰問章》中解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時,以為“夫子以‘多能’為‘鄙事’”云云,與《論語》原意似乎就有些游離甚乃誤會了。如此之類,其他地方也有,請讀者自行留意。
十、本編以現今國家圖書館所藏《四書指月》殘存明寫本的影印本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唯該影印本原書不知卷數,有眉批,除《孟子》七卷外僅存《論語》六卷,其中尚有缺頁。該書按章分節疏講二書,將馮氏的知識、見解融匯其中,對讀者頗具輔導作用。而在研究《四書指月》的過程中,鄙人曾見一古籍版的馮書點校,其間句讀的訛誤觸目即是,令人不堪卒讀。魯迅先生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曾寫過多篇關於“點句的難”的文章(具見《花邊文學》和《熱風》等集子),現在看來,這種令人憂慮的現象依然還沒能有效解決。因為不當的校點非但不能成為馮夢龍的功臣,反而欲使之湮滅了的。誠然,馮氏學識淵博,所涉經史子集的內容甚廣,其校點難度確乎不小,亦自是實情,但有些似乎頗為明白的居然也斷句有誤,那恐怕就說不過去了。至於筆者自知學識譾陋,雖勉為校點,然不敢遽稱處處標點皆能允當無憾,尚祈世之博雅君子有以匡我未逮,則幸甚!但總之一句話,讀者若能時時做到念誦馮氏《論語指月》一書,則達到明事理,會讀書,善撰文,足研究,能管理,擅領導等等境界,是當可深信不疑了。而宋代開國宰相趙普所謂“半部《論語》打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語本《鶴林玉露》卷七),這或許就是對上述見解的最簡括性闡述吧? 2012年7月15日,歲次壬辰仲夏穀旦於都門城東藉齋,阿袁記。
![陳君[詩人、學者、文學家、魯迅學家] 陳君[詩人、學者、文學家、魯迅學家]](/img/9/7cf/nBnauM3X0IDO1MjN4gjM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4IzLxg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