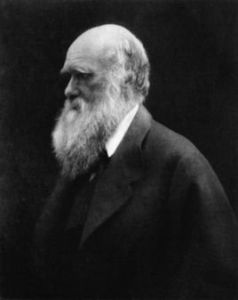歷史概要
達爾文之前的進化觀念
在 達爾文之前,大多數對於物種多樣性的解釋都秉承了與基督教教義相結合的 亞里士多德主義觀念。達爾文在《 物種起源》第三版的歷史概要中寫道:“直到今天,大多數博物學家認為物種是永恆不變的。它們被分別地創造出來。許多作者都巧妙地維護著這一觀點。”
但生物進化的理念並不源自達爾文。早在達爾文祖父那一代就流行著生物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思想,而一些自然哲學家更是被看作達爾文的先驅。例如E. G. 聖-希萊爾認為,識別同源性是梳理進化關係的核心手段。J. L. N. F. 居維葉則反對希萊爾的觀點,並強調功能的重要性。但他主張,物種不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變化。因為根據他的觀測,每個物種的結構看上去都像經過了細緻的調節,以至於最微小的改變都會導致整個有機體的功能受到破壞。居維葉同意地質災變說,並認為部分物種會隨著地質災變的發生而消亡。與居維葉同時代的J. B. 拉馬克提出了不同的理論。他認為物種會發生變化;動物物種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這些物種的變化是通過繼承獲得性狀得到的。在拉馬克1802年的論文中,他描繪了一種進步式的進化理論:“[物種]從最簡單的上升為最複雜的……自然界中最簡單的產物會相繼地產生出其它產物。” 在1809年出版的《動物學哲學》中,拉馬克主要提出了三個觀點:第一,物種的變化受到外部壞境變化的影響;第二,在物種的多樣性之下存在著統一性的基礎;第三,物種總是會進步式地發展。相比於達爾文的進化論,拉馬克的理論呈現出以下三個不同點:第一,他的解釋中沒有提及自然選擇的機制;第二,他認為物種是朝著完美的方向發展的;第三,拉馬克的理論中不存在物種滅絕。
此外,達爾文的進化論與上述理論有一個決定性的不同。P. J. 理查森和R. 博伊德認為,“在達爾文之前,人們將物種構想為具有本質的、沒有變化的類型——就像幾何圖形和化學元素那樣” ,而達爾文則在族群的層面上思考物種。達爾文的這一觀念與他的自然選擇理論是相互聯繫的。
社會環境
除了這些理論先驅之外,部分社會環境對達爾文理論的產生與傳播而言也具有重要意義。當時人們熱衷於收集化石,而這些對這些化石的研究為生物學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然而人們收集化石的熱情並不源自對生物學知識的渴求——這一行為主要受到自然神學的影響。根據W. 佩利的想法,如果我們在沙灘上發現了一塊手錶,那么會認為這件精緻的東西是被人設計的;同樣,當我們發現結構如此精美的生物時,就應該相信這些東西是上帝設計的。人們收集化石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尋找上帝的作品。另一個重要的事件是《創世的自然歷史遺蹟》在1844年匿名出版。(後來作者被鑑定為R. 錢伯斯。)這本書中提倡“進步主義”的進化理論。其中認為物種的變化由遙遠的、神聖的創造者所管制。此外,像當時許多博物學家一樣,作者相信每個物種都是分別發展而來的;也就是說,它們沒有共同的祖先。《遺蹟》是維多利亞時代非常流行的“科普讀物”。儘管科學界對它的反應十分冷淡,但直到十九世紀末,該書的銷量都勝過《物種起源》。達爾文也指出,“《遺蹟》在1844年出現……在我看來,它很好地讓這個國家的人注意到這個主題……並為人們接受類似的觀點準備了基礎。”
此外,達爾文的觀點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很大的轟動。相反,當A. R. 華萊士與達爾文在1858年聯名發表論文並召集博物學家旁聽時,大家對這一理論幾乎完全不感興趣。他們認為其中並沒有特別令人震驚的革命性理論。甚至在1859年《物種起源》第一版出版時,公眾也只是反應平平。同時,M. 魯斯認為,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人們更感興趣的是同源學。“適應器[這樣的概念]對於嘗試著辨別同源性的人來說只是一個麻煩” 。
從上述歷史中可以看出,達爾文的理論並不是含著銀匙憑空出世的。在達爾文的進化論沒有受到重視的情況下為其代言、造勢,並創造出“達爾文主義”一詞的事實上是華萊士。但是華萊士與達爾文的觀點存在很大分歧。 輝格史觀的“達爾文主義”多指華萊士所倡導的“純粹達爾文主義”。
基本簡介
達爾文運用大量地質學、古生物學、比較解剖學、胚胎學等方面的材料,特別是他在環球航行期間以及研究家養動植物時所獲得的第一手材料,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現存多種多樣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漸演化而來的,揭示了自然選擇是生物進化的主要動因,從而使進化論真正成為科學。自然選擇的主要內容包括變異和遺傳、生存競爭和選擇等。變異是選擇的原材料,在生存競爭中,有利的變異將較多地保存下來,有害的變異則被淘汰。有利變異在種內經過長期積累,導致性狀分歧,最後形成新種。生物就是這樣通過自然選擇緩慢進化的。英國生物學家A.R.華萊士與達爾文同時提出了類似思想,並於1889年第一次把達爾文的學說稱為“達爾文主義”。達爾文主義的著名代表人物還有T.H.赫胥黎和E.H.海克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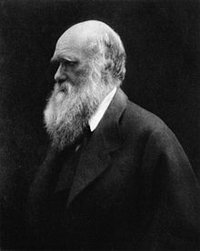 達爾文
達爾文新達爾文主義的由來
達爾文對批評的回應
自《物種起源》出版後,許多人對達爾文的 自然選擇學說提出了質疑。其中最重要的挑戰來自St G. 密瓦特和F. 簡金。
在密瓦特對達爾文的批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自然選擇這樣漸進式的進程超出了當時地質學理論所允許的範圍。達爾文的生物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C. 萊爾的地質學理論影響。在1830年出版的《 地質學原理》中,萊爾描繪了緩慢、漸進的地質變化過程;而他所估算的地球年齡也略長於他同時代的理論家。但是物理學家W. 湯姆森用熱力學定律重新估算了地球年齡。他通過計算地球從融化金屬的溫度冷卻到當前溫度所需的時間,得出地球年齡為1-4億年的結論。其中可供生物進化的時間為1000-3000萬年。而根據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生物進化至少需要3億年。湯姆森的這一結論直到二十世紀初人們發現利用同位素測定地球年齡的方法後才被否定。
簡金的反駁主要基於當時流行的混合遺傳(blending inheritance)理論。根據這一理論,脖子較長的長頸鹿與脖子較短的長頸鹿通過交配繁殖出的後代是脖子中等長度的長頸鹿。那么如果只存在一隻脖子較長的長頸鹿,它只能與其它脖子較短的長頸鹿交配。數代之後,其後代的脖子會越來越短,到最後幾乎與其它脖子較短的長頸鹿一樣。簡金把這樣的後果稱作“沼澤效應(swamping effect)”。如果沼澤效應是對的,那么自然選擇根本無法將具有適應性的性狀保留下來。
為解決這些問題,達爾文在1868年的書中提出了他的遺傳理論: 泛生論。在這一理論中,達爾文事實上允許了拉馬克式“獲得性狀遺傳”的存在。達爾文認為泛子(gemmule)可以沉睡和再現,因此它不需要在每一代中都被表達出來。(具體參見 泛生論。)在引入了泛生論後,達爾文通過用獲得性狀遺傳機制解釋部分生物進化現象而縮短了進化所需的時間,並迴避了沼澤效應。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達爾文的理論大多只被套用於植物和其它較低級的生命形式;第二,就像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所陳述的那樣,致殘(mutilation)無法被遺傳。他在解釋泛生論時也提到了這一點。基於以上兩點描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A. 魏斯曼切斷老鼠尾巴的試驗事實上無法證偽泛生論。
華萊士與新達爾文主義
諷刺的是,“達爾文主義”一詞在達爾文死後才開始流行。華萊士1889年出版了《達爾文主義》一書。華萊士希望藉此推進一種“純粹的”達爾文主義。它拒絕了達爾文的泛生論以及其它所有承認獲得性狀遺傳的內容。在書中,華萊士提到:“……我的所有工作力圖展示出在新物種產生的過程中自然選擇壓倒性的重要性。因此我站在達爾文先前的立場上……我認為這本書的立場是在擁護純粹的達爾文主義。”
華萊士認為魏斯曼的理論完全支持他所提出的純粹達爾文主義。魏斯曼的工作駁斥了“用進廢退”的獲得性狀,並在身體細胞(Soma)與遺傳物質(Germ plasm)之間放置了壁壘。但事實上,魏斯曼並沒有完全否認外界因素對遺傳的影響。他區分了“自發的胚芽選擇(spontaneous germinal selection)”與“誘發的胚芽變異(induced germinal variation)”;只有前者類似於今天所說的基因突變。
G. J. 羅曼斯創造了“新達爾文主義”這個詞。從他的另一個表述,“極端達爾文主義(Ultra-Darwinism)”中可以看出,羅曼斯本人將“新達爾文主義”看作一個貶義詞。他將“新達爾文主義”和“純粹達爾文主義”用作“華萊士主義”和“魏斯曼主義”的同義詞。“這樣我們就能區分出達爾文的達爾文主義和與之對照的華萊士的達爾文主義,或者說,跟後者是同一回事的魏斯曼的新達爾文主義學派。”
F. 埃爾斯頓-貝克認為,新達爾文主義實際上是直接從華萊士那裡跳到了魏斯曼那裡——其中並沒有經過達爾文。“確實,即便達爾文從未存在過,我們大概也能或多或少地得到今天的新達爾文主義。華萊士提供了自然選擇的理念,並像一個新達爾文主義者那樣是嚴格的選擇論者;而魏斯曼的作用顯然是引入了隔離遺傳物質的理念——它將除了自然選擇之外的進化方式全都無效化了。”
從今天生物學和人類學的發展情況看,新達爾文主義並不比達爾文的達爾文主義更加優秀。生物學中的 表觀遺傳可以被看作是獲得性狀的遺傳,而在 文化進化理論中,社會科學家們幾乎完全放棄了將文化單元與基因進行嚴格類比的做法。因此,從適用性上看,達爾文的達爾文主義並不“落後於”新達爾文主義。
重要貢獻
19世紀下半葉,細胞學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陸續發現了細胞核、染色體以及有絲分裂、減數分裂等重要事實。在這些成就的基礎上,魏斯曼通過自己的實驗研究,認真探討了遺傳和進化問題。他做了著名的小鼠尾巴切割實驗,發現連續切割22代,小鼠尾巴並未變短,他由此否定獲得性狀遺傳(見拉馬克主義)。魏斯曼提出,生物體由種質和體質所組成。種質即遺傳物質,專司生殖和遺傳;體質執行營養和生長等機能。種質是穩定的、連續的,不受體質的影響,它包含在性細胞核主要是染色體裡。獲得性狀是體質的變化,因而不能遺傳。魏斯曼認為,進化是種質的有利變異經自然選擇的結果。1917年,摩爾根提出“基因論”,把魏斯曼的種質發展為染色體上直線排列的遺傳因子、即基因。新達爾文主義是進化學說發展中承上啟下的一個重要階段。魏斯曼把遺傳學和自然選擇學說結合起來,開創了進化論研究的新方向。他首次區分種質和體質,指明了遺傳的物質基礎及其連續性,在遺傳機制上補充了達爾文的觀點。這是新達爾文主義的重要貢獻。然而,魏斯曼把種質和體質絕對對立起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爭論焦點
達爾文主義與非達爾文主義都是進化論的分學說。
達爾文主義堅持認為進化的動力在於“自然選擇”。重視環境和生態的作用。
非達爾文主義則認為在DNA分子水平上,認為生物進化所標保留下來並不都是所謂的“適應環境的性狀”,而是“這個形狀的存在並沒有影響到這個物種的生存”。人們在研究DNA分子結構和基因結構時,發現由貯存遺傳信息的核普酸分子的置換所造成的基因突變,除了有害的之外,能夠保留下來的有利突變是微乎其微的,大部分則是對於自然選擇來說既無利也無害的“中性”突變。如果把輕度有害、近似中性的突變算在內,中性的則占整個突變數量的大多數。因此,在進化中擔任主角的不是“有利突變”,而是“中性突變”。
達爾文主義學派側重從生物體結構的高層次、從生態角度考察進化問題,非達爾文主義學派側重從生物體結構的低層次、從生化角度考察進化問題。由於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出了相互矛盾的看法,
形成了兩種對立的學說。然而,如果全面考察這兩個層次上的進化機理,即可發現這兩種學說並不是絕對排斥、互不相容的。高層次與低層次是相互聯繫、相互滲透的,兩個層次上都存在有利、
有害和中性這三種變異。單用選擇說或單用中性說都不能全面說明任何一個層次上的進化機理。從認識論上說,無論是選擇說還是中性說,都是對進化問題認識的一個方面,是認識發展過程的一個片段,都具有相對的真理性,都不能把任何一種學說絕對化。
達爾文主義的終結
進化論是自然科學最重要的基本理論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大自然科學基石;不用說,達爾文及其學派對進化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儘管人們往往知之不多,但早已默許、習慣了的“生存鬥爭、自然選擇”卻是一個錯誤的進化觀!而且,達爾文主義也並不等於馬克思主義;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觀也不等於馬克思主義的進化觀。
比如:恩格斯生前就曾堅定地站在達爾文一邊,駁斥狂妄的杜林先生;同時也明確指出:“…但是進化論本身還很年輕,所以,毫無疑問,進一步的探討將會大大修正現在的、包括嚴格達爾文主義的關於物種進化過程的觀念①。”而且,恩格斯還曾特地申明:我們只是“暫且承認‘生存競爭’這個公式。②”至於我們還知道的:西方現代達爾文主義學派一般都是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者,那就更不用說了。
可見,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觀與馬克思主義的進化觀不是一回事。
可惜,恩格斯生前沒有來得及作較為系統的進一步探討,沒有留下經他“大大修正”了的關於物種進化過程的論述。更重要的是,一百多來由於種種原因,在現代社會主義理論中,達爾文主義一詞也差不多完全被進化論所替代,以至人們只要一提起進化論差不多都是指達爾文主義。似乎歷史上從來就不曾有過兩種不同的進化觀;似乎達爾文主義“關於物種進化過程的觀念”再也沒有人懷疑了…
那么,恩格斯生前又為什麼“毫無疑問”的要“大大修正”呢?恩格斯的意見是否早已陳舊過時;原本就沒有必要區分兩種不種的進化觀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當然不贊成教條主義。因此說到底,達爾文主義究竟有沒有錯?它的錯誤性質究竟怎樣?是不影響進化論的發展還是已成為其發展的障礙?馬克思主義是否也可以永遠建立在這個不正確的自然科學基礎之上呢?
這裡,我們就來作一些初步的探討,但願能引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興趣。
一,重審達爾文主義
美國動物學大師,忠實的達爾文主義者老克利夫蘭,對其有一段極精當的描述,我們謹摘錄如下:
“該原則乃是根據這樣的觀察事實:沒有兩個生物是完全相同的;至少有些變異是可以遺傳的;所有類群都傾向於產生太多的同類;因為繁殖的個體比可生存的個體多,所以在個體之間存在競爭。按照達爾文的看法,在生存競爭中,具有能使之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的那些生物就會生存下來。如果它們生存了下來,因而比有利變異較少的生物有著較多的後代的話,那么它們的遺傳特徵就會以較大的比例出現在一個世代中。這種自然選擇繼續下來,就會產生連續的進化變化。③”
這就是達爾文主義關於物種進化過程的觀念(或原理)。毫無疑問:“沒有兩個生物是完全相同的”換句話說,所有個體之間都存在差異。但是,並非所有差異都是變異。同樣也是觀念事實:所有生物類型的形態特徵、大小及顏色等都有一個大致的差異範圍;人們也早已習慣了這個範圍內的差異,都將其視為一般差異;只有那些明顯超出這個範圍的差異,人們才視為變異。這裡顯然撇開了這個無疑十分重要的邏輯劃分,直接就跳到了變異的遺傳。“至少有些變異是可以遺傳的”那么,哪些變異可以遺傳?哪些變異又不可以遺傳?差異與變異在遺傳中的意義是否完全一樣?決定遺傳和不遺傳的原因又是什麼?不用說,遺傳是研究生物進化不可迴避的重要環節,可惜這裡都沒有提及。“所有類群都傾向於產生太多的同類”顯然,這只能一般地說;比如大熊貓就不“傾向於產生太多的同類”。這且不說,這裡又撇開了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觀察事實:各種生物的繁殖能力也是千差萬別的;而且,生物的繁殖能力一般總與後代的成活就率成反比。比如在自然界,蝦類一次能產幾十萬粒卵,卻只有百分之幾甚至千分之幾的成活率;而許多高級哺乳動物一次只產一二個幼子。達爾文自己就曾告訴我們:生物不同的繁殖數量是與它們是否能有效的保護後代相關的。因此,我們也並沒有理由來否定這樣一個推論:生物各不相同的繁殖能力與各物種不同的繁殖方式一樣,也是對繁殖環境的一種適應。
顯然,這裡的目的無非是為下面的推論服務:“因為繁殖的個體比可生存的個體多,所以在個體之間存在競爭。”不用說,這個前提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還沒有被繁殖出來的個體是無所謂生存的。這樣的“事實”不需要“觀察”,當然也不能算真理。況且,這兩者之間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比如在蜂巢中,後羽化的新蜂王往往還沒有露頭就被前者消滅了。其意義不過是當第一隻新蜂王意外死亡時,總還有第二、甚至第三隻來補充,從而增加了該種群能夠及時延續下去的保證係數。當然,兩隻新蜂王同時出來的情況也是有的,但畢竟很少,而且,這也會造成兩敗俱傷;因此,為了儘可能防止這樣的情況出現,先蜂王產下兩枚王卵所間隔的時間總比兩隻非王卵多的多。
在這裡,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是那些大型的鷹類。它們不象家禽那樣同時孵出許多雛鳥,而總是分先後孵出兩隻雛鳥。一般情況下後者也不具備與前者競爭的能力,如果是食物短缺的年份,那么首先被淘汰的總是後者,除非前者意外死亡。因此我們說,這實際上也是對繁殖環境一種機動的適應:是在繁殖過程中,對可能出現的食物短缺,以及意外事故的積極預防。“按照達爾文的看法,在生存競爭中,具有能使之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的那些生物就會生存下來…”最初看來,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象上述兩個例子,淘汰或生存的順序其實早在新個體被繁殖之前就基本確定了,這與個體是否具有什麼變異並沒有什麼關係。再如在馬、鹿一類動物的種群中,最容易被淘汰的不也總是那些最幼小的個體嗎?在這種情況下,達爾文主義往往就把個體之間的競爭上升到種群之間的競爭,以此來湊合淘汰論。然而,正如“沒有兩個生物是完全相同的”,也沒有兩個生物種群是完全相同的。即使在同一個生態系統內,兩個同類生物種群所享受到的環境條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因此說到底,無論是對於不同的生物個體還是不同的生物種群來說,決定生存與否的因素都是多方面的,是否具有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充其量也只是眾多因素之一。只有在其它因素都完全相同的前提下,達爾文的這個推論才成立。
舉例來說吧,有兩匹小馬,其中一匹具有“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比如跑的更快;那么什麼情況下,這個“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才是這兩個個體之間生存與否的決定因素呢?很顯然,這兩個個體必須同樣大小、同樣健壯、同時發現危險,而且,與危險的距離也同樣,它們的反映速度也同樣,當時的疲勞程度也必須同樣等等。試想,在自然界中這種情況出現的機率又能有多少呢?再比如,我們就算一隻飛白蟻比其它所有個體都具有“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吧,那也總不至於能使之不怕風吹、雨打、蜘蛛與鳥獸吧?再如,我們就算一隻小長頸鹿比其它所有個體都具有“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頸子長的更快;那也總不至於一斷了奶它的頸子就比它的父兄更長吧?
由此可見,在決定生存與否的所有因素中,有否具有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往往都是微不足道的。最後,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例子:在中央台的《動物世界》里,我們常見大群角馬狂奔的鏡頭;它們那樣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究竟乾什麼去呢?原來,他們總是把繁殖的時間與區域儘可能的集中,以便於在一定的區域與時間內,它們的幼仔數量能遠大於食肉動物的需要量;直到過了這段時間,各種群才帶著倖存的已能與它們差不多善跑的幼仔擴散到原地去。在動物界,類似的現象很多,比如鹿、驢、大馬哈魚以及許多鳥類等。
由此可見,動物過量繁殖的意義無非是要增加延續後代的保證係數,而並非像達爾文主義所猜想的那樣是競爭。這就好比那些醫療條件越差的地區,計生工作就越難做一樣,誰聽說哪家生的孩子多是為了要讓他們“優勝劣汰”的呢?
“如果因為它們生存了下來,因而比有利變異較少的生物有著更多的後代…”
一眼看去,這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而現實更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比如在動物繁殖的季節里,我們常見到同性爭偶的現象,這歷來都被當作自然選擇的一個重要證據。其實我們也不難發現,遠不是所有個體的有利變異同時也是這種竟爭的有利因素。比如,有的個體跑得快是有利變異,有的個體耳朵靈是有利變異,有的個體眼睛尖是有利變異,還有的個體善於改變自己的顏色或形體是它的有利變異等等。很顯然,這些有利變異都不能保證它們在爭偶中取勝,因而也就不能保證它們“有著較多的後代”。
對於雌性來講就更不用說了,“具有更適應於環境的變異”與具有較強的繁殖能力顯然是兩碼事。
總而言之,根據以上粗淺的討論我們至少也可以感覺到:達爾文主義遠不象原先所想像的那么周密。
但是,由於多年來形成的一種迷信,或習慣性的崇拜,人們不管對進化論究竟了解多少,總願意相信達爾文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對此有必要再作稍微進一步的探討。
二,達爾文主義的由來與困境
在自然界,生物適合於環境,環境也適合於生物;越是生態環境少受侵害的地方,生物與環境就越顯得和諧統一,相得益彰。即使我們觀察一隻小蜘蛛,它的外形、顏色、結構與器官的功能等都無一不與它的生活方式相吻合。大自然美妙無限,以至很早以前許多先哲就被它所吸引,辛勤探索其中的奧密。在《舊約》以前,百家爭鳴,許多研究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可惜,後來教會霸權,還是多門科學母體的哲學成了神學的婢女,《舊約》就獨霸天下了。它告訴人們:所有物種都是上帝分別、特意地創造出來的。這就是“獨創論”;又叫“特創論”。
獨創論認為:當初上帝所創造的各物種就是人們現在所見到的形態特徵;也就是說,物種是不變的。
大約在十八世紀前後,隨著造船工業與航海技術的發展,人們關於自然界中各種動植物的知識也大大的豐富起來了;還有那些人們早已熟悉了的家養動植物種,幾乎每天都在告訴人們:物種不是不變的,而是在變的。
於是,人們對獨創論越趨不滿,開始尋找新的答案。
比如康德、還有達爾文的祖父,都在這方面作過不懈的努力。而且,他們也都注意到了:生物的形態結構與其生活方式的關係最為密切。
其中最著名的是拉馬克,他最先高舉進化論的旗幟向獨創論衝擊(拉馬克的觀點本源於他的老師_布豐,可惜布豐在舊勢力面前沒敢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拉馬克的進化觀叫做“用進廢退”。他舉例說:長頸鹿的頸子就是因為它的祖先總是要伸長頸子去吃高枝上的樹葉。那么,長頸鹿的祖先又為什麼總要伸長頸子去吃高枝上的樹葉呢?
看起來,這只能是環境所迫了;也就是說,環境條件的改變迫使生物改變它們生存活動的方式;而正是在這個改變了的生存活動方式的長期作用下,生物的形態結構等也必然要隨著改變了。
因此,這個觀點又叫做“獲得性遺傳”(後來又被稱之為:適應與遺傳)。可是,這個觀點在當時卻遇到了一個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礙:因為在當時看來,根據這個原理,似乎所有生物都應該與環境條件完全一致,並隨著環境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然而事實上遠不是所有生物都總是隨著環境條件的而改變,而且改變的方向也極不一致。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康德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墮入了不可知論;拉馬克也沒有找到令人滿意的答案。
達爾文很早就讀過前人(包括他祖父的)有關進化論的著作,但直到環球考察後才堅信:世界上沒有不變的物種;這才完全認清了獨創論的荒謬(請注意,還不是神創論),從而堅信進化論。但大量的考察與試驗也沒有能使他在生物變異的原因方面取得多大的進展。於是,他放棄了拉馬克的研究方向(達爾文祖父的觀點是與拉馬克相接近的),比康德更明確的提出自然選擇的進化觀(它是由康德最早提出來的;而且在亞里士多德那裡就有這個觀點的萌芽),認為:變異與進化是兩回事,變異的原因很多,使用與不使用只是其中之一,而進化則是具有一定方向的連續不斷的變異;而且,對物種進化的理解也不需要窮盡各種變異的原因,因為,各種變異都只是物種進化的前提或基礎,這裡只要能證明生物總是在“彷徨變異”(達爾文語)就足夠了;正是由於自然選擇為那些變異規定了方向,物種才進化了;因此,自然選擇才是進化的主動因。毫無疑問,這在當時來說,確實“再好沒有了”(恩格斯語),它使進化論又獲得了新生,從而推翻了獨創論,使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這裡,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達爾文對生物生存的外部條件的研究。(還須說明一點:限於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當時,對眾多觀察事實進行歸納比較,這也還是許多學科研究的主要方法;當時也正是歸納法的鼎盛時期,甚至曾出現荒謬的歸納萬能論。因此,在達爾文的研究中也必然要留下這一歷史的烙印。)下面就是他在《人的由來及性選擇》一書中的研究:
一,以一百萬以上的美國士兵為調查對象,結果證實:“當成長時居住在西部各洲有使身材增高的傾向”。二,調查還證實了海軍生活會延緩成長。例如:“十七、八歲的陸軍士兵和海軍士兵身材有巨大差別。”三,根據古爾德先生的調查:“人的身材與氣候、土地高度、土壤沒有關聯,甚至同生活的富裕和貧困也不以任何支配的程度相關聯。”
四,“但是,這一結論又同維勒美根據法國不同地方應徵士兵身高的統計直接相反…”
於是,達爾文堅信:外部條件的意義只在於“可以引起幾乎無限的彷徨變異…”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例子:當年,羅伊艦長本來堅決不同意達爾文參加環球考察。因為他所崇拜的拉法捷爾曾教導說:長著象達爾文這樣鼻子的人是不具備航海所必需的精力和決心的。
再如,達爾文在歸納法的基礎上提出的,他自己也認為“神密的”的所謂“生長相關律”:什麼藍眼睛的純白貓都是,或差不多都是聾子;具有反芻胃的動物同時也一定是偶蹄的動物等等。
現在看來這似乎很可笑,但在當時卻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連恩格斯早先也曾做出過諸如鴨嘴獸那樣的錯誤推論,這就是證明。
我們再來看看達爾文的實驗。
達爾文堅信:所有家養動植物種都與人工選育有關。但是很顯然,人們在選育這些物種的同時也或多或少的改變了它們生存的環境條件。為了比較外部條件的作用與選擇在進化過程中的意義,達爾文作了長期的大量的試驗。比如:直到現在世界上仍有最早由達爾文選育的,並以他的名子命名的觀賞鴿種。正因為這些新鴿種源於其中的普通鴿種在同樣的家養條件下仍是原來的形態;而且,該事實又在許多動植物種的選擇試驗中普遍得到證實。這么一來,達爾文就找到了一根似乎能支撐他的理論體系的擎天柱。
可惜,後人不久就發現:選擇只能在生物原有的品性中進行,新品種不過是原品種中某些品性的積累或擴大。然而在自然界,一物種具有一些祖先物種所不具備的品性卻是一個普遍現象,這又如何解釋呢?
老克利夫蘭認為,這個主要弱點在本世紀初由於基因和染色體的發現變得可以理解了。他說:“基因可以發生突然的、自發的和隨機的變化,這種變化稱為突變…
突變是進化的創造力,自然選擇給它們定了方向。⑤”
可惜的是:這仍然經不住自然界的檢驗。
比如,我們常見的青蛙總是把卵產在水草上,直到蝌蚪變成小青蛙才能離開水;而有一種蛙只把卵產在離水面的植物葉上,等小蝌蚪出來了才掉到水裡去;另外,還有一種熱帶雨蛙,它們一生都不在水裡度過,小蝌蚪直到變成小青蛙才從蛙卵里出來。在這裡,如果用達爾文主義來解釋,那自然是由於它們共同祖先的基因發生了“突然的、自發的和隨機的變化”,當然也由於第二種蛙的生存環境淘汰了第一種蛙,第三種蛙的生存環境也淘汰了第一和第二種蛙。那么反過來說,第二種蛙的生存環境往往也並不存在淘汰第三種蛙的因素;而且,第一種蛙的生存環境往往也並不存在淘汰前兩種蛙的因素;也就是說,如果基因“突然的、自發的和隨機的變化”真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真理的話,那么,在第二種蛙的生存環境裡就至少在多數情況下也應該有第二和第三種蛙的共生現象;而三種蛙共生也就應該是我們常見的現象了。可見,在第二種蛙的生存環境裡,青蛙的祖先並沒有發生向著第三種蛙演化的所謂“基因突變”,同樣,在常見蛙的生存環境裡,蛙的祖先也沒有發生向著第二、第三種蛙演化的“基因突變”。
再比如,現在有很多物植物新品種,特別是出於雜交與基因工程的新品種,它們的優良品性總免不了要逐代退化,無論人們是多么精心地加以選擇也不能扭轉它退化的趨勢。在這裡,基因為什麼就不向著人們所需要的方向再繼續“突變”呢?由此可見,基因的變化至少在通常情況下並不是雜亂無章、“突然”和“隨機”的。
早在達爾文生前就有人提出:家養物種人工選擇的效果總是隨著選擇代數的增加而呈遞減趨勢,如果這表示人工選擇存在著一個極限的話,那么,無論我們做了多少代的選擇試驗,與自然界物種所存在的代數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這樣的選擇試驗又怎能證明自然界的進化過程呢?達爾文卻認為:這個極限是不存在的,因為,那些家養物種在我們以前就存在很久了,而直到現在它們不仍然在變異嗎?
總之,對於現代的科學知識來說,達爾文時代的研究方法有許多都有已顯得很陳舊落後了,我們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以現代的科學知識來要求前人。
實際上,在達爾文以前,人們的選種意識還不同程度地為舊說所抑制,而隨著進化論的傳播,逐漸成為自覺的行動。特別是選種在最初幾代往往效果顯著,這就為達爾文贏得了眾多信徒。然而多年以後,人工選擇的局限越趨明顯的暴露出來,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年沒有被達爾文所重視的孟德爾的遺傳學才受到人們普遍的注意。今天,選擇早不是新品種的主要來源了,雜交與基因工程已遍地開花,這類科學知識也正逐漸進入人們的常識範圍。以上現象也早已隨處可見,實際上,它們每時每該都在否定著達爾文主義。
三,非達爾文主義進化原理
恩格斯早就明確指出:“‘適應與遺傳’用不著選擇和馬爾薩斯主義,也能決定全部進化過程⑥。”現在我們就把這個進化原理簡述如下:
首先,我們縱觀整個動物界,不難發現:各種動物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存活動的方式;動物的等級越低,其生存活動的方式就越簡單、僵化,其內容也越貧乏、單調;各種動物的形態結構和器官的功能等都與它們各自的生存活動方式相吻合;那些生存活動方式又總與它們生存於其中的環境條件相吻合。另一方面,一般地說,越是原始的物種,它們生存於其中的環境條件也越原始,或者這個環境條件的變遷史也越簡單。實際上,這就已經說明了:環境條件的改變迫使生存於其中的生物改變它們生存活動的方式,而正是在這個改變了的活動方式的長期作用下,動物的形態結構等也必然要隨著改變。可是,當年在拉馬克等人看來,根據這個原理,各物種的生存活動方式似乎都應該隨著環境條件的改變而改變,而這與當時大量的觀察、實驗就遠遠不相吻合,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這就因為局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人們還不知道這樣一個事實:世界上並非沒有不在變的物種(達爾文也承認:有些物種經過了漫長的歷史時間,仍然是原來的形態);世界上只是沒有完全不可變的物種;關鍵只是,當時的人們沒有注意到:各物種的穩定性和可塑性也是千差萬別的(請注意:各物種的“穩定性”與“可塑性”是一回事,因為穩定性越強,其可塑性自然越差,反之亦然)。我們不難發現:一般地說,越是古老的物種穩定性越強,而越是年輕的物種可塑性越好。
因此,即使在同一個生態系統內,環境條件的演變對某些物種來說,或許還遠遠不足以威脅到它們原來的生存活動的方式,那么,這些物種就保持原來的生存活動方式不變,當然,它們的種特性也保持不變(這就是達爾文所始終不能明白的,為什麼“有些物種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間,仍然是原來的形態”的原因);而對另外一些物種來說,或許就大超過了它們變異性的範圍,而且當這些物種也不能避開(比如遷徙)時,那么,這些物種就要被淘汰了;只有這樣一些物種,環境條件的演變對它們來說,既越來越嚴重地威脅到它們原來的生存活動方式,卻又在它們的變異性的範圍之內,而且,它們也不能徊避這個演變著的環境,這時它們才不得不逐漸改變自己原來的生存活動方式,以適應環境。正是在這個改變了的生存活動方式的長期作用下,它們的形態結構等也必然要隨著相應的改變了。
這裡,我們先來看這樣一個例子。家貓是肉食性動物,顯然,我們在肉食的範圍內怎么改變它的食物種類,都不會改變家貓的食性;而且,如果一下斷絕了肉食,家貓也就會餓死了。不過,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用在肉食中逐漸增加素食的辦法也是可以訓練家貓完全以素食為生的(現在就有許多養貂戶這樣來節省肉食)。當然,一代兩代是不足以訓練出一個素食“貓”的物種的,但訓練的代數越多,這種訓練就容易,可見這個趨勢不管是多么微弱也總是存在的。當然,這個新物種就不再是貓了。正如專吃竹葉的大熊貓,其祖先不就是雜食性的動物嗎?大概沒有人懷疑大熊貓是一個獨立的物種吧?順便說說,如果說大熊貓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那么,在家貓生存的一般環境裡也並不存在淘汰素食貓的因素,為什麼我們就沒見過或聽說過一隻偶而也願意素食的貓,以至於讓自然選擇能夠發揮作用呢?
再比如,我們要想把熱帶植物直接移栽到北方,這顯然是不會成功的。但是,現在就有許多原產於南方的植物品種,正逐漸的向北方延伸。
相反,原來生長在乾旱或者相當貧瘠地區的野生植物,一般都具有一些能適應其生長地的特殊本領(比如根系特別發達,具有針狀的葉等等;據說野生馬鈴薯不但能獲取空氣中的養份,還具有捕捉昆蟲的本領);而一但得到人類的精心照顧,它們原來的特殊本領也就必然要逐代退化了。
實際上,這就說明了這樣一個遺傳的基本規律:在整個生物進化過程中,那些在生存活動中作用越大的器官與性能(比如人的大腦和手)進化的越快,而那些在生存活動中負作用越大的器官與性能退化的越快(比如人類遠祖的尾骨);有些器官在生存活動中雖然沒有什麼作用了,但也沒有什麼負任用,往往也就殘留在生物機體中了(比如人的盲腸與動耳肌等)。
另外,有遺傳就必有遺傳信息,而且這個遺傳信息也就有可能在遺傳過程中,受到某些外力的直接作用而改變。從前,這個規律完全在人們的意識之外起作用,因此就被認為物種會產生了所謂“突然的、自發的和隨機的”“突變”。然而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對遺傳變異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因此,現在越是那些野生物種聚集的地方,即使從前一直被視為蠻荒之地的處所,也越是被看成了無價的基因寶庫。正因為那些野生物種一般都具有一些特殊的本領,諸如特別能耐旱、耐寒、耐瘠薄;特別能抗風、抗鹽鹼、抗病蟲害等等,而且越是古老的物種它們的這些性能也越穩定;而現在的科學家們已能夠獲取這些野生物種的某些基因,用以創造出他們所需的動植物新品種(比如據報載,現代科學居然還能把動物的基因,比如把魚的耐寒基因移植到蕃茄上)。
由此可見,基因工程本身並不能創造基因。
最後,局限於個人的學識與研究程度這裡還遠不足於給整個生物界的進化主動因作一個結論;但至少就動物界來說,這樣一個結論應該說與馬克思主義的進化觀是基本吻合的:
生存活動才是進化的主動因。
四,討論的意義
或許有人會說,這兩種進化觀並沒有本質區別,適應與遺傳也是自然選擇的題中就有之義,因此也沒有必要區分兩種不同進化觀。的確,連恩格斯也說過:“最近,特別是由於海克爾,自然選擇的觀念擴大了,物種變異被看做適應和遺傳相互任用的結果,同時適應被認為是過程中引起變異的方面,遺傳被認為是過程中保存物種的方面⑦。”
這是因為在當時,沒有自然選擇,適應與遺傳還不能完全解釋全部進化的過程。而且,無論如何,自然選擇也必竟是一種進化觀,它總比獨創論要先進,因此,在反對獨創論的意義上說,這兩種進化觀必竟是同盟的關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才說,“暫且承認‘生存鬥爭’是個公式”。
不用說,自然界存在生存競爭,但是,有競爭也有依存。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達爾文以前,他今天的(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的)⑦信徒們所強調的正是有機界中的和諧的合作,…在達爾文的學說剛剛被承認之後,這些人便立刻到處都只看到鬥爭。⑧”顯然,也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兩種見解在某種狹窄的範圍內是有道理的,然而兩者都同樣是片面的和褊狹的。⑨”
那么,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呢?原來,當時正處在自由資本主義的鼎盛時期,在經濟領域剛剛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新生的資產階級正愁不能在理論上也戰勝封建領主,達爾文及時地為他們送來了自然選擇的進化觀。一時間,那些在自由競爭中僥倖成功的機會主義者和投機家們,以及形形色色的陰謀家、野心家和冒險家們,他們不約而同的都聚集在了進化論的旗幟下:適者生存!這就是當時曾風行一時的口號。更有甚者,當時還曾冒出一個所謂“存在即合理”的反動論調,當即受到恩格斯的嚴厲批判。
現在,進化論與獨創論的鬥爭早已結束,而徹底清除神創論又是自然選擇所不能勝任的了。而且,在許多科學領域,比如考古學與遺傳學,歷來起指導作用的實際上都是“適應與傳”的進化觀而不是自然選擇觀。特別是在人類起源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方面,它不但沒的積極是的意義,而且是極其有害的。比如法西斯主義就是自然選擇發展到極端的一個典型事例,甚至直到今日,法西斯的幽靈仍在西方的夜空中飄蕩;試想,難道我們沒有必要徹底清除法西斯的理論基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