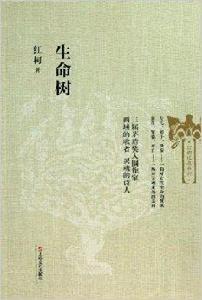內容簡介
《紅柯作品系列:生命樹》寫到了樹,神性的生命樹,還寫到了少數民族神話傳說中的神牛。作者在邊疆遼闊的背景下,嫻熟地運用神話、傳說、歌謠,粗獷恢弘又細膩地描述生命的成長,在日常生活的場景中展開呈現著複雜的人性思考和天地萬物的神性氣象。這種重體驗的日常化視角,可以說是一個內地人對邊疆生命萬象的禮讚,由於紅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對邊疆文化的融入者,而不是傳奇故事的講述者,所以他的小說和邊疆生活之間基本上沒有裂隙,沒有隔膜感。
作者簡介
紅柯,本名楊宏科,1962年生於陝西關中農村,1985年大學畢業,先居新疆奎屯,後居小城寶雞,現執教於陝西師範大學。曾漫遊天山十年,主要作品有“天山系列”長篇小說《西去的騎手》《大河》《烏爾禾》等,中短篇小說集《美麗奴羊》《躍馬天山》《黃金草原》《太陽發芽》《莫合煙》《額爾齊斯河波浪》等,另有幽默荒誕小說《阿斗》《家》《好人難尋》等。曾獲馮牧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中國小說學會獎長篇小說獎、陝西省文藝大獎等。
序言
我曾經是新疆伊犁州技工學校的一名教師,伊犁州真正算得上中亞腹地的一個好地方。有一首歌曲“我們新疆好地方”,不客氣地說,新疆的好地方全在伊犁,伊犁州包括整個西天山的伊犁河谷,南北走向的塔爾巴哈台山脈,中亞與北亞大草原分界處的阿爾泰山脈,即行政劃分的伊犁地區、塔城地區、阿勒泰地區,幾乎全是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糧倉的集中地,伊犁河谷被稱“塞外江南”,跟法國普羅旺斯一樣生長著藍色夢幻般的薰衣草、阿爾泰即是金子與寶石之地,塔城是有名的中亞糧倉。筆者當年剛剛落腳新疆,領導特批一方木料,來自天山西部大森林的白松木,在陝西老家哪見過這么好的木料,散發著伊犁河谷特有的濃烈的清香,一個假期就乾透了,很快就打成家具。我在天山腳下總算安營紮寨有家了。
從我居住的小城奎屯去伊犁有兩條路,一條即烏伊公路,沿天山西行過果子溝;另一條向南走獨庫公路翻越天山達坂,在崇山峻岭中的喬兒馬向西進入伊犁河上源喀什河谷,鞏乃斯河谷,途經唐布拉草原那拉提草原,也是天山最茂密的原始森林帶,包括雲杉,白樺紅樺,野核桃野蘋果等等,其中一棵雲杉即雪松變成我屋裡的家具,途中休息時,我走進陰涼的林中,撫摸一個粗壯的樹樁,可以坐兩三個人,有很深的裂縫,可以插進一隻手,可以感受到來自大地深處的力量。後來我寫過一個短篇《樹樁》,小說的主人公坐在樹樁上下不來了,樹樁冒出了樹液,人跟樹合在一起,長在一起。這條路一年只有七八兩個月可以通行,兇險至極,又奇妙無比。唐布拉草原與那拉提草原,是地球四大最美麗的草原之一,唐布拉蒙古語印章,那拉提蒙古語陽光。蒙古兵征服世界後翻越西天山,凍得直跳,進入那拉提草原,迎來溫暖的陽光,就高呼那拉提。在草原之外,西天山的懸崖陡壁,深溝大壑,常常令人暈眩,驚嘆,盤羊、大頭羊、北山羊、岩羊,傲然立於懸崖絕壁,要不是那一聲聲鳴叫,會誤認為岩石的一部分,而岩嘴上的孤樹給人最初的印象完全是一隻展翅欲飛的蒼鷹,真正的蒼鷹懸於空中一動不動,儼然一棵傲然挺立的樹。奎屯河的上源喬兒馬是這種奇觀異景最集中的地方。我專門寫過短篇小說《喬兒馬》與《雪鳥》寫那些身處絕域的水工團職工。每一次過天山達坂都有一種有去無回的悲壯。2009年夏天剛剛給長篇《生命樹》劃上句號,突然有一個機會來新疆,從伊犁過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可以看見喬兒馬水文站的雪山了,遙望喬兒馬,我百感交涕,喬兒馬有烈士陵園,那裡躺著為修建獨庫公路犧牲的工程兵烈士,從喬兒馬開始的奎屯河上源,先後有七十多位水工團職工殉職。水工團就在我們隔壁,朝夕相處,我生活的奎屯綠洲就靠這條河滋養。
與天賦神境的伊犁阿爾泰不同,奎屯石河子這些墾區都是軍墾戰士們的傑作,先在綠洲邊上建林帶、擋住風沙,才能讓莊稼長起來。執教於技工學校就有機會走遍天山南北。新疆更多的是戈壁沙漠。一上路就是七八個小時十幾個小時,樹就很容易成為一種夢想成為一種精神性的東西。也就很容易理解古代的波斯詩人把他們的經典之作命名為《薔薇園》《果園》《真境花園》。維吾爾人的祖先回鶻人最先居住在蒙古大漠,那個時期的回鶻人在他們的神話傳說里,把自己的祖先當作樹之子,樹窟里誕生了生命,就是他們的祖先。北亞大漠時期的《烏古斯傳》,烏古斯就在樹洞裡發現一位美麗的少女,烏古斯娶少女為妻,生下四個英雄的兒子。在哈薩克柯爾克孜等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詩里,英雄的誕生都有一個共同的開始,老汗王無子,王后去森林祈禱,在林中懷孕,然後生下樹一般高大雄壯的兒子。我們就可以理解成吉思汗成為汗王之前,就在三河之地的不兒罕山下看中了一棵樹,當時就告訴左右,死後以此樹安葬自己。蒙古人的汗王其陵墓也堪稱人間一絕,絕不會跟漢人帝王那樣大興土木費那么大勁安葬自己,蒙古人僅僅用幾丈白布一根圓木掏空,掘土而葬,簡簡單單,明明白白,一如遼闊平坦的大地。生命沒那么複雜,複雜不等於豐富,更多的是蒼白是虛張聲勢。1998年我寫中篇《金色的阿爾泰》時忍不住寫到了樹,寫到了哈斯·哈吉甫的《福樂智慧》,那一刻我才明白從1983年發表處女作用“紅柯”這個筆名到1998年寫《金色的阿爾泰》時,紅柯就是一棵樹,樹上的一根小小的樹枝。那時就有寫《生命樹》的想法。我還是認為那時我的功力寫一根樹枝尚可,寫完整的一棵樹遠遠不夠。
我還記得我在天山腳下第一次聽“生命樹”傳說的情景。這是哈薩克人對宇宙起源的解釋,哈薩克人沒有說這是一棵什麼樹?只說是一棵生命樹,長在地心,每片葉子都有靈魂。從那一刻起,大地上的樹就在我的世界裡不存在了,包括給我做家具的天山雲杉,阿爾泰白樺樹,山嶽般的榆樹,房前屋後的楊樹,大漠深處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爛的胡楊樹,都不符合哈薩克人傳說中的“生命樹”。從地心長出來的這么一棵樹,地球算什麼?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地球是一隻長翅膀的鳥,棲居在生命樹上。地球有生命,有呼吸,有血液,有心跳,我相信古老的夸父追趕太陽至大漠,毛髮化為草木,血流化為河流,筋肉化為泥土,骨頭成為山脈,我相信周穆王一次次地到西域崑崙會西王母,因為周人來自塔里木盆地,用他們在大漠綠洲的種植技術,開發了我的陝西老家岐山,岐山成為周的龍興之地和宗廟所在。周人的偉大母親姜嫄踩巨人腳印懷孕,生下農業神后稷,培育五穀。作為周人之後,在天山腳下遙想《穆天子傳》《山海經》這些漢民族古老的神話傳說,很容易融入準葛爾大地厄魯特蒙古人的大公牛傳說,哈薩克人的生命樹傳說,維吾爾人的少婦麥西來莆尤其是生命樹,哈薩克人以此來接結構宇宙;西北黃土高原的漢族剪紙藝術又以生命樹來揉和松鼠仙鶴鹿猴於一體,包融了整個宇宙天地,那一刻我才明白,先秦那個大時代,也就是《穆天子傳》與《山海經》的世界西域與中原是一體化的,共同的想像力直達宇宙的本源,以至於地球的另一端地中海岸邊的古猶太人也有卡巴拉生命樹的傳說,與在東方的生命樹驚人的一致:即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傳說中的生命樹就成了我的小說《生命樹》的基本框架。絲綢之路東起長安沿秦嶺祁連山天山而行是有道理的:那也是黃河流經之地,山河、山海不就是大地的基本結構嗎?不就是宇宙天地的精神嗎?山河、山海是經,是生命經典,超過三墳五典。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海涅總結莎士比亞戲劇時說:莎士比亞有他的三一律(時間地點情節):同一地點就是整個世界,同一時間就是永遠,同一情節就是人類的活動。絲綢之路不單單是商道還是靈魂之旅精神之旅神話之旅,抒寫人性的目的是探索人性的頂點即神性,沒有人性內在的光芒地球就是一堆垃圾。
我現在居住的西安南郊大雁塔就專門為高僧玄奘而建,在大雁塔南邊還有王寶釧住過的寒窯,在西涼招了駙馬的薛平貴;回長安探望王寶釧,還要耍小心眼兒反覆試探守身如玉的王寶釧。長安當地人另一個傳說:薛平貴壓根就沒有回長安,王寶釧最終在寒窯化成灰。老百姓不忍王家三小姐有如此悲涼的結局,運用民間想像力讓那個負心漢薛平貴衣錦還鄉回長安探寒窯。王寶釧野菜度日十八年,“十八年老了王寶釧”。陝西方言老了即死了。《生命樹》里的伊犁女子李愛琴到小說結尾時的悲壯與淒涼不由得讓我想起寒窯里的王寶釧。2006年剛寫完《烏爾禾》,我就得到一次回新疆的機會。2009年夏天寫完《生命樹》,以伊犁女子李愛琴結尾,一周后我就來到伊犁河畔,看著洶湧的伊犁河波濤,我再次想起李愛琴與丈夫在伊犁的生活,一切如同夢幻。天山—祁連山—秦嶺一脈相承。絲綢之路基本沿山而行。連清真寺也是唐代的長安化覺寺,清代的烏魯木齊陝西大寺,伊犁伊寧市的陝西大寺。清末陝西回民義軍敗退中亞又形成陝西方言為主的東乾人,即黃河東岸子,中原人的意思。陝西方言給整個大西北以至中亞打上了強烈的底色。西域本來就是《烏古斯傳》《江格爾》《瑪拉斯》這些史詩流傳的地方。《生命樹》中的烏蘇與奎屯以奎屯河為界,烏蘇是西域古城,又是蒙古人的草場,烏蘇蒙古人演唱的《江格爾》別具一格,這就是我把《生命樹》的主要場地放在烏蘇的原因。生命樹應該長在亦農亦牧的地方。修改這部書時我不得不把生命樹最終確定為胡楊樹,維吾爾人把胡楊叫托克拉克,意即最美麗的樹。大地上最高的不是山,是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