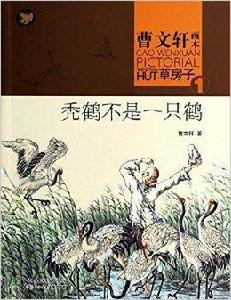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一部值得珍藏一生的經典之作 一部講究品位的少年長篇小說 一部催人淚下、撼動人心的故事 千萬中國兒童的閱讀珍品
作者簡介
曹文軒: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協副主席,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作品集有《憂鬱的田園》《紅葫蘆》《追隨永恆》《甜橙樹》等。長篇小說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紅瓦》《根鳥》《細米》《青銅葵花》《天瓢》以及“大王書”系列和“我的兒子皮卡”系列等。主要學術著作有《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小說門》等。《紅瓦》《草房子》《根鳥》《細米》《青銅葵花》《天瓢》以及一些短篇小說分別被譯為英、法、德、日、韓等文字。獲省部級學術獎、文學獎四十餘種,其中包括中國安徒生獎、國家圖書獎、“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中國圖書獎、宋慶齡兒童文學金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冰心文學獎大獎、金雞獎最佳編劇獎、中國電影華表獎、德黑蘭國際電影節“金蝴蝶”獎等獎項。
圖書目錄
內容簡介
追隨永恆(自序)
《禿鶴不是一隻鶴》正文
曹文軒獲獎作品書目(部分)
經典意象“草房子”:記憶中國童年情感
文摘
桑桑是校長桑喬的兒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國小的校園裡,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國小是一色的草房子。
十幾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規則,又似乎是沒有規則地連成一片。它們分別用作教室、辦公室、老師的宿舍,或活動室、倉庫什麼的。在這些草房子的前後或在這些草房子之間,總有一些安排,或一叢兩叢竹子,或三株兩株薔薇,或一片段預告開得五顏六色的美人蕉,或乾脆就是一小片夾雜著小花的草叢。這些安排,沒有一絲刻意的痕跡,仿佛是這個校園裡原本就是有的,原本就是這個樣子。
這一幢一幢草房子,看上去並不高大,但屋頂大大的,裡面很寬敞。
這種草房子實際上是很貴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麥秸蓋成的,而是從三百里外的海灘上打來的茅草蓋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長在海灘上,受著海風的吹拂與毫無遮擋的陽光的曝曬,一根一根地都長得很有韌性。陽光一照,閃閃發亮如銅絲,海風一吹,竟然能發出金屬般的聲響。用這種草蓋成的房子,是經久不朽的。這裡的富庶人家,都攢下錢來去蓋這種房子。
油麻地國小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很鋪張,比這裡的任何一個人家的選草都嚴格,房頂都厚。因此,油麻地國小的草房子裡,冬天是溫暖的,夏天卻又是涼爽的。
這一幢幢房子,在鄉野純淨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樸來。而當太陽凌空而照時,那房頂上金澤閃閃,又顯出一派華貴來。
桑桑喜歡這些草房子,這既是因為他是草房子裡的學生,又是因為他的家也在這草房子裡。
桑桑就是在這些草房子裡、草房子的前後與四面八方來顯示自己的,來告訴人們“我就是桑桑”的。
桑桑就是桑桑,桑桑與別的孩子不大一樣,這倒不是因為桑桑是校長的兒子,而僅僅只是因為桑桑就是桑桑。
桑桑的異想天開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為,是一貫的。桑桑想到自己有個好住處,他的鴿子卻沒有——他的許多鴿子還只能鑽牆洞過夜或孵小鴿子,心裡就起了憐憫,決心要改善鴿子們的住處。當那天父親與母親都不在家時,他叫來了阿恕與朱小鼓他們幾個,將家中碗櫃裡的碗碟之類的東西統統收拾出來扔在牆角里,然後將這個碗櫃抬了出來,根據他想像中的一個高級鴿籠的樣子,讓阿恕與朱小鼓他們一起動手,用鋸子與斧頭對它大加改造。四條腿沒有必要,鋸了。玻璃門沒有必要,敲了。那碗櫃本來有四層,但每一層都沒有隔板。桑桑就讓阿恕從家裡偷來幾塊板子,將每一層分成了三檔。桑桑算了一下,一層三戶“人家”,四層共能安排十二戶“人家”,覺得自己為鴿子們做了一件大好事,心裡覺得很高尚,自己被自己感動了。
當太陽落下,霞光染紅草房子時,這個大鴿籠已在他和阿恕他們的數次努力之後,穩穩地掛在了牆上。
晚上,母親望著一個殘廢的碗櫃,高高地掛在西牆上成了鴿子們的新家時,她將桑桑拖到家中,關起門來一頓結結實實的揍。
但桑桑不長記性,僅僅相隔十幾天,他又舊病復發。那天,他在河邊玩耍,見有漁船在河上用網打魚,每一網都能打出魚蝦來,就在心裡希望自己也有一張網。但家裡卻並無一張網。桑桑心裡痒痒的,覺得自己非有一張網不可。他在屋裡屋外轉來轉去,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帳。
這明明是蚊帳,但在桑桑的眼中,它分明是一張很不錯的網。
他三下兩下就將蚊帳扯了下來,然後找來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地將蚊帳改制成了一張網,然後又叫來阿恕他們,用竹竿做成網架,撐了一條放鴨的小船,到河上打魚去了。
河兩岸的人都到河邊上來看,問:“桑桑,那網是用什麼做成的?”
桑桑回答:“用蚊帳。”桑桑心裡想:我不用蚊帳又能用什麼呢?
兩岸的人都樂。
女教師溫幼菊擔憂地說:“桑桑,你又要挨打了。”
桑桑突然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但在兩岸那么多感興趣的目光的注視下,他還是很興奮地沉浸在打魚的快樂與衝動里。
中午,母親見到竹籃里有兩三斤魚蝦,問:“哪來的魚蝦?”
桑桑說:“是我打的。”
“你打的?”
“我打的。”
“你用什麼打的?”
“我就這么打的唄。”
母親忙著要做飯,沒心思去仔細考查。中午,一家人高高興興地吃著魚蝦。吃著吃著,母親又起了疑心:“桑桑,你用什麼打來的魚蝦?”
桑桑借著嘴裡正吃著一隻大紅蝦,故意支支吾吾地不說清。
但母親放下筷子不吃,等他將那隻蝦吃完了,又問:“到底用什麼打來的魚蝦?”
桑桑一手托著飯碗,一手抓著筷子,想離開桌子,但母親用不可違抗的口氣說:“你先別離開。你說,你用什麼打的魚蝦?”
桑桑退到了牆角里。
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一邊有滋有味地嚼著蝦,一邊高興得不住地擺動著雙腿,一邊朝桑桑看著:“哥哥用網打的魚。”
母親問:“他哪來的網?”
柳柳說:“用蚊帳做的唄。”
母親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房間裡去。過不多一會兒,母親又走了出來,對著拔腿就跑的桑桑的後背罵了一聲。但母親並沒有追打。
晚上,桑桑回來後,母親也沒有打他。
母親對他的懲罰是:將他的蚊帳摘掉了。而摘掉蚊帳的結果是:他被蚊子叮得渾身上下到處是紅包,左眼紅腫得發亮。
P27-33
後記
經典意象“草房子”:記憶中國童年情感
李利芳(蘭州大學教授,兒童文學博士)
《草房子》首次出版於1997年12月,它已經成為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上的一個經典之作。作品寫了一個男孩“桑桑”六年的小學生活,時空背景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中國南方鄉村。作為跨越了30多年的歷史記憶書寫,曹文軒對這部作品的藝術經營與價值寄寓都是相當用力深刻的。這是一部非常講究品位的少年長篇小說。
《草房子》是中國鄉土童年記憶敘事的典範之作。基於對“兒童文學”構詞中“兒童”與“文學”雙重價值屬性關係的深入思考,曹文軒通過《草房子》賦予了“中國兒童文學”永恆的精神生命與純粹的文化品格。
從形式到內容,《草房子》的藝術內涵構成都非常豐富有機。對它的品鑑與欣賞可以從不同層次、不同維度、不同元素中立體展開,文本為讀者設計了一個巨大的開放的審美體系,值得你去沉潛進入,慢慢咀嚼,升華個人的生命理解。
《草房子》的人物造型很特別。故事的開端從一個很普通但又很不一般的孩子講起,他叫“陸鶴”,但實為“禿鶴”。禿鶴不是一隻鶴,但他常常“鶴立雞群”。不過遺憾的是這並不是因為他的優秀,而是因為他的缺陷。曹文軒寫過很多處於弱勢地位的孩子,他深諳這些孩子孤獨而痛苦的內心世界。
閱讀完這第一個人物的故事,想必讀者已經感悟到了曹文軒筆力的與眾不同。你會強烈地感受到禿鶴是“存在”的,他是一個“尊貴”的個體。“禿”與“鶴”的意義差異極好地生成了這一人物形象的文學表現力,不過支撐其精神性格的主因倒還不在其特殊的外表,而在其挺拔的思想。
序言
追隨永恆
“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動?”這一命題的提出,等於先承認了一個前提:今天的孩子是一個一個的“現在”,他們不同於往日的孩子,是一個新形成的群體。在提出這一命題時,我們是帶了一種歷史的莊嚴感與沉重感的。我們在咀嚼這一短語時,就覺得我們所面對的這個群體,是忽然崛起的,是陌生的,是難以解讀的,從而也是難以接近的。我們甚至感到了一種無奈,一種無法適應的焦慮。
但我對這一命題卻表示懷疑。
作為一般的,或者說是作為一種日常性的說法,我認為這一命題可能是成立的。因為,有目共睹,今天的孩子其生存環境確實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所臨對的世界,已不再是我們從前所面臨的世界;今天的孩子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從生理上,與“昨日的孩子”相比,都起了明顯的變化。
然而,如果我們一旦將它看成是一個抽象性的或者說具有哲學意味的命題提出時,我則認為它是不能成立的。我的觀點很明確——在許多地方,我都發表過這樣的觀點:今天的孩子與昨天的孩子,甚至於與明天的孩子相比,都只能是一樣的,而不會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
我對這樣一個大家樂於談論並從不加懷疑的命題耿耿於懷,並提出疑問,是因為我認為它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它直接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取向、觀察生活的態度、體驗生活的方式乃至我們到底如何來理解“文學”。
遺憾的是,在這短小的篇幅里我根本無法來論證我的觀點。我只能簡單地說出一個結論: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處境,都一如從前;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對人的最底部的結構的預設,因而是永恆的;我們所看到的一切變化,實際上,都只不過是具體情狀和具體方式的改變而已。
由此推論下來,孩子——這些未長大成人的人,首先一點依舊:他們是能夠被感動的。其次:能感動他們的東西無非也還是那些東西——生死離別、游駐聚散、悲憫情懷、厄運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獨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脈脈溫馨和殷殷情愛……總而言之,自有文學以來,無論是抒情的浪漫主義還是寫實的現實主義,它們所用來做“感動”文章的那些東西,依然有效——我們大概也很難再有新的感動招數。
那輪金色的天體,從寂靜無涯的東方升起之時,若非草木,人都會為之動情。而這輪金色的天體,早已存在,而且必將還會與我們人類一起同在。從前的孩子因它而感動過,今天的這些被我們描繪為在現代化情景中變得我們不敢相認的孩子,依然會因它而感動,到明日,那些又不知在什麼情景中存在的孩子,也一定會因它而感動。
“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動?”我們一旦默讀這一短句,就很容易在心理上進行一種邏輯上的連線:只有反映今日孩子的生活,也才能感動今日的孩子。我贊同這樣的強調,但同時我想說:這只能作為對一種生活內容書寫的傾斜,而不能作為一個全稱判斷。感動今世,並非一定要寫今世。“從前”也能感動今世。我們的早已逝去的苦難的童年,一樣能夠感動我們的孩子,而並非一定要在寫他們處在今天的孤獨中,我們表示了同情時,才能感動他們。若“必須寫今天的生活才能感動今天的孩子”能成為一個結論的話,那么豈不是說,從前的一切文學藝術都不再具有感動人的能力因而也就不具有存在的價值了嗎?豈不是說,一個作家十幾年,幾十年乃至一輩子的經驗都不再具有文學素材的意義,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們隨風而去了嗎?
再說,感動今世,未必就是給予簡單的同情。我們並無足夠的見識去判別今日孩子的處境的善惡與優劣。對那些自以為是知音、很隨意地對今天的孩子的處境作是非判斷、濫施同情而博一泡無謂的眼淚的做法,我一直不以為然。感動他們的,應是道義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這一切是永在的。我們何不這樣問一問:當那個曾使現在的孩子感到痛苦的某種具體的處境明日不復存在了呢——肯定會消亡的——你的作品將又如何?還能繼續感動後世嗎?
就作家而言,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一份獨特的絕不會與他人雷同的生活。只要你曾真誠地生活過,只要你又能真誠地寫出來,總會感動人的。你不必為你不熟悉今天的孩子的生活而感到不安(事實上,我們也根本不可能對今天的孩子的生活完全一無所知)。你有你的生活——你最有權利動用的生活,正是與你的命運、與你的愛恨相織一體的生活。動用這樣的生活,是最科學的寫作行為。即使你想完全熟悉今日孩子的生活(而這在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你也應該有你自己的方式——走近的方式、介入的方式、洞察和了悟的方式。我們唯一要記住的是,感動人的那些東西是千古不變的,我們只不過是想看清楚它們是在什麼新的方式下進行的罷了。
追隨永恆——我們應當這樣提醒自己。
曹文軒 1997年4月28日於北京大學燕北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