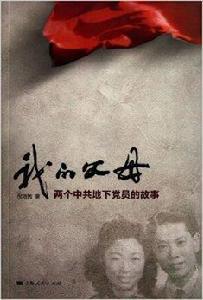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我的父母:兩個中共地下黨員的故事》記錄了倪培明先生父母的愛情故事。
他從一個酒店的拉門小郎和跑堂,成長為中共上海電話公司地下黨的核心人物和工運領袖……
她是著名的“天一閣”藏書樓范家的後代,曾擔任地下黨女支部書記,勇敢機智地與各種敵對勢力交鋒……
他們是兩個普通的中共地下黨員。在那翻天覆地的革命大潮里,這兩朵浪花的故事,也足以映照出一部催人淚下的史詩!
作者簡介
倪培民,1954年生,本書主人公倪復生和江怡之子。文化大革命期間父母受到迫害,從為父母抄寫“交代”、“申訴”而開始對人生、社會感到爨惑,初以文學和書法排遭興情,進而走上哲學之路。“文革”後從上鋼一廠考人大學,先後獲復旦大學哲學學士、碩士,美國康奈迪克大學哲學博士。現任美國格蘭谷州立大學哲學系終身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教學及東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和交流。著有《孔子:人可弘道》等若干中英文哲學著作,個人書法集《筆墨哲思游》及五十餘篇哲學論文。曾先後擔任夏威夷大學及香港大學客座教授、北美中國哲學家協會會長、國際亞洲哲學與比較哲學學會會長,並曾應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特邀在世界公眾論壇“文明對話”等國際會議上作主旨演講。
圖書目錄
代序
前言
第一章 投身革命
第二章 紮根民眾
第三章 嚴峻考驗
第四章 不讓鬚眉
第五章 地火運行
第六章 工會鬥爭
第七章 臨危不懼
第八章 安全撤退
第九章 六次勞大
第十章 迎接勝利
後記
附錄1 大事年表
附錄2 戰友名錄
歷史照片
文摘
倪復生的祖籍應該算是浙江鎮海,可是他從來不知道在鎮海有什麼親戚。聽說他的父親倪慧揚小時候受不了族長的欺凌,打斷了族長老爺的腿骨,隻身逃出鎮海,來到上海,到處打短工。後來,終於在英商會德豐拖駁船洋行找到了一份差事,安下身來。倪慧揚生性倔強,不愛說話。乾起活來,是烏龜摜在門板上——“硬碰硬”,沒日沒夜地乾。為了保住“飯碗”,他又學會了幾句“洋涇浜” (英語),所以被逐漸提升,若干年後當上了拖駁船隊的“老軌”——總輪機長。這個職位不僅給他帶來了一份較為優厚的工資,還不時地可以得到一些“外快”,於是,他在岳州路租了塊地,造起了木板房,娶了妻,生下二男一女,日子過得還不算壞。
1916年,總輪機長又娶了個小老婆鄺惠蓮。1917年的農曆5月22日(公曆7月10日),鄺惠蓮生了個兒子,就是倪復生,小名“毛陀”。
倪復生出生的這個年頭,正是世界風雲變幻的時代。席捲全球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一頁嶄新的歷史,隨著十月革命的爆發,翻開了。一股新鮮的血液,流入了中國這一麻木的泥足巨人的身軀。古老的中國,開始甦醒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席捲著中華大地。童年時代的倪復生並不了解這一切。雖然他也曾和小朋友們一起扛著木棍,排著隊伍,唱著“打倒列強”的歌曲,在小巷裡遊行,但這支歌對他來說只是一首容易上口的兒歌而己。大革命的失敗,也沒有在他的頭腦里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而只是無形中對他的一生起著重大的影響。
一般的人回憶起童年時,都會想到母愛和父愛的溫暖,可是倪福生回憶起童年時,卻只能慘澹地一笑:“我對母愛和父愛缺少體會。”由於外室的地位,他母親在生了毛陀以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和他父親住在一起。總輪機長每個月只給他們一些微薄的生活費,每周來一、二次,有時看看就走了。鄺惠蓮是廣東人,生就一個急躁的脾氣,受不了這種冷落,經常跟丈夫吵吵鬧鬧,可經濟大權畢竟在丈夫手裡,所以最終只好拿兒子出氣。“你這個小浮屍!” 每當不順心時,母親就這樣稱呼他。也許是遺傳的吧,毛陀也天生一副犟脾氣,寧願挨上一頓打罵,一副廣東血統特有的炯炯大眼也從來不肯討饒。不過,母親打他也不全是沒道理的。他記得很清楚,6歲那年,有一次外公病了,母親拿出6個銅板,叫他去買些金銀花送去。他跑到半路上,給賣棉花糖的吸引住了。仗著外公對他的寵愛,他用6個銅板換了棉花糖。回到家裡,撒了個謊,只說已經買了金銀花送去了。沒想到幾天后母親見到外公問起他吃了金銀花後感覺怎樣,外公給問得莫名其妙。結果回到家裡,他被吊在床樑上,著實吃了一頓“生活”(挨了一頓打)。
8歲了,該讀書了,可這么少的生活費,供養他上學有困難。他舅舅來了,說有個“廣肇義學”,是廣東人開的,專收廣東同鄉子弟,不要學費。倪復生從小就跟著母親學會了一口流剃的廣東話,可是廣東人沒有姓倪的,於是他就跟著母親姓了鄺。取了個官名,叫鄺福生,報考了這個學校。所以,他兒時的有些小夥伴(比如後來成了著名話劇演員的喬奇,就是他國小里同班的同學),並不知道他姓倪,只知道他姓鄺,鄺福生,這個名字一直用到他21歲。
廣肇義學與老式的私塾不同,已經帶有一點新式的色彩。學生從小貓三隻四隻讀起,也學點英語。每個星期一早上,全體學生面對國民黨黨旗,背誦“總理遺囑”,不管懂不懂,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眼睛一閉,咿咿哇哇地背誦起來:“余致力於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背完總理遺囑,還要唱國民黨黨歌,“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然後是校長訓話。學校的老師管得很嚴,動輒打罵學生。福生的學習成績並不算壞,可有時也免不了被老師的藤條抽得手心紅腫。
學校離家很遠,他每天早上做完家務,就去上學了。帶著12個銅板,可買一碗陽春麵,作為午餐。放學回家,就背起弟弟,用廣東背孩子用的布背兜在胸前一紮,騰出兩個手做晚飯。這時候,他母親一般是在鄰居家裡打麻將。
自從生了他以後,母親又先後生了12個孩子,可是最終只活下來4個。他回憶說:“當時白喉病流行,好幾個弟妹都死於這個病,家裡常常一口口小白皮棺材抬出去。記得我的弟弟承基(原名福基)生下來的那一天,剛剛死了一個弟弟,小屍體還躺在家裡。我舅舅一個星期裡面死掉三個孩子,都是死於白喉。媽媽心裡當然不好受,怪來怪去,又怪到我頭上。'都是你!你這個老大屬蛇,弟弟妹妹都叫你這條毒蛇咬死了。'弟弟承基屬虎,媽媽說,'不行,將來你們兩個在一起龍虎相鬥,他又要給你咬死的!'就這樣,承基生下來就過繼給了一家姓周的去撫養。後來,因為沒有女兒,母親就領了個小姑娘,那就是我的乾妹倪福珍。”
在學校有嚴師管束,在家裡又得不到母親的慈愛,使他養成了一種孤僻的性格。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爭結束後,他們搬到了岳州路,和他父親住在一起。在那裡,大母所生的幾個兄弟都看不起他,粗活重活都叫他乾。每天清早起來,就要劈一大堆柴,然後給弟妹洗尿布、燒早飯。這種生活,使他幼小的心靈中滋長起一股反抗的力量。“一定要爭口氣!”他學會了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寧肯吃苦,受委屈,也不求人。只有晚上,當他獨自一人躲進自己的小閣樓時,他才感到有了自由的天地。
這個只有五六個平方米的小閣樓靠著正房背面,門開在地板上,從後院的一個活動小梯子爬上去,托起閣樓地板就可以出入了。抽掉梯子,根本看不出上面有個小房間。閣樓有兩扇窗,一扇就面臨後院。院子裡有兩個原屋主的墳堆,還有兩棵並立的大樹。他在樹上擱了一根鐵條,作為單槓。另一扇窗外面是一片屋頂。這裡的每片瓦片下面都是他藏東西的地方。後院還有一個邊門可通到隔壁一家小工廠。他常在晚上從這小門裡不聲不響地溜出去找小朋友們打桌球玩,一直玩到很晚,才又悄悄地從這小門裡溜回。這些“偷”來的娛樂,在他苦惱的生活中,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因此,儘管這個閣樓很窄小,隔壁那家小工廠的馬達聲日夜轟鬧,震得樓板都顫動,又是冬涼夏曖,夏天蚊子滿身亂咬,冬天雪花紛紛揚揚飄進屋來,可他還是喜歡它。這裡沒有兄姐們的歧視,也沒有父母的斥罵,這是一小片屬於他自己的自由天地。
1931年8月,老輪機長失業了,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斷了,15歲的福生不得不輟學,自己謀生了。
記不起是誰介紹的,他進了一個洗染店當學徒。白天用粗大的板刷刷衣服,整天地刷,肥皂水浸得雙手發了白,幾天下來,手臂酸得抬都抬不起了。晚上,老闆就讓他睡在櫃檯底下,隨便抓點東西蓋蓋。做了兩個月,人瘦了,兩條大腿長滿了癩疥瘡,眼眶陷得深深的。他舅舅看不過去,說:“別幹了,先跟我到碼頭上跑腿去吧,以後再另找個好一點的生意(工作)。”
他舅舅鄺惠振,在大英輪船公司當報關員。,福生跟著他跑跑腿,到海關、商品檢驗站等處核對、蓋戳,在碼頭上收收籌碼,每個星期從舅舅那裡拿六角錢零用。這已經比在洗染店當學徒強多了。就用這六角錢,他買了些書本雜誌,繼續自學文化。
可是,一直靠舅舅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想到這個,他心裡自然十分焦急,所以,他常常獨自跑到大陸商場圖書館(即後來的南京東路新華書店)去看報紙上的招聘欄。
1934年10月份的一天,岳州路13l號(即今129弄2號)來了一封印有“新亞大酒店”紅字的信,信封上赫然寫著“鄺福生先生”的字樣。他媽媽拿到這封信,始則一愣,繼則破口大罵:“小浮屍!滾出來!你在外面吃了飯,欠了債,人家討債來了!”
福生給罵得莫明其妙,拿過信來一看,哈哈大笑起來,“媽,不是討債,是我考進了!”
原來,他偶爾在大陸商場的招聘欄里看到新亞酒店招收boy(侍員)的啟示,啟示上寫明,凡具國小文化水平,會簡單英語會話及廣東話、上海話、國語對白(即國語),且眉目端正者,均可報考。福生自忖條件適當,試了一下,想不到果然錄取了。
他喜孜孜拿著貼子來到新亞酒店,當上了拉門小郎——專門在大門口給客人拉門的boy。以後,又先後調到西餐問、中餐間,最後調到樓上侍候包廂,照現在的說法,也算是個“上手”了吧。直到晚年,他還可以穩穩噹噹地一手托上一個盤子,一手抓起五個杯子,逢年過節時偶爾給子女們露一手。
差事(工作)變了,薪水略多了一些,福生在家裡的地位也上升了,長兄們不敢隨意欺侮他了。他自己更是處處好勝,要在家裡爭口氣。那年他大母死了(1937年春),父親把他和大母所生的兩個兒子叫到跟前,說:“現在我失業了,這個喪事你們兄弟幾個包下來。各人出多少錢,自己報。”
福生沒有多加思索,咬咬牙,拍拍胸脯說:“我出一百塊大洋!”
兩個異母兄弟一聽,傻了眼了,只得硬著頭皮也報了一百。後來事實上他們倆個都是靠變賣家裡的財產來交差的。只有福生,到酒店裡借了一百元,在工資里扣了好幾個月才還清了債務。但是從此以後,那兩個兄弟再不敢小看他了。P13-17
後記
我們的故事其實只講了一半。故事中這兩位普通的共產黨員的道路並沒有走完。
解放後,他們都當了領導幹部。職位不是很高,但工作一直很忙。
他們後來想要個女兒,結果卻一連生了三個都是兒子。老二叫小培,老三叫幼培,等最後一個兒子出生,想不出其他形容“小”的好字眼了,乾脆把前三個兒子的名字都改了,在“培”字後面給他們各加上了“中華人民”四個字,叫培中、培華、培人、培民。
在解放後的最初十年里,他們主要搞工會工作,參加了三年國民經濟恢復工作,參加了民主改革,搞過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時,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六十年代初,他們先後離開工會,在工交系統行政管理崗位上,為發展上海的工業交通,灑過無數汗水,熬過無數通宵。那些年裡,他們很少有和孩子親熱的機會。幾個孩子都是外婆和保姆一起帶大的。
正像在解放前他們沒有一帆風順一樣,在解放後,他們也遇到過不少曲折。由於地下黨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的“戰功”沒法用“消滅”了多少敵人那樣的方式來明確地計量,他們的對敵鬥爭,也不可能像在戰場上那樣壁壘分明,而常常需要利用“合法”的和社會上通行的(包括結拜兄弟、甚至對敵人行賄等等)手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展開工作,所以地下黨的幹部在解放後大多數都因為“歷史複雜”而未能得到充分的信任和重用。倪復生的脾氣耿直,對下級他是關懷、愛護、寬容,對上級則從來不肯奉承或者報功。他很多年都沒有得到提升。江怡憑著她年輕能幹,又是女性,很快被提升到和倪復生一樣的級別——行政十三級,享受了所謂高幹的待遇,但也長期做著辦公室的事務性工作。他們一直很低調,從來不讓自己孩子有幹部子弟的意識。為此,他們還特地把居所選擇在黃浦區一般市民的里弄里,而不是高幹集聚的地區,並要求全家都把保姆看作自己家庭的一員,不得有任何歧視。雖然身居領導崗位多年,他們兩人都從來沒有學會官場裡的習氣,只知道黨把他們放在哪裡,就在哪裡勤勤懇懇地工作。
曾經和他們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戰友們,1949年後有的依然在上海,平時常有來往,有的則被安排到外地工作,難得見上一面。和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又成了“羅培”和“小范”,總有說不完的話,親密得像是兄弟姐妹。當年他們當中的“高級知識分子”陸文達,後來當了上海市房地產局副局長,自己家長期住在桃園路一個不大的老式公寓裡,里永遠堆滿了各種書籍。雖然他知識面很廣,還頗得書法和圍棋的妙趣,他晚年卻把自己的才智都投入到了《上海房地產志》的主編工作上了。陸文達的妻子、江怡的入黨介紹人鄭少如,曾在上海公用事業局擔任辦公室主任。她那淡泊祥和的姿態,絲毫不會讓人聯想到電影小說里地下黨女英雄的形象。當年在籌組電話公司工會鬥爭中和江怡一起站在第一線的劉勵方,1949~N曾擔任過上話工會黨組書記、工會主席,後來又擔任了中共上海市市內電話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但在孩子們的眼裡,她永遠是他們親切的“勵方阿姨”。她的丈夫、當了上海長寧區副區長的“小蘇”(馬四方、蘇湮池),來去都是一輛“老坦克”。他飛身躍上車子瀟灑而去的身影,還透露著當年在鐵路上當地下交通時的英姿。他們的地下黨老上級錢正心,解放後曾任上海出版印刷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永安第三棉紡織廠黨委書記、廠長,中共靜安區委常委、統戰部長等職。他那矮小的身材,永遠顯得過長的棉布上衣,一副厚得像啤酒瓶底的眼鏡,憨厚的笑容,配上他在上海老式石窟門裡弄的那十幾平房米的居所,使他依然屬於“掉在人堆里就找不到了”的“地下黨”。
倪復生的大弟弟周承基後來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從部隊轉業以後,他被安排在安徽合肥工作,但舉手投足,依然是一派軍人的作風。雖然他給自己的四個兒女起名“燕、飛、南、方”,最後卻還是沒能回到上海,在合肥鋁廠廠長的職位上退下來離了休。那“新四軍”的情結永遠伴隨著他,似乎只要他的老首長一聲召喚,他就會“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江怡的三個弟弟,後來都當了領導幹部。范仁良從當年陳渭南擺過的報攤上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後長期在出版系統工作,曾擔任上海美術出版社副社長。范仁珊解放後考入上海電話公司工作,曾任公司工會常委、宣傳委員會主任,後調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幹事。文革以後他曾任中共上海靜安區蠶宣傳部副部長、區委黨校校長。江怡最小的弟弟范仁風,解放後讀了高中,後來一直從事教育行政工作,曾擔任中學校長多年。在他們的心目中,姐姐姐夫永遠是他們的榜樣,是他們家族和精神的核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和許許多多這樣的共產黨員一樣,倪復生和江怡也挨了整,被“靠邊”、。“打倒”、抄了家。先是“走資派”,後是“叛徒”,再是“特務”,一頂頂帽子不由分說地套到了他們的頭上。他們像罪犯一樣被造反派押上台去,掛上牌子,九十度彎腰,接受批鬥。他們被關進“隔離室”,長期不準與家人見面,受盡了種種屈辱和令人髮指的殘酷刑罰。他們被驅趕到五七幹校,關進“牛棚”,。每天在看守人員的押解下做苦役犯的重活。他們的培培(培中)由於在就讀的學校里為父母的遭遇抱不平和“抨擊中央首長”(江青),被打成反動學生。另外幾個兒子和他們的弟弟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株連。他們的“阿姆”,那位可敬的老人,幾乎被逼瘋,每天呆呆地站在電車站,等女兒女婿回來。與他們一起出生入死過的地下黨的戰友們,也紛紛受到衝擊,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不過也正是因為文革,他們的歷史被兜底翻地審查了一遍又一遍,我們這本回憶錄里的好多資料,不僅得以在那時被“翻”了出來,而且得到了反覆的核實。總算, “四人幫”被粉碎了,文革中對他們的各種誣陷被確定為冤案,得到了平反,他們第二次獲得了“解放”。他們的阿姆盼到了這一天,含笑離世。1978年5月,倪復生調任交通部上海航道局副局長。1979年4月,江怡出任上海市儀表局黨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1982年她又被調任中共上海市委人事安排小組工作,為黨和國家選拔了一大批優秀的高層幹部。這些幹部後來都擔當了重要的領導崗位,有的還進入了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其中絕大部分都經受住了改革開放的考驗。但是,自然規律不饒人。這時的他們,再也不像解放初期那樣雄姿英發,也不像六十年代初那樣精力充沛了。頭髮已經斑白,精力已經衰退,各種疾病也紛紛出現了。他們壯心猶在,但漸感力不從心了。倪復生在1983年11月開始離休,江怡則在晚年還擔任了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辦公室的領導工作,為收集、整理黨史資料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98年11月6日和1999年8月24日,江怡和倪復生先後在上海華東醫院去世。這後面幾十年,也有許多可以令人感動嘆息的故事,待以後有餘暇時,整理出來,再作為本書的下篇吧。
序言
光陰如梭。曾經對我呵護有加的倪復生(倪福生)伯伯和江怡(范夢青)阿姨已經離開多年了。如今,連我自己的孩子也已越過了需要大人呵護的年齡。然而打開培民《我的父母》的手稿,隨著一個個從小耳熟能詳的姓名映入眼帘,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物似乎頓時出現在我的身邊。“文革”後期替父母“平反”的奔忙之中,我曾經多次探訪與這些名字連在一起的長輩,接受他們的關愛和幫助,那歲寒之後遇和煦春風般的時光永生難忘。
1979年,趁著“文革”中接受“審查”時被“翻淘”起來的記憶尚還清晰,兩名曾經的中共上海電話局地下黨黨員——倪復生和江怡夫婦,決定把他們一生的經歷記下來,傳下去。他們向兒子倪培民一次次地口述自己的回憶,還多次約來老同事、老朋友一起核對和補充事實。本書就是倪培民根據當時記錄整理的他父母1950年以前生活的傳記。
兩位傳主出生在上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上海,他們的父母是上海早年來自浙江和廣東的“移民”,是現代意義上最早的中國工人。江怡的父親和叔父,曾是1925年五卅運動的積極參加者。“八一三”淞滬會戰上海淪陷後,22歲的倪復生和14歲的江怡,先後考進美商上海電話公司成為接線員。當時,倪復生已經在尋找抗日門路時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很快便擔當起了在公司里重建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重任。而為求生計虛報4歲才得到飯碗的江怡,純樸正直、上進心強,很自然地接近並加入了了地下黨。倪、江在並肩工作中建立起感情,結為伴侶。十載荏苒,他們和地下黨戰友一起,宣傳抗日,發動捐款;為改善工人生活條件與資本家鬥爭;演出話劇、出版刊物、舉辦活動,團結教育民眾。在白色恐怖中生活、工作,他們幾度出生入死,命懸一線。1947年10月,倪、江奉命撤退到解放區。1949年解放全國期間,他們參與了北平和天津郵電系統的接管工作;江怡還被派往歐洲參加世界工聯第二次代表大會和世界青年第二次代表大會。解放後,倪、江回到上海,年輕的地下黨員從此成為新上海建設的領導者。
倪復生和江怡囑兒子記下這一切當然不只是為了自己的後代,而更是要給社會留下一篇信史,一篇有血有肉、有情有意,別具一格的信史。
由於記下的都是兩位傳主親身的所作所為、所見所聞,書中所敘史實有一般史料中難以見到的豐富真實的細節。比如當時在電話工人中引起關注的倪復生被日本人逮捕事件:倪因自己的疏忽而和暗號紙一起意外落入敵掌時的痛悔,關在憲兵隊當夜巧用電話把訊息通知黨組織後的釋然,57個日日夜夜裡所經受的種種酷刑,靠堅強和機智與敵人多次有驚無險的周旋,出獄後將“福生”更名“復生”那一刻的百感交集,都一一躍然紙上。又如抗戰勝利前夕江怡和地下黨戰友在電話局大樓散發《新四軍賀年卡》事件:趁凌晨夜班中的休息時問,兩個“小姑娘”溜出休息室,來到大樓一層層空寂的走廊里,輕輕地用腳尖將“賀年卡”從門縫底下撥進每一個房間。第二天早上,前來上班的日本人發現了“賀年卡”立即動手組織搜捕。而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江怡對此渾然不覺,還提著裝有剩餘賀卡的提包,在下樓的途中發掉了最後幾張,幸運地在敵人關門搜捕的前一剎那離開了公司……類似的例子書中俯拾即是。這些細節在在透露出當時上海電話局地下黨人勇敢、堅定,在成功和挫敗交織著的歷練中從單純幼稚走向成熟老練的風貌,以及他們當時身處的真實環境,是我們從其他僅作事實陳述的史料中無法體會到的。
倪復生和江怡顯然從一開始就決定以他們的“個人傳記”為基礎,托起一座上海電話公司地下黨的“群像”。他們盡搜記憶,列舉出上百個真名實姓的人物。書中記錄的活動之參與者既有劉寧一、李立三等共產黨高級幹部,更有許許多多名不見經傳的普通民眾和普通黨員。
倪、江特別留意記下那些在革命潮流中僅僅得以短暫存在的人物。倪復生的政治啟蒙人陳君博只是一名共青團員,他在大革命失敗後失去了組織關係,卻執著地堅持“從報紙上、書上尋找黨的指示,確定自己的活動方向”。陳引導倪認識了共產黨以後,有事回了廣東老家從此杳無音信。倪的入黨介紹人李小里、江的政治啟蒙人陳偉和林海倫,都不久便失去了聯繫,多年後輾轉打聽到的,竟是他們犧牲了的訊息。“在那血雨腥風的日子裡,有多少人就默默無聞地死了,為了革命,為了國家,他(她)們不知葬身在哪一棵樹下,哪一塊石邊了,甚至連姓名都沒留下。”這本書里不僅記下了許多類似人物的名字,還生動地展現了他們當時的舉止言行,即使只有一場對話抑或幾十個字的描寫,都因著真情的回憶而使那些光彩的生命瞬間永遠定格下來。
倪、江、電話公司地下黨主要的直接領導錢正心,戰友陸文達、鄭少如、劉麗芳(劉勵方,我母親)、盧雙文、方秀雲、何馥麟、吳寶琳、蘇湮池(馬四方,我父親)、陳啟瑞、吳炯明……還有許許多多進步民眾和積極分子,更都是這本傳記的“共同傳主”。他們大多和當時的倪、江一樣,曲身貧困,在抗日戰爭期間加入或接近共產黨。中共地下黨除當今影視節目中常見的“情報系統”,還有“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等系統。電話局地下黨屬於後者,其主要的工作,是團結和教育民眾,與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家和國民黨鬥爭。電話公司的這批青年工人之所以被共產黨所吸引,甚至願意為其獻身,是因為他們確信共產黨的事業是為窮人、為社會大多數人謀福利的事業。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年輕的共產黨員們度過了他們傳奇般的青春。國難當頭之日,他們選擇挺身而出;忠孝難全之時,他們選擇精忠報國。他們所忠於的,正是流淌在我們民族血液里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覺悟,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如今他們雖然多已作古,卻將因為本書而得以更長久地活在後代的心裡。
本書的作者倪培民繼承了先輩的責任感和情懷。身為美國大學的一個全職哲學教授,用業餘時問傾力把幾十年前的記錄整理成書出版,所花的心力、心血,非他人能夠想像。過去,書是要“傳世”的,書應該要活得比作者更長。現在,由於文字普及、出版便捷等原因,這種傳統正遭到顛覆,許多人編書、“做”書、只為當下的一次性消費。“新生事物”固然不可厚非,但是也總需要有一些人把傳統繼承下去。據我理解,培民寫這本書的目的有兩層。一是為倪伯伯江阿姨立傳,留給家族的後人,這是“盡孝”。二是通過為父母立傳而為他們生活的時代立傳,留給世人,這是“盡大孝”。二者都可敬、可佩。本書出版,倪伯伯江阿姨和他們已故的戰友們,當九泉含笑,他們那些依然健在的戰友們,更當感到由衷的欣慰。
最後忍不住還想添幾句“多餘的話”,說出自己對培民寫作的一點偏愛。在為父母和他們的戰友記下這段信史的同時,培民還為我們描畫了一幅上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上海一帶社會風情的長卷。展讀“畫卷”我們看到:那所為同鄉子弟辦的 “廣肇義學”里,學童們搖頭晃腦地大聲背誦著“小貓三隻四隻”和《總理遺囑》;羊腸般的小巷深處,一幢老式磚木結構房子的客堂背後,端端正正地掛著一張長長的照片,那是房問的男主人和工友們在參加五卅運動失敗後的合影;日本憲兵隊電刑刑具旁,良心未泯的中國翻譯趁人不注意,突然做出兩個手腕交叉的動作,把減輕痛苦的方法暗示受刑人;一座紙醉金迷的舞廳里,放著軟綿綿的音樂,唱著“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舞廳樓上,幾個青年靜靜地坐在那裡讀著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小年夜傍晚的靜安寺寫路上熙熙攘攘,熱鬧非凡,人群中穿行著專偷拎包的小“癟三”;長江水道上航行著槳劃纖拉的小船,一位生意人橫臥在小船內倉,著一身綢衫褲、戴一副茶色鏡,手搖摺扇,悠悠地盤算著賣給蘇中解放區的那批西藥的利潤……是啊,歷史的長河波瀾壯闊,但並不清澈。就連本書中這些曾經為革命出生入死的共產黨員,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竟都成了“革命”的對象。然而,“事業文章,隨身銷毀,而精神萬古如新;功名富貴,逐世轉移,而氣節千載一日。”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就是有一種精神,一種氣節,貫穿始終。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是倪復生在獄中默誦過無數遍的詩句。上海電話局地下黨黨員們當然知道自己未必能夠像文天祥那樣名垂千古。然而他們從文天祥那裡繼承的一片丹心,卻一定還會世世代代地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