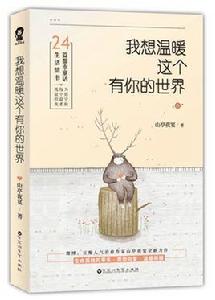內容簡介
夜幕落下,霓虹滿街。
靜謐的小巷深處,隱藏著一間遠近聞名的小食堂。
這裡除了美味的食物,還匯集了光怪陸離的都市童話。
隱秘而苦澀的暗戀,虛幻與執著的理想,疏離卻牽絆的親情……
所有迷茫與痛苦,歡喜與思念,都在縷縷馨香中,化作點點溫暖鐫刻於心。
一盞深巷暖燈,一縷紅塵煙火,守護這世間最美好的溫暖。
或許還未遇見,或許將要離開,
我想溫暖這個有你的世界,
無論你在哪裡,當夜幕落下,星辰睡去,還有我的溫暖陪你。
作者簡介
山亭夜宴,2006年至今在雜誌上發表各類短篇小說,擅長撰寫社科文藝等文章,以及各類小說稿。曾在《南風》《中華傳奇》《愛客》《微言情》等雜誌發表作品。已出版作品:《唯愛與美食不可辜負》《暗戀古董衣》《如花美眷,終不敵逝水流年》《宋朝娛樂頻道》《那些細碎卻美好的時光》等。
媒體書評
合上書,我想著生活中各種細碎的事,有些欣喜,有些遺憾,很日常。從前喜歡追逐驚天動地的故事,現在更關心與生活有關的事,可見人的想法真的變化很大。大概人到了某個時候,看過足夠的風景,經歷過一些事,遠方啊還是附近啊,差別不大。我喜歡到處尋找一家安靜的小店,會餐會友還很安靜,就像書里的人,喜怒哀樂全是生活。
——葉婷婷
每個憂傷的人都有著孤獨寂寞的靈魂,只有在夜晚才能卸下偽裝,讓靈魂安靜而自由地綻放。二十多個溫暖的情感故事,是一個個與深夜有關的都市童話,也是獻給那個孤獨的自己的生活情書。這裡有最治癒的美食,最有趣的故事,和最深情溫暖的相遇。今夜,願你遇到溫暖的人,陪你枕星光入眠。
——七月七日下雪天
總想在不經意間,邂逅這樣一間溫馨的小店,在這裡,會有一盞燈溫暖你的整個夜晚,也會有一個喜歡聆聽你的人,溫暖你的整個世界。有時候,心就像一座孤獨的花園,總有一天,我們會衝破時間的孤傲,與所有溫暖不期而遇。
——小張扒
目錄
夜的第一章
深夜報社食堂
從此孤獨愈演愈烈
深夜的高跟鞋
鬢邊不是蝶戀花
七月十五日夜渡河
幽夜裡的名姝
月的第二章
紅霧濕人衣
未必是西風
喝了口貌似寡淡的湯
月影花蔭
不成歡笑不成哭
蠟梅朵朵,為誰綻放
燭的第三章
玫瑰與綢緞的房間
斜風細雨不須歸
橫笛簪花
葉茱萸的二三事
他的夢魘
閒者的小謊言
星的第四章
亂摘黃花插滿頭
林下有酒
故園春色如許
水浮花輕
相思是苦藥
守夜人的藍莓酒
精彩文摘
灰泥牆上的一株小花,雨後的露水,布滿爬山虎的矮樹籬笆,小河對面的人家在陽台上曬棉被,白色被單掛滿陽台,兩個小孩趁機上來搗亂,大人追著趕他們下樓。
思凡有天晚上問我,幾時有空陪她去拍外景。我好奇,以為她被星探選中,從此當上大明星。結果不是,她一個做手工飾品的好友邀她去玩,買了台二手單眼專門用來拍照,找思凡做模特,順便玩幾天。
她積攢了一年的假期正好用上,報社食堂相聚的人少了,大家也漸漸不高興去了,好像每個人都忙了起來,剩下自己還是老樣子,實在不好意思。
人來人去,緣聚緣散。
趁著小長假來臨之前,思凡與我在火車站見面,她帶了一堆衣飾,拖著個小行李箱,我背著筆記本,出發去度假。
火車上人不多,假期前難得的清靜。思凡說她最近剛搬家,交通比以前方便,周邊環境也很熱鬧,卻也因此而不得安寧,下樓買個咖啡也要排半天的隊伍,從前她會穿著拖鞋睡衣晚上去買個優酪乳,現在只要想到下樓就開始頭疼,擠在一堆時尚潮男潮女之間,她連出門扔個垃圾也要掙扎半天。
“你怕什麼呢?”我笑著問她。
“在別人的自拍里成了奇葩,反面教材。”思凡懊惱地搖著頭說。
她不是不修邊幅的人,她喜歡精緻漂亮的事物,但不會因此而要求樣樣做到完美,發在朋友圈裡的照片,心情特別好時才會想起來修一修。她說:“我不需要向別人證明安全感,生活是粗糲的。”她頭上的蝶戀花髮簪閃了閃,掉了一顆珠子。
她說,那個人來找她了。
潘生年長思凡兩歲,兩人學戲時結識,他留學歸來成了一名律師,看望年幼時的恩師時兩人又遇見了。
她喜歡的男生與她最好朋友在一起,這世界上最爛俗的橋段每天都在上演,隨時隨地發生在身邊,上演了千萬遍的三角戀無法滿足人們對愛情的渴望。
再次見面的兩人,他穿著一身休閒西裝,頭髮打理得一絲不苟,幹練、帥氣,每個見過他的人都要替他介紹女朋友。他微笑有禮貌地婉拒,實在被問得緊迫了,他才說:“我有未婚妻。”說話時,眼神看著思凡。她轉過臉去,裝作不認識他。
這么多年了,哪種結局她都猜想過,她最好朋友成了他的未婚妻,她卻直到他歸國才知道,不知是她實在遲鈍,還是她一廂情願,她只覺臉上火辣辣的,像被人當面抽了一個耳光。
潘生走上前與她打招呼,思凡不看他,像在賭氣,她明知很可笑卻實在忍不住,總不能當著他的面哭,鬧又不成,他們之間從未開始,她連生氣的權力也沒有。
“你好嗎?”他問。
“嗯。”她答。
“還住在原來的地方?”
“嗯。”
“改天一起吃飯。”
她沒應聲,這樣太小家子氣,旁人看著更像鬧彆扭。她含糊地喔了一聲,他沒有再問,很快被人喊去說話。很多人等著與他說話,不僅因為他是留學歸來的律師,年輕有為,他家庭條件出眾,父母都是醫生。潘生一走進房間,每個人都想認識他。
思凡閒聊了一會兒後,便推說有事先離開,恩師留她吃了飯再走,她找了個藉口便開溜了。她看到最好朋友的車停在拐角,她從另一條巷子落荒而逃,像是被撞破的第三者,她只有鬼鬼祟祟地跑。她邊跑邊哭,罵自己蠢,蠢了那么多年,誰會像她這么不切實際,潘生這樣的人怎么可能會單身,他從前長相俊美,成年後英氣逼人,他父母一定很驕傲,生了個這么優秀的兒子。
忽然,她被人一把拉住,她嚇了一跳,抬頭一看是潘生,他像個生氣的蠟像站在她面前,眼神充滿責怪的意味。從前,他總是嘲笑她粗心大意,記不住唱詞,貪吃愛偷懶,他記住的全是她的缺點。
她甩開他的手,她穿著一身過時的套裙,腳上一雙平底鞋,整個人比他矮了一個頭,氣勢輸了一大截。出門時,她化了淡妝,現在一定也成了小花臉,又不是在唱戲,這么“濃墨重彩”給誰看?她越想越氣,只要是關於他的事,沒有一件能讓她心平氣和。
潘生做了個停戰的手勢,解釋了他沒有來找她的原因。
她打斷道:“你忙你的,不用告訴我,本來也不熟。還有啊,你不要當著這么多人的面跑來跟我說話,他們年紀大,朋友圈不會玩,但看熱鬧還是會的。”他笑了,笑得很開心,她生氣時會妙語如珠,與她平時的羞澀截然相反,要是他再逗她,她會立刻變得咄咄逼人。
巷子外響起了汽車鳴笛聲,思凡神情不悅,好囂張的氣勢,居民區內也這樣按喇叭。潘生聽了也皺了皺眉頭,說:“一起吃頓飯怎么樣?”
她想了想,終於點頭。兩人慾言又止地道別後,他走了。懊惱隨之而來,她開始時不時地看著手機發愣,他加她的微信好友,她還沒點同意,他缺席了那么久,難道就憑他一句話,兩人就能成為不時看看對方過得怎樣的朋友?誰都知道朋友圈的生活秀,她總不能因為他一個人,裝個濾鏡展示自己,要是同意加了,她可不敢保證以後會不會。
她想來想去,最糟糕的感覺是讓他知道,沒有他,她還是老樣子。
兩人還未約定見面的時間,不巧地在報社食堂附近的百貨公司撞見,思凡驚得掉頭就走,卻又在食堂看到潘生與未婚妻電影散場後一起買飲料的情形。
思凡覺得自己早過了還會為此生氣的年齡,她不是十幾、二十歲的小女生,公司為了節約出差開支,她經常一個人出差,在人生地不熟的工作環境,盯工程、跟進度。家裡急得不得了,一去一兩個月,她母親在電話里尖叫著要她辭職嫁人,給她安排了條件優渥的結婚對象。她看過照片,依稀記得在某個酒宴中見過一面,肥頭大耳的男人,是三姑六婆眼中最合適的丈夫人選,主要就是會賺錢,脾氣不太好,找個溫順的女孩生個兒子,以後不用工作,專心相夫教子。她聽得胃裡翻江倒海,餐桌上的海鮮大餐都像從臭水溝里挖出來的,她藉口失陪,跑去洗手間乾嘔。
沒多久,說媒的人跟她母親說,“當初你女兒看不上人家,現在人家結婚了,生了個兒子,女方一結婚辭了工作在家帶孩子,日子過得滋潤啊……”她母親表面上滿不在乎,掛了電話便數落她,吃飯時問她:“你以後怎么辦,我是要老要死的……”
大學畢業後,她母親便開始張羅她的婚事,現在工作了這么多年,別說結婚,連個交往對象也沒有,反倒規矩得像個天天參加高考的學生?
思凡一氣之下主動申請去跟項目,一個人在北京待了半年多。她大學同學有幾個在北京打拚,日子過得自由自在,要不是項目結束,公司調她回來管理新部門,她已經打算在北京的分公司一直工作下去。
潘生出差去北京時,打電話約她見面,思凡輾轉地知道他和未婚妻的婚事延後了半年,本該籌備婚禮,又遲遲不見動靜。她猜到了兩人有事發生,她同學撂狠話給她:“你千萬不要十三點上身,他們哪怕是婚禮取消都跟你沒有半點關係,你去或不去見他,都是出於朋友之情,不要一廂情願地以為內心有愧,‘愧’也輪不到你。”
思凡臉上表情沒撐住,差點眼淚掉下來,心裡當然明白同學說得沒錯,能這么說她的人,是真的在乎她。
潘生約了她兩次,第一次她加班,第二次他臨時要提前回去,兩人終於沒見到面。她舒了口氣,有的事一旦開始,便不知道何收場,已經過去那么多年了,爛死在心裡也好,她當然明白少了她的潘生,他還是他,少了潘生的她,只會再經歷一次一巴掌把自己打醒的痛徹心扉。
“生他的氣嗎?”我問。
思凡端著兩杯香草茶放在長桌上,靠著河岸的陽台上種了幾盆花,吊在架子上,不修邊幅地恣意生長,有陽光雨露,葉瓣碧綠可愛。
“如果總是把錯怪到別人身上,我永遠都跟過去一樣幼稚。他心智健全,誰也左右不了他,我沒什麼可不甘心的。”
“是啊。”
“你知道嗎?他就是那種你跟他一旦交往了,永遠在等他電話的人,每次約會見面,連說話也是,你不知道他感興趣什麼,他心裡在想什麼,一步步讓你抓狂,你又捨不得離開他——”
“你和他在一起了?”
思凡沉默了,喝著香草茶,眼神盯著長桌上的布紋。
悠揚的笛聲穿過河面而來,對面的小陽台上一個少年在練習橫笛,清脆、圓潤的樂聲,在午後的陽光下那么猝然,沁人心脾。
我想起來,或許在哪兒聽過這首曲子。某張唱片,塞在落滿灰塵的紙盒子裡,以為還會找出來再聽,結果連播放的機器都消失了。
思凡髮髻邊的蝶戀花髮簪閃了一下,她做手工的朋友替她補上了碎鑽,看起來毫無差別。她把髮簪輕輕地放在長桌上,整理完頭髮,重新盤成一個髻插上髮簪。
我拿了個蘋果在手上,清脆香甜,一口接著一口地啃著,在尷尬而又安靜的氣氛中儘量保持輕鬆。
“你覺得不應該嗎?”她的說話聲很輕,輕到與對面飄來的笛聲糅合在一起。
“我覺得你的同學把該說的都說盡了。”
思凡的雙手撐在長桌上,臉頰朝著河上悠悠划過的小船,船駕著遊船,幾個遊客在拍照,有兩個神情緊張的遊客要同伴坐下,抱著手上的包,不敢亂動。
“我該聽嗎?”她問。
“她本意恐怕不是如此,只是告訴你可能會發生的事,你心裡要明白。如果喜歡上一個能讓自己抓狂的人,也是命中注定的事,勇敢或膽怯意義都不大,只在於你,甘不甘心。”
思凡握著香草茶的茶杯,眼神出神地瞪著前方。陽光從雲層鑽出來,河水粼粼地閃動,蕩漾開來。
“我做了一些缺德事,”思凡放下茶杯,眼神依然望著河面,“我受夠了別人眼中的乖乖女,什麼事都逆來順受,到現在我母親還為我沒有聽從她的安排而喋喋不休。我就偏不聽她的話,偏不—”
她深深吸了口氣,仿佛將要脫口而出的話卡到喉間,猶豫著是去還是吐出來。
我裝作不在意地盯著筆記本,已經沒電了,手機也是,總得點什麼來分散注意力。
“那天他走出來追上我,我們接吻了,”思凡握著雙手,聲音有些激動,“在北京的時候我們天天晚上在一起,他急著趕回去,部分原因是她知道了,他決定攤牌。”
“嗯。”
“之前為什麼會延期我不知道,不是因為我,兩個快要結婚的人一個星期也聯繫不到一次。我知道這樣說很刻薄,但他們早就出現了裂痕—”
“他從未告訴過你嗎?”
思凡沒有回答,看起來她似乎知道,只說:“我看過那么多悲劇的愛情故事,也被那么多美滿的現實生活感動過。真的、假的,千千萬萬次,都比不上愛上一個人。我知道很多人已經不再相信愛情,但愛是一個人的,是一個秘密,愛上或愛過的人都知道的秘密。我不認為神聖,我只想擁有一次。”
悠揚的橫笛聲莫名地有些傷感,她髮髻邊的蝶戀花宛如撲火的那隻蛾。
“現在呢?”我問。
“我跟他說和朋友出去玩幾天,他說要來陪我……”她笑了為自己小小的勝利心喜,“我說不用了,我想跟朋友玩幾天。”
她的眼神透著喜悅,食指尖敲著茶杯,忽然,她問:“你想說點什麼,說什麼都行。”
我搖頭,將剩下的香草茶喝完。
“我已經無藥可救了,是不是?”她問。
“不要這么傷感地愛一個人,不要心懷必死之念地愛著他,你只是愛一個人,不是要向世界交代……”
她摸了摸髮髻上的簪子,蝴蝶戀著一朵玉簪花,猶然,玉潔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