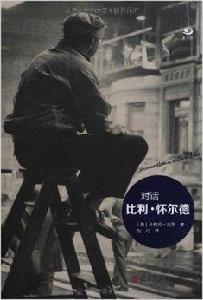內容簡介
《對話比利·懷爾德》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卡梅倫·克羅CameronCrowe (亦譯作卡梅隆·克羅威)美國著名導演,身兼劇作家、演員、製片人 ,於1957年7月13日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的棕櫚泉,目前執導影 片九部,最初卻是以樂評人的身份為人熟知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這是對懷爾德七十年電影生涯的第一次嚴肅考察……在這場考察中充滿了隱晦與逃避……而正是這種貓鼠遊戲使《對話比利·懷爾德》變得非常棒。——約翰·格雷戈里·鄧恩(John Gregory Dunne),《紐約客》
《對話比利·懷爾德》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好萊塢人物描畫之一,揭示了一個精明、淘氣與苛刻的人,他和他搬上銀幕的那些角色一樣有趣。——愛德華·古特曼(Edward Guthmann),《舊金山晚報》
卡梅倫·克羅現在證明了懷爾德式觸動的存在,他那些好電影中優雅的窘事在另一代人的心中已經變成一件件壯舉。——安德魯·歐哈根(Andrew O’Hagan),《紐約書評》
克羅捕捉到了這位大師獨特的聲音。每讀一頁都像是在抿一口香檳。——約翰·鮑爾斯(John Powers)《時尚》
懷爾德(和克羅)帶給我們的是私人談話中流露出的簡短的、不耐煩的……不自覺的喜劇天賦……《對話比利·懷爾德》的大部分篇幅都用在了關於他作品的令人著迷的細節討論上,懷爾德把智慧的寶石調配到了一本充滿啟發性的編劇導演手冊中。——薩拉·克爾(Sarah Kerr),《紐約時報書評》
名人推薦
這是對懷爾德七十年電影生涯的第一次嚴肅考察……在這場考察中充滿了隱晦與逃避……而正是這種貓鼠遊戲使《對話比利·懷爾德))變得非常棒。
——約翰·格雷戈里·鄧恩( John Gregory Dunne),《紐約客》
《對話比利·懷爾德》是有史以來最好的好萊塢人物描畫之一,揭示了一個精明、淘氣與苛刻的人,他和他搬上銀幕的那些角色一樣有趣。
——愛德華·古特曼( Edward Guthmann),《舊金山晚報》
卡梅倫·克羅現在證明了懷爾德式觸動的存在,他那些好電影中優雅的窘事在另一代人的心中已經變成一件件壯舉。
——安德魯·歐哈根( Andrew O' Hagan),《紐約書評》
克羅捕捉到了這位大師獨特的聲音。每讀一頁都像是在抿一口香檳。
——約翰·鮑爾斯( John Powers),《時尚》
懷爾德(和克羅)帶給我們的是私人談話中流露出的簡短的、不耐煩的……不自覺的喜劇天賦……《對話比利·懷爾德》的大部分篇幅都用在了關於他作品的令人著迷的細節討論上,懷爾德把智慧的寶石調配到了一本充滿啟發性的編劇導演手冊中。
——薩拉·克爾( Sarah Kerr),《紐約時報書評》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附錄
序言
“你給這東西想好結尾了嗎?”比利-懷爾德,這位在世的最偉大的編劇兼導演問道。
那是在1998年春天,厄爾尼諾的雨水已經製造了太多的麻煩,所以在這個瀰漫著濕氣的下午,我們都不想再提起頭上這場籠罩著加州的傾盆大雨了。他的辦公室坐落在貝弗利山的邊道上,我們就在那裡的門外見面。走上一小段台階之後,就進入了他安靜的辦公室。鑰匙在他的手中叮噹作響,他尋找著正確的那一把,然後又低頭看了一眼左邊鞋上鬆開了的鞋帶。要再走一步很可能就會被鞋帶絆倒了,所以他在門廳里停了下來。他91歲了,許多年前就已經不可能彎腰了。他沒有看我,我也沒有看他。一股尷尬的氣氛凝聚在我們中間,於是我彎下腰快速幫他把鞋帶繫上,之後我們都沒有再提這件事。我們進入他的辦公室,坐下來進行最後一場談話,這一系列的訪問已經持續了超過一年了。
請想像某場聚會裡一個散發著優雅氣息的時刻,一場只有比利·懷爾德影片中的人物參加的聚會。
鋼琴那邊正在攪動著一杯酒的,是《雙重賠償》(DoubleIndemnity)里在劫難逃的沃爾特·內夫(WalterNeff)。他努力不去盯著《熱情似火》里興高采烈的甜甜(sugar)。另一個房間裡,《桃色公寓》里的芙蘭·庫布利克(FranKubelik)與C·C·巴克斯特(C.C.Baxter)面對面貼身跳著某種後現代爵士舞,與此同時,《日落大道》(SunsetBoulevard)里的諾爾瑪·德斯蒙德從主樓梯上走下來,與《倒扣的王牌》里殘忍而野心勃勃的查克·塔特姆(chuckTatum)相會。而門外月光下,屈身躲在樹上相思成病的薩布里納(Sabrina),關注著整問房子裡這些互不相同的人的一舉一動,渴望著看上一眼戴維·拉臘比(DavidLarrabee)。
這將是怎樣的一個夜晚啊。但很可能發生的情況是,這場聚會的主人忍受不了那么多人向他鞠躬致意。比利·懷爾德,銀幕故事的大師,並不喜歡接受太多的讚美。他生命的最近10年經常需要盡義務接受獎盃與讚許,但事實甚至更加具有懷爾德風格(Wilderesque)。那些幾乎是同一群人的行業偶像們,與其授予他各種榮耀,還不如請偉大的懷爾德拍攝一部新電影。就身體狀況而言,懷爾德現在活動要很謹慎,有時需要一根拐杖。但他幾乎每天都要出現在貝弗利山的辦公室里,閱讀文章、聯繫他在藝術界的朋友們,他始終與超負荷的、沒有人物個性的可悲的當代電影保持著聯繫。
比利·懷爾德的作品是一個寶藏,裡面充滿了有血有肉的鮮活人物和精彩的生命體。在他的創作真經中有從頭笑到尾的喜劇、尖銳的人物刻畫、社會諷刺、真實的懸念、辛酸的浪漫,等等,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哀傷與興奮、冷嘲熱諷與痛苦難耐,這些都在他的作品中具有相同的分量。偉大的恩斯特·劉別謙(ErnstLubitsch)教會了他導演之樂,但可能是他的記者經歷給了他一種能力,使他能分辨出真相看起來什麼樣,聽起來又是什麼樣。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在多年之後,比利·懷爾德的作品與他同時代任何人的作品相比,都更多地作為對人類真相的描寫而存在著。在1997年美國導演工會引薦獲得DGA提名獎電影人的宴會上,在場的四位被提名者被問到了是誰點亮了他們創作上的靈光。所有人都認可一個名字:比利·懷爾德。
下面簡要說一下他四海為家的豐富一生。懷爾德1906年6月22日出生於小城蘇哈(Sucha),此地位於波蘭境內,後又成為奧地利的一部分。他的名字叫薩繆爾(samuel),但他的母親總是叫他比利(Billie),還稱他的哥哥威廉(Wilhelm)為威利(willie),後者出生於1904年。幾年後懷爾德一家移居到維也納,之後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被後人刨根問底且過分誇大了,對這些事情,懷爾德自己在我們的談話中都做了很好的解釋。“大部分事情都是捏造的,”他現在說道,“在過去,他們就愛幹這種事。”
不過在媒體的記載中有一件事是無可辯駁的,懷爾德的創作生涯是從他在維也納接到報社記者的工作開始的。他熟練地掌握了自己的工作,並很快有了喜歡對題目緊追不捨的名聲。1926年6月,在爵士音樂家保羅·懷特曼(PaulWhiteman)的邀請下,懷爾德出差到了柏林,並在那裡留了下來。從此他的記者工作——以及他的生活——變得更加多彩與混亂。為了寫一篇系列報導,懷爾德甚至去當陪人跳舞的舞男,並記錄下了這段經歷。他的想像力很快使他成了一名編劇,在蒸蒸日上的德國電影業中當一名槍手。很快懷爾德就成了署名編劇,他作品的水準也不斷提高,而這時戰爭卻日益逼近了。他逃到了巴黎,後來又到了美國,最終懷爾德在洛杉磯站穩了腳跟,並和其他歐洲難民結成群體,而這些人將會改變電影史。恩斯特·劉別謙在此之前就到達了,懷爾德很快就與他的偶像搭上了關係,在1938年與他合作了《藍鬍子的第八任妻子》(Bluebeard'sEighthWife),一年之後又有了影響深遠的《異國鴛鴦》(Ninotchka)。懷爾德在1942年首執導筒,拍攝了《大人與小孩》(TheMajorandtheMinor),本片由他與他第一位偉大的合作者查爾斯·布拉克特《2harlesBrackett)聯合編劇。他最近的電影是1981年的《患難之交》(Buddy,Buddy),合作者是另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I·A·L·戴蒙德(I.A.L.Diamond)。
懷爾德那種善於發現人類的陰暗面,並用富於啟發的幽默批判這個陰暗面的天賦很早就顯現了出來。“我在家常常挨打。”他會就事論事地談論這種事,性格中缺少自我憐憫。但是他童年的細節在其訪談里遠遠沒有被發掘出來。這些年面對尖銳的問題時,懷爾德是超然而沉默寡言的,然後緊接著他就會拋出一個新的話題或者笑話來。
1928年,懷爾德的父親在柏林去世,他是在去美國的路上在此作短暫停留看望比利。懷爾德的母親死於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他用事業上的堅持不懈與無可比擬的才智與這一可怕的記憶鬥爭。懷爾德在好萊塢這個充滿殘酷商業競爭的世界電影之都蒸蒸日上,他拍攝影片,被那些還在默默耕耘的人們推崇為創作天才、閃耀著智慧光輝的導演以及世界級的幽默作家。他的外在形象是趾高氣昂的、難以侵入的。有許多年他被人評價為庸俗,而他後期的作品多年來也飽受抨擊。這是每一位創新者在公眾視野下都會遭受的一劫。今天,很少有電影人不想自己與他相提並論。他是一個固執的浪漫主義者與高雅的人。他的作品因為沒有趨炎附勢或對某些事過分慷慨激昂而流傳至今。他在作品中沒有濫用感情,於是他以藝術家的身份永生。作為自己作品的鑑賞人,他頭腦冷靜,有時甚至可以說是個冷酷的父親。他已經贏得了每一個獎項,接受了每一次嘉許。而且他依然在世。其輝煌的一生被完美地創作並演繹出來,人們不禁要思索:也許年輕時的比利·懷爾德塑造的最偉大的人物,就是比利·懷爾德自己。
1995年,我有兩部電影正在醞釀中,而且多年來我一直受到比利·懷爾德的作品的啟發。就像許多積極進取的導演一樣,我前往他辦公室去朝聖。他對我的作品一無所知,我也沒指望他知道。我帶了一張《桃色公寓》的海報與一腦子的問題。我迫切地要求與他會面,這是由我的經紀人,創新藝人經紀公司(cIAA)的羅伯特·布克曼(RobertBookman)安排的,他是懷爾德一個不熟的熟人。我提前幾分鐘到達了他位於貝弗利山的辦公室,它藏在布賴頓街(BrightonWay)的一家禮品店後面一棟沒有明顯特徵的建築里。裡面沒有一點聲音。我透過郵件槽望進去,看到了一幅兩間昏暗房間的景象,裡面沒有裝飾紀念品,只有一些書和一張擺滿文案的寫字檯。
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裡我沿著街區閒逛,消磨時光,用投幣電話給他的電話答錄機打電話。最終,就在我第二次決定離去,拿著鑰匙向我的汽車走出第一步時,懷爾德從對面的小巷中出現了。他看上去就是典型的懷爾德的樣子,一個矮小壯實的男人,穿著粗花呢外套,戴著便帽,直直衝我走來。我作為一個從沒有朋友或親密家屬活到這個歲數的人,以一種過分正式的方式謹慎地走向他。我介紹了自己。絕對沒有火花——零度共鳴。他迅速禮貌地例行公事地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後尋找我手上的馬尼拉紙信封。他以為我是郵遞員。
我提到了我們上午11點的約會,懷爾德看上去很驚訝。他馬上道歉。他說他完全不知道這次會面,並邀請我走上樓梯。“上來吧,我要記一下這件事。”
在我隨他走上台階時,他正在腦中查閱著本周的約會記錄。沒有,沒有與卡梅倫·克羅(CameronCrowe)的會面計畫。他打開辦公室示意我進來。布告欄上釘著一張瑪琳·黛德麗的照片。牆上掛著一組大衛·霍克尼(DavidHockney)拍攝的懷爾德與他的妻子奧德麗(Audrey)的拼貼照片。一幅愛因斯坦(Einstein)的肖像;一張框起來的懷爾德與黑澤明(AkiraKurosawa)以及費德里科·費里尼(FedericoFellini)合拍的照片。而在門上,有一句我曾經在書上讀到過的,由索爾·斯坦伯格(SaulSteinberg)設計的著名簽字:“劉別謙會怎么做?”
我在他對面坐下後他先聽了一陣電話留言。但裡面卻沒有我的留言。他聽著一個《洛杉磯時報》的作者打來的電話,對方用快節奏且不帶色彩的語氣解釋說他對於一篇關於奧斯卡的文章有一個問題,而他截稿的最後期限就是現在。對方快速說了一遍自己的電話號碼,懷爾德一開始試圖記下來,但在記了3個數字後就放棄了,並放下了筆。“我不會給你回電話的。”他對著答錄機說。他轉向我。“我能為你做什麼?”
懷爾德耐心地聽著我對他作品的溢美之詞。一開始心不在焉,後來有了一些活力,很快就興高采烈起來了,他回答了我的大部分問題。說了一些即使不是,也聽上去像是秘密的事情,然後用一個小時中的大部分時間討論了他導演與選演員的技巧。懷爾德強調了選演員的重要性——舉了加里·格蘭特的例子,他錯失了找他做演員的機會,這件事一直以來廣為流傳。他曾經希望他出演《龍鳳配》(Sabr’ina)以及之後的《黃昏之戀》,但都沒能如願。最後,懷爾德拿起筆在我帶來的海報上籤了名。懷爾德像是老朋友一樣看著那張海報。“《桃色公寓》,”他說,“好電影。”
“我最喜歡的電影。”我說。
“也是我最喜歡的。”他說道,好像這是剛剛下的最終決定。“我們有正確的演員。它起效了。”他乾巴巴地停了一下。“我想不出什麼有意思的話能寫在你的海報上。”他簽了名字和日期。當他和我走向房門時,我告訴他自己希望他在我的第3部影片《甜心先生》中出演一個小角色。他建議我快開拍時再聯繫他。他說他不是個演員。“只是個小角色,”我說,“但它很重要,是傑里·馬奎爾(即甜心先生)的導師,原運動員經紀人迪基·福克斯。”
“小角色?”他說道:“那我絕對不會答應了!”
他走進了洗手問,它就在順著大廳走下去的地方,當我離開時,他特別提到關於那個角色的事我應該再給他打電話。他站在洗手間的門前說,“卡梅倫,這是個好名字。在德國,人們只有兩個名字。漢斯……還有赫爾穆特。午安。”這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讓步,它被風格化地表露了出來。他消失在廁所里。我離開了,身上綁著創造力的火箭。
之後幾個月,我一直告訴朋友們我已經開始與比利·懷爾德討論讓他在我的電影裡演一個角色的事。我甚至把它排在了拍攝計畫的第一個鏡頭。懷爾德將會是我的幸運符。
但是只有一個問題——我找不到他。我給他的經紀人打電話,他回電話說懷爾德提過這件事,但他還沒有聽到懷爾德的決定。當拍攝日期漸進,我最終找到了他辦公樓外的一個實習生。給他的任務是——一看到那位大師就給我打電話。
現在已經是1995年末,今天是湯姆-克魯斯(TomCruise)、小庫珀-古丁(CubaGoodingJr.)以及邦尼·亨特(Bonnie}tunt)的第一天彩排日,他們現在都已經加入了《甜心先生》的拍攝。電話來了,懷爾德現在在辦公室。我試著打了電話,鈴聲響了一下後他就接了。
“懷爾德先生,我是卡梅倫·克羅。我們之前討論過您在我電影中演出的事情。”
“別煩我!”他咆哮著,“我是個老人。不是個演員,我也不會出現在你的片子裡。”偉大的比利·懷爾德接著掛了電話。
不久之後,我與湯姆·克魯斯踏雨走在貝弗利山的路上。我們的任務是親自拜訪懷爾德。有電影裡的明星撐腰,我們應該能夠面對面達到目的。
懷爾德應了門,表達了對我們不期而至的驚愕之情。但他還是請我們進去了。在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裡,我們請求他,並與他討論這部電影,他還是說不。(“我知道自己做得了什麼做不了什麼……我只會搞砸你的電影。不會有好結果的。找別人吧。我很尷尬,我現在很不自在。”)克魯斯把身子往前傾,開始唱高調,解釋說懷爾德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他還是說不。我提起了他說的自己對沒法找到加里‘格蘭特演出的失望,解釋說我很不願意放棄這一夢幻組合。懷爾德看著我——或更確切地說,正視著我。我覺得自己像個馬屁精,一個滿嘴屁話的傢伙,但可悲的事實是,我說的每個字都是真的。
他與克魯斯談論了《龍鳳配》、《異國鴛鴦》以及《日落大道》,精確地分析了我們電影中的情節,最後他問了我一個私人問題。
“這是你的第一部電影?”
“第三部。”
“想過放棄嗎?”
“想過,”我答道,完全誠實地面對這一私人問題。
他點點頭。當然,我答錯了,而且馬上就知道了。看來我已經在導演新兵訓練營一題就被踢出了門。或者也許這話是以一種文雅的形式冒犯了他。或者,嘿,這是比利·懷爾德啊,那一定是以上兩種可能都是真的了。他沖我眨著眼睛,好像在說,“導演是一項艱難的工作……哈姆雷特式的不堅定只應放在舞台上,上帝啊。”他再沒正眼看過我。他不可動搖而又魅力十足,堅定,沒有花言巧語……“堅定”是對這位紳士的最準確描述,這位之前不肯回我電話,現在毫不猶豫地用強大的氣場對我與銀幕上的傑里·馬奎爾說不的人。最後我們起身離開了。
“很高興見到你,也很高興見到你,”他謙和而有威嚴地說。他的目光划過我停在了湯姆·克魯斯身上,“特別是你。”
我和克魯斯離開他的辦公室進了車。我剛剛讓這位世界上最大牌的明星見識了一樣他沒怎么經歷過的東西:失敗。第一天的彩排我沒打算有什麼成果。我們默默開車回去,繼續彩排,拍電影,每過幾周就提一次懷爾德。他的回絕的力量在幾個月後還是讓人覺得恥辱,這成了克魯斯和我之間的一個黑色笑話。有時我會重提一下會面中那個刺痛我心的幽默段子,那個懷爾德式的再見:“很高興見到你,也很高興見到你……尤其是你。”我們總是會大笑,痛苦地笑。
1997年2月,《甜心先生》已經上映幾個月了。《滾右》(RollingStone)雜誌刊登了一篇文章詳細敘述了這段關於懷爾德的插曲以及影片的拍攝情況。從比利·懷爾德與奧德麗·懷爾德的長期朋友卡倫·勒納(KarenLernet。)的辦公室發來了一封傳真。勒納第一次見到懷爾德夫婦是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當時她是《新聞周刊》(Newsweek)的記者;她之後嫁給了艾倫·傑伊·勒納(Alan.JayLerner)uj。勒納這些年來與懷爾德夫婦的關係非常親密。她是他們家定期到訪並共進晚餐的客人,同時還是個懷爾德迷。她讀了我在《滾石》上的文章。問我是否對做本書的想法感興趣,一本比利.懷爾德的新的訪談錄,和弗朗索瓦·特呂弗(FrancoisTruffaut)的《希區柯克與特呂弗對話錄》(Hitchcock)差不多。當然這個想法很吸引人,但是我給她打電話說了我的顧慮。懷爾德和我不怎么一見如故。我不想強推這個專題。英雄通常應該與別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把自己擺在書架上,放在檔案里,保持一個能夠繼續做英雄的距離。我不想繼續挫敗。
但勒納堅持,她對我說懷爾德也讀了我的文章,並且很喜歡它。懷爾德已經提出要讓我給他做一篇雜誌專訪——他最近沒有做過多少訪談——勒納建議我們試試看我們之間有沒有化學反應。如果有,也許這篇訪談就能變成一本書。我將回到我們之前的災難發生地,開始討論兩部懷爾德記憶尚存的電影——《雙重賠償》與《桃色公寓》。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受虐狂行為。我有一個新的劇本要著手。沒有時間。最好的做法是把這個來自大師的邀請看成是一次不正常的變故、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糾纏、一個我應該放聰明點拒絕的事情。
當然我馬上就開始計畫與懷爾德的會面了。
“你看起來長高了,”他一打開辦公室的門就說道,“你隨著你的成功變大了。”懷爾德穿著西裝、背帶褲與流蘇的平底便鞋。他示意我進入我們第一次見面的同一個小房間。在問候了我幾句之後,他就把話題轉到了即將到來的奧斯卡獎,《甜心先生》獲了5項提名,包括最佳影片,特別是克魯斯被提名最佳男主角,這對於喜劇電影和喜劇表演真的是一大恩惠。“而且我喜歡演我角色的那個傢伙。”他加了句。
我笨拙地擺弄著錄音機,測試麥克風,而懷爾德則像往常一樣怡然自得。他那時已經90歲了,而我卻已經在匆忙努力跟上他的速度了。但是,就像懷爾德自己最好的作品裡那樣,事情在第一幕一開始就會有一場糾結。我馬上就會發現,在通向完成這本訪談錄項目的道路上,散落著許多我的先行者的遺骸。
懷爾德不希望再有關於他的書出版了。他已經對其他寫他的書不滿意了——他覺得它們錯誤滿篇,而且更糟的是還很無聊。最近的一次嘗試是一個德國作家寫了一本只用德語出版的書。他認為這本書美國讀者不會感興趣。之前的一次問答式嘗試在許多年前就被否決了,只有少數記者曾經把他的聲音變成文字——那是富含著中歐措辭、美國俚語和要人命的純智慧的混合物。沒有什麼事情比一本正經的懷爾德本身更好笑的了,他很少因為自己的笑話笑,但是卻用工匠式的喜悅之情滿意地看著你大笑。可是,90歲高齡的他已經對“把我抬成偶像”沒有興趣了。他一再地強調,在他看來,我們這第一次訪談,就是把我們的關係結束在一份令人愉快而有益身心的記錄上的嘗試。“這是為你的雜誌,”他說道,“這是為你的專欄。”
專欄?我根本沒有專欄。
他手扶到桌子上,戴上一副新眼鏡,然後用長而柔軟的手指小心翼翼地調整了一下面前裝著Tic—Tacs牌糖果的透明小盒,一根手指忽然彎到了患有關節炎的一邊。桌面上滿是紙張——全世界的來信,電影節的邀請,電話號碼——還有桌邊那個電話答錄機,旁邊是那個當他在辦公室時就親自接的電話。
在我們訪談開始的前半小時,我經歷了一場奇怪的似曾相識的經驗。我已經讀了之前所有關於懷爾德的書,看了他的許多訪談。但是這次談話的氣氛有一道美麗的弧線,在他闡述他一如既往的尖銳而有趣的觀察時加上了一層生活氣息。卡倫·勒納在一邊親自觀看我們的第一次訪談,這有效地緩和了氣氛。我們的談話是從很多趣事開始的,其中的一些很有名,但是我記者的背景向我大聲耳語要我往下挖——搞到一篇懷爾德從沒有真正給出過的訪談。這一下午真是典型的懷爾德式糾結。當我本應坐在家裡寫一部新的電影時,卻在努力把懷爾德拉進一個他堅決不想參與的計畫。我在陽光明媚的下午坐在懷爾德對面,談論著現代的一些最偉大的生命——生於比利-懷爾德心裡與腦中的生命——並把我們的談話看作是一條通向未來的痛苦鏈條。
在本世紀早期他的所有同代人中,只剩下比利·懷爾德還活躍地堅守在這裡了。他的記憶清楚,在我們的談話中他很少用記不清當作託詞。他還在重塑、反思著他的電影,還在為錯失的對話或者機會而傷心。這種表現是不同尋常的,卻也是一睹那些事情的真相的機會。不管是誰,作為一名導演,在最好的狀況下也會對60年來的瑣事糾纏不清。而在寫作這篇文章時,他已經將近92歲了,卻依然是一個對電影與電影業滿懷嘲諷的觀察者——雖然他很少使用Film或Cinema這些詞——他時刻關注著大部分的當代電影,經常與他的朋友理察(Richard)與芭芭拉·科恩(BarbaraCohen)(理察.科恩於1999年5月去世)一起在家中的放映室觀看那些影片。“Pictures”一詞是懷爾德為用膠片講故事這一耗費其一生的職業選擇的術語。在超媒體與全球化時代,懷爾德對自我的重要性的意識一點也沒有減弱。
我看著他大聲嚼著Tic—Tacs糖,禮貌地、有時小心地處理著我好幾張紙的細節問題。我知道這不會容易。他不鋪張感情。他不是總能明白我的俚語,而我在聽他談論將近一個世紀的工作時,有時會跟不上他在不同時間點跳來跳去的腳步。最後,他是一個舞者。他總是試圖用著名的掌故遮掩什麼,這些掌故多年來已經被一個或者兩個或者四個入迷的晚餐聽眾磨得透亮了。我的目標就是在聽他火花四射地背誦自己最好的故事和最偉大的成功時,挖出隱藏在那之下的東西。有些問題可能已經被問了很多次;躲避它們對懷爾德來說太有趣了。一瞬之間,他就能看透你最渴望的那個問題。如果智慧是你最大的武器,幹嗎不常用?他就是這么做的。懷爾德自己就是他最偉大的人物。這樣一個人物到底是怎樣書寫、怎樣生活的呢?從90歲高齡的比利’懷爾德那裡尋找答案可以變成一項全職工作。而這僅僅是個開始。
卡梅倫·克羅
1998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