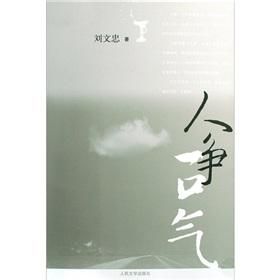內容簡介
《人爭一口氣》是一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生人的真實的人生故事。主人公生在中原地區一個富裕的大家族,然而出生不久即遭遇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連綿不斷的兵禍、匪禍,使他們的家族家業中落,他也相繼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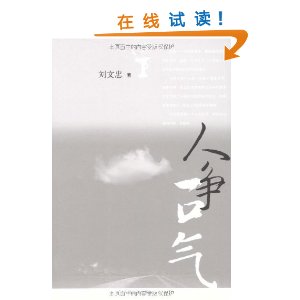
148年家鄉解放,雖然父親生前是親共的鄉紳,而且土改前全家已經淪落到靠討飯過春荒,但家庭成分依然被定為地主,這使他背負了幾十年的精神重壓。然而也正是因為解放,他才有機會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讀了大學,讀了研究生。
研究生畢業的他一心要做個事業有成的人,以報答社會。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卻讓他將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都奉獻給了各種“運動”……
但他有著不認命、不服輸的精神,認定知識會改變命運,他把少年時代的困苦與艱難當作一生的精神財富,在時代的浪潮中,始終保持著自己的理想,堅守著自己的節操,奮力筆耕,寫下了大量著作。
此書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第一代知識分子的生活縮影,作者以樸素流暢的語言和白描的手法,揭示出許多駭人聽聞的事件,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他始終關懷幫助弟弟,把親情看得高於愛情,又讓人在宇里行間讀到一種動人的情感力量。
編輯推薦
《人爭一口氣》是一個中國最普通,最基層的百姓的生活史,也是一個出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命史。
它絕對是個人的,充滿了細枝末節,雞零狗碎:但這些雞零狗碎又無不打著多災多難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時代印記,體現著重情重義,孜孜以求的民族的精神。
它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歷史,同時它也是時代的,民族的!
作者簡介
劉文忠,1936年生,江蘇豐縣人。1962年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65年山東大學中文系漢魏六朝文學專業研究生畢業,師從陸侃如先生。長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曾任古典文學編輯室副主任,編審,中國《文心雕龍》學會副會長、顧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數十年來,利用業餘時間奮力筆耕,有《鮑照與庾信》、《中古文學與文論研究》、《漢魏六朝詩文選》、《正變·通變·新變》、《左思與劉琨》、《虛實話三國》等三十部著作,發表學術論文六十餘篇,鑑賞文章三百多篇。
目錄
一個古老的傳說
劉氏家族
劉家遭遇的一次匪禍
便集的第一個大學生
劉汝薌的長子孫劉福德
劉福德交友袁敬文
劉啟明誕生
認祖歸宗的紅軍排長
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一任鎮長
幼兒時的啟明
劉福德的臨終託孤
劉家的長工秦令雲大叔
逃反歸來的老爺爺
啟明幼時與八路軍的接觸
“風來了,雨來了,老和尚背著鼓來了”
民眾運動
八路軍北撤之後
聽大人講故事
“挖穩患”運動
到親戚家讀書
“大分家”與設“望鄉台”
進城讀書
蹲監獄與逃出監獄
第二次到姑母家讀書
家鄉解放了
他嘗到了種地的艱難
討飯的開始
啟明要飯
冷冷清清過大年
母親的病
人窮志不窮
母親之死
他做了小女婿
土改中的劉家
讀國中與鬧離婚
關鍵時刻他遇到了袁敬文叔叔
奶奶讓他記住秦令雲等人的大恩
一個讓他單戀了多年的女同學
走進大學之門
姑父王天錦的遭遇
轉入中文系
接踵而來的運動
在大躍進的年代裡
夢中入黨
放文藝衛星
奶奶的病與死
大學生參加整社
在姐姐家過春節
三元擅自退學
讀書的干擾太多了
聽老領導俞銘璜做報告
與女友在南京相見
為胡小石先生守靈
寫畢業論文
考研究生
“天涯何處無芳草”
初見導師陸侃如先生
研究生學習生活點滴
孫老師之死
他要回了自己的房屋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三有三無牌”研究生
去曲阜參加“四清”運動
畢業論文與“大批判”
姐姐與弟弟
第一次尋找弟弟
第二次尋找弟弟
到北京工作
“文革”的經歷和見聞
流浪江湖的弟弟
姐姐的自殺
文聯的“黑旗兵事件”與朱學奎之死
砸印尼大使館與火燒蘇聯大使館
工軍宣隊進駐之後
到“五七”幹校去
徐資料員之死
在“五七”幹校的生活
他成了“五一六”分子的審查對象
吃死雞與死豬
幹校的木工熱
第二次的留守生活
重新走上工作崗位
他面臨著新的抉擇
三元的毛驢車和婚姻大事
解除了後顧之憂,卻又面臨著新的困難
把“文革”中失去的時間找回來
學術活動與筆耕生涯的開始
姑母與劉家的三代人
當副主任與入黨
出版社評職稱
當了八年的黨支部書記
沒有複審權的複審和超前的終審
為出一本好書而呼喊、力爭了六年
遲到的“國家圖書獎”獎狀
“親情遠比泰山重,外物猶如鴻羽輕”
老某與劉大狗的下場
三十多部書是怎樣寫成的
筆耕路上遇郭強
他所撰寫的兩篇碑文
他是艱難玉成的人
文摘
一個古老的傳說
公兀前二百多年的時候,荊軻受燕太子丹的派遣,在易水餞別之後,唱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慷慨悲歌,西人強秦,去刺殺秦始皇。也許是秦始皇命不該死,荊軻失手,反死在秦始皇的刀下。秦始皇為了發泄他的心頭仇恨,用他的寶劍把荊軻大卸八塊,讓手下人分別埋在八個不同的地方。這時有一位方士向秦始皇進諫說:“大王容稟,我觀天象,看到在豐邑的上空,有一股雲氣,像是王氣。”
秦始皇最忌諱哪個地方有王氣,聽到此話,便急著問方士:“愛卿有何辦法,可以破除豐邑的王氣?”
方士回答說:“荊軻這小子的屍體已被大王砍成八塊,如能在豐邑埋上一塊,可以破除那裡的王氣。”
秦始皇用右手拍了一下面前的几案,斬釘截鐵地說:“如此甚合孤意,傳朕的口令,從速辦理。”
當天,兩輛馬車便離開鹹陽東去,前輛車上載著幾個方士,後輛車上載著幾個武士,車上還帶著一個麻袋,麻袋內裝著荊軻的頭顱,不日便到達了豐邑。
方士們看到古豐的西北有一團白色的雲氣盤桓,便用手向西北指了指,帶著馬車向西北方向駛去。到了豐邑西北三十五里地方,便讓馬車停了下來,說道:“就埋在這裡吧!”
幾個武士到附近的百姓那裡拿了幾把鐵杴,挖了一個三尺深的坑,一個方士一腳把荊軻的頭顱連著麻袋踢下坑去,口中念念有詞地說:“我把你踢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這兩輛馬車回到豐邑,又向縣令傳達了秦始皇的一道手諭,命令縣令建一個“魘氣台”,目的還是破除豐邑的王氣。
荊軻的墳墓原來並不大,同情他的老百姓不斷地為他添墳,墳頭便越來越大,人們稱這個墳頭為“荊冢”,墳地附近有個村莊,這個村莊便命名為“荊冢村”。
秦始皇萬萬沒有想到,他在豐邑埋下的是一顆復仇的種子。公元前256年,豐邑生下了一個孩子,這便是秦家王朝的掘墓人劉邦。荊軻死的時候,劉邦已經二三十歲了,只是還沒有嶄露頭角。
“荊冢村”的故事,不見於正史記載,只不過是一個古老的傳說罷了。
劉氏家族
往事越千年,明代洪武年間,山西洪洞縣大量向外移民。有一位姓劉的青年農民,帶著他的妻子和兩歲的兒子,從洪洞縣的老鴰窩遷徙到了荊冢村,挑著一副擔子,一路上歷盡了千辛萬苦,步行了七八百里路,才到達目的地。一副擔子上挑的,便是他們的全部家當。搬遷始祖的名字,沒有留下來。六七代譜系無考,到了清代中葉,劉氏才有了《家譜》。生活在明代萬曆年間的劉沼,被尊為“冠譜一世祖”。到了清代末年,劉家人丁興旺,發展成擁有一千多人口的大家族。在劉沼的眾多子孫中,有窮的,也有富的,世代都有讀書人,也出了幾十個秀才。還出了一個做官的,曾經做過直隸州的判官。除了這家做判官的劉汝舟擁有四五千畝土地外,還有十幾戶中小地主。當然也有一此貧苦的農民。
荊冢村的南頭有一個魏莊,在明代末年出了一個太監,人稱魏小官。他與大太監魏忠賢攀上了關係,從此大富大貴起來。據說他家的屋樑都是烏木的。為了他家買東西的方便,他在荊冢村設了一個集市,並把荊冢村改名為便易集,簡稱便集。
明末發生過一次黃河泛濫,決口的地方在山東與河南的交界處,開了口子的黃河咆哮著,怒吼著,滾滾向東北流去。魏莊被黃水衝垮了,並陷落下去,便集的南頭衝出了一條河。魏莊被毀滅了,便集卻倖存下來。
便集村有人想挖掘當年陷落下去的烏木樑頭,白天一天的發掘,僅能使梁頭露出一點,到了第二天,梁頭又不見蹤影了。多次的嘗試都是如此,以後,人們便也死了這條心。1953年挖河的時候,有一位農民在河底挖出了一個陶瓷罐子,打開一看。是醃好的韭菜花。有個不怕中毒的民工嘗了嘗,還居然有韭菜花味兒。
這是魏家的遺物,魏太監家的瓷器,至少是明代官窯的產品。挖河的民工只帶乾糧不帶菜,他們見第一個品嘗的人吃下去沒事,一個個便就著乾糧吃起來,不一會兒吃得精光。但這個瓷罐在民工回家的路上不小心被摔碎了。如果留到現在,這個明代官窯出產的陶瓷罐子,可能要賣個大價錢。
劉家的人居住在便集村的比較集中,村子的北半部大半都是劉家的人,以房分和居住的院落而論,又分為東西兩院。到了清代中期,東院的和西院的都出了幾戶地主,土地有十頃八頃的,也有三頃兩頃的。東院的老劉家,在清光緒年間,三四代人在一起過日子不分家,竟出現一百多人在一起吃飯的大家庭,做飯的大鍋直徑足有四尺左右,在我國歷史上清代是人口最多的時代,從老劉家的人口生息繁衍的歷史,也可以看到一斑。
東院劉家的劉錫祉與劉錫祐是親兄弟,兩人各生了四個兒子,叔伯兄弟八個。八兄弟中的老五叫劉汝薌,他自幼讀書,光緒年間考取了秀才,他一面經營土地,一面學習中醫,買了大批的醫書,天天在細心研讀。皇天不負有心人,不幾年,便成了方圓幾十里出名的小兒科醫生。他是一個樂善好施的人,對於村中的窮苦百姓,在他們挨餓的時候,總要周濟一點糧食,讓人家能夠度過春荒。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起義軍的散兵游勇到處受到清兵的搜捕追殺,有兩個小長毛逃到了便集村,一個姓仇,一個姓袁,兩個人還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姓袁的這孩子才十五六歲,身上還受了傷。劉汝薌與這兩個小太平軍戰士的年紀也差不多,他看他們怪可憐的,便收容了他們。按照當時的法律,私藏小長毛是犯法的,劉汝薌對收容小長毛也有點擔心,想著把袁小毛的傷養好後,避一避清政府查辦太平軍的風頭,再把他們送回家去。過了一段時間,袁小毛的傷也養好了,劉汝薌用他出門乘坐的轅車,派人把這兩個小太平軍戰士送回了老家。姓仇的被他的父母留下了,但姓袁的父母說什麼也不願讓兒子留在家裡,他們怕清政府追究。袁小毛又跟車回到了便集。劉汝薌還是冒著風險把他留在了自己家裡。幸虧村中無人告發,倒也沒惹出什麼麻煩。
就這樣袁小毛便留在便集村安家落戶了。先給劉家的一家老小剃頭,後來又在劉家的幫助下在便集村的街面集市上搭了一間小房,開了個剃頭鋪。再後來小毛也娶上了老婆,雖然過得不富裕,幾代之後也成了便集村子孫滿堂的一戶人家。
劉汝薌當醫生並不是為了賺錢,只是為了積德行善、治病救人。他一生沒收過病人的一分錢,一輩子沒開過藥店賣過藥。把脈看舌之後,便把小兒的症狀向家長一一敘說。家長連連點頭便表示醫生診斷的準確。開方之後,又囑咐病兒家長說:“西門裡郝家的藥又全又便宜,到那裡去抓藥吧!”其實當時便集村的藥店有三四家之多,多是他本家侄子、侄孫開的,藥價稍微比郝家貴一點。郝家是外來人,為了生意能在便集村站住腳,故意比別的藥店便宜一點。劉汝薌知道,貧苦的農民抓幾服藥不容易,當時的中草藥雖然很便宜,但一服藥也要幾斤糧食的價錢,為此,他不怕斷了本家侄子、侄孫們的財路。
找劉汝薌老先生看病的人總是絡繹不絕,有抱著孩子來的,有背著孩子來的,也有推著一個木頭輪子的小土車來的。他們都知道先生不要錢,是義診,有的人也不止一次帶孩子來看病。逢到生瓜梨棗成熟的季節,便用家織的土布手巾,或包著斤把二斤鮮紅的小棗,或包著兩個小甜瓜,讓劉老先生嘗嘗鮮。老先生總是婉言謝絕。有時實在推不掉了,便收下一個瓜幾個棗。
劉家遭遇的一次匪禍
1921年,一場災難降落在劉家大院。那年頭正是軍閥混戰、土匪橫行、民不聊生的時代。山東魯西南一帶,土匪特別猖獗,常常集結兩三千人馬,圍攻村鎮,打家劫舍,綁票勒索。
便集是一個集鎮,縱橫交叉的兩條三里長的十字街把村鎮分成四塊,東西南北有四個寨門,連線四座寨門的是寨牆,寨牆的四角還設定了炮樓,安裝了清代鑄造的大炮。寨牆子外邊還挖了一道一丈寬的寨溝,當地人稱為“寨海子”。寨門晚上關閉,打更、放哨的事都有人管,儼然像一個中世紀的寨堡。這是村寨的第一道防線。
這種中世紀的寨堡到了近代是落伍了。清末民初,洋槍洋炮逐漸多了起來。連土匪也有了洋槍,已經不是昔日的刀客。村寨的地主和大戶人家,為了對付土匪,也買了一些洋槍。長槍多數是漢陽兵工廠造,當地人稱為“湖北條子”。便集村看家護院的長槍大約有三十多條,多集中在劉家,南頭的馬家也有幾戶地主,不過七八條槍。
劉汝薌家的槍沒有他三哥劉汝薺家的多,但他有一把德國造的膠把手槍,可以連發十一顆子彈。這是豐縣城西北方圓幾十里之內唯一的一支德國造的膠把盒子槍,號稱“城西北第一槍”。
便集的北邊五里有個村莊叫毛莊,這是劉氏家族的一個外莊子。那時的地主有了錢就知道買地,本村周圍的土地沒有多少可買的了,就到遠一點的地方去買。買了遠處的地以後,就得有人去耕種,去管理,去建宅院,這種新建的村莊就叫外莊子。劉氏家族這樣的外莊子除毛莊外還有兩三個,最遠的離便集有三十里之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