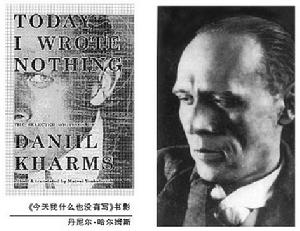概述
丹尼爾·伊萬諾維奇·哈爾姆斯(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Хармс)(1906——1942)
前蘇聯文學家。1906年生於彼得堡,20年代初步入文壇,加入文學團體“真實藝術協會”,同時寫出大量詩歌、小說和劇本。20年代末起主要從事兒童文學作品的創作,他的兒童詩一時家喻戶曉。1942年,哈爾姆斯無辜遭鎮壓,後被恢復名譽。 1927年,哈爾姆斯的《伊莉莎白·巴姆》一劇在列寧格勒上演,該劇中所體現出的情節和衝突的淡化、人物的木偶化、台詞的非連貫等特色,使得有些研究者認為:哈爾姆斯是荒誕派戲劇的先驅之一。60——70年代,他的詩作紛紛重新發表。1987年第14期蘇聯《圖書博覽》刊登了哈爾姆斯的組合短篇《斷片》。
| <th> 基本信息欄</th> | |
| 中文名:丹尼爾·伊萬諾維奇·哈爾姆斯 外文名: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Хармс 國籍:前蘇聯 出生地:彼得堡 成名:伊莉莎白·巴姆/1927年 | 平生:1906——1942年,年僅36歲。 文學團體:真實藝術協會“OBERIU” 作品: 戲劇代表作《伊莉莎白·巴姆》 作品集《今天我什麼也沒寫》 組合短篇《斷片》 地位:兒童作家、荒誕派戲劇先驅、後現代主義天才 |
簡介
原名:丹尼爾·伊萬諾維奇·尤瓦喬夫(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Ювачёв),筆名“哈爾姆斯”來源於對英文字“Charms”和“harm”(“迷人”和“傷害”)間的諧音關聯,也因為他十分欣賞英國文學形象福爾摩斯。
評價:“陀、托二人的小說在俄羅斯學校廣為普及,適合於14到16歲的青少年,當你是18歲時,這些小說的確頗有裨益。但到了30歲,一個人總要讀寫不同的東西,而哈爾姆斯就是這樣的作家。讀一讀蘇聯早期的俄語詩歌和美學理論,你會發現,如果這些俄羅斯作品早就被翻譯過來的話,同時代的美國詩文理論就黯然失色,毫無必要了。” ——翻譯家 馬特維·延科列維奇
作品的主題: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躲藏,不安的生命真實感和對不起眼的細節的投入
作品的風格:擅寫怪誕的散文和兒童故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列寧格勒前衛藝術家中贏得聲名。
生平:
1905年哈爾姆斯生於聖彼得堡,父親是當地的政界和宗教界知名人士。
1925年起,哈爾姆斯便開始在誦詩會和其他前衛活動中顯露頭角,成為蘇聯作協的前身之一“全俄詩人協會”列寧格勒分部的成員,發表了兩本詩集,這是哈爾姆斯在世時唯一發表的兩部“成人”作品。
1927年,哈爾姆斯同一批實驗文學家,包括亞歷山大·維丹斯基(1900-1941)和詩人尼古拉·扎波羅茨基(1903-1958)一道成立了文學社團“OBERIU”(“真正的藝術”的縮寫),並成為其中堅力量。社團的初衷是為了應和風行歐陸的超現實主義,同時挑戰蘇聯官方推行的沉悶的美學風尚。
1942年,列寧格勒遭受圍困,哈爾姆斯本人也為這種挑戰付出了代價,最終死於獄中,年僅36歲。
人物傳記
陌生的丹尼爾·哈爾姆斯 ■於大衛
厄內斯特·海明威有一次把世界文壇比喻成拳擊場,調侃說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這兩位重量級拳手為他力所不敵,讓他恐懼。不過,在一些西方評論家看來,同另一位俄羅斯作家相比,陀托二氏的作品太過小兒科。這位作家對大部分讀者來說相當陌生,他的名字是丹尼爾·哈爾姆斯。
蘇聯時期的優秀作家的創造和革新,為世界文學提供了豐富的文化成果,不過百十來年間這塊土地上的特殊歷史有時讓這條供應鏈時斷時續,一些作品和作家無法進入同時代人的視野。時過境遷,新時代並不具備並未足以完成對這些作家的再認識的能力。這些作家或作品又由於其特殊的背景而被評論家草率歸類,成為一種“時代的發現”。現在,人們才能漸漸看清這些作家的偉大之處。丹尼爾·哈爾姆斯(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Хармс)就是這樣的作家,他足以稱作當時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現代主義,或者說後現代主義作家,其作品遠非具有某些現代特徵的布爾加科夫或普拉東諾夫可以比及。美國達克沃斯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由馬特維·延科列維奇翻譯的丹尼爾·哈爾姆斯作品集《今天我什麼也沒寫》,為這一評斷提供佐證,再次把這位被忽略的天才推薦給西方讀者。
作家半個多世紀前便離世而去,少為人知,所知者也一般把他貼上兒童作家的標籤。丹尼爾·哈爾姆斯的作品當時很少受到出版社的認可,賴以為生是兒童故事創作。其餘的作品,包括大部分詩文均發表在地下出版物上。長期以來,哈爾姆斯被歸類為“荒誕主義”作家。然而,細品之下,他的作品非但並不荒誕,且更多透射了對生活各種境況和人性本真的獨到關注,實際上同其他反專制的作家和作品大異其趣。
哈爾姆斯1905年生於聖彼得堡,父親是當地的政界和宗教界知名人士。哈爾姆斯擅寫怪誕的散文和兒童故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列寧格勒前衛藝術家中贏得聲名。作家原名為丹尼爾·伊萬諾維奇·尤瓦喬夫(Даниил Иванович Ювачёв),筆名“哈爾姆斯”來源於對英文字“charms”和“harm”(“迷人”和“傷害”)間的諧音關聯,也因為他十分欣賞英國文學形象福爾摩斯。自1925年起,哈爾姆斯便開始在誦詩會和其他前衛活動中顯露頭角,成為蘇聯作協的前身之一“全俄詩人協會”列寧格勒分部的成員,發表了兩本詩集,這是哈爾姆斯在世時唯一發表的兩部“成人”作品。1927年哈爾姆斯同一批實驗文學家,包括亞歷山大·維丹斯基(1900-1941)和詩人尼古拉·扎波羅茨基(1903-1958)一道成立了文學社團“OBERIU”(“真正的藝術”的縮寫),並成為其中堅力量。社團的初衷是為了應和風行歐陸的超現實主義,同時挑戰蘇聯官方推行的沉悶的美學風尚。哈爾姆斯本人也為這種挑戰付出了代價,於1942列寧格勒遭受圍困期間死於獄中,年僅36歲。
現如今,哈爾姆斯已成為俄羅斯當代文學中的獨特的絕響。作家誕生一百年後,俄羅斯文學界再度發現了他的特殊價值。翻譯家馬特維·延科列維奇評價說,“陀、托二人的小說在俄羅斯學校廣為普及,適合於14到16歲的青少年,當你是18歲時,這些小說的確頗有裨益。但到了30歲,一個人總要讀寫不同的東西,而哈爾姆斯就是這樣的作家。讀一讀蘇聯早期的俄語詩歌和美學理論,你會發現,如果這些俄羅斯作品早就被翻譯過來的話,同時代的美國詩文理論就黯然失色,毫無必要了。”
哈爾姆斯直到晚近才為世界讀者知悉,部分原因是作家曾對聖彼得堡文學界的趣味抱持著一種牴觸的態度。雖然作家天性叛逆,獲罪落囚並死於飢餓,但他並沒有向繁榮但道德腐朽的西方大肆拋售所謂蘇聯歷史真相,因而並不符合西方對典型蘇聯詩人的想像。相反,哈爾姆斯的筆下,人們互相躲藏,避免見面(這恰是他作品的主題之一),或陷入種種難以解釋的複雜和無意義的差事中,就像下面的短篇《會面》(The meeting)里的情形:
“現在,有一天一個人去上班
路上他遇到了另一個人,
那人剛買了一條波蘭麵包,
正趕回他的家裡去。
就是這樣,差不多。”
這就是整篇故事。哈爾姆斯用他的典型的結尾句,到底告訴了我們什麼?文學的慣例讀者自然懂得文學的慣例:從作品的第一個句子開始,文字將拓展出一個由行動和主題所編成的網,逐漸引人信服,才可稱之為“故事”。哈爾姆斯則不同,他寧願把這種敘述稱作“事件”或者“事故”,並非本質上的故事。讀者如果不能忍受這種故事帶來的失望,看來也只能找些文不對題的註解聊以自慰了。
“OBERIU”秉承的觀念是預言性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人性的劇烈轉變,這種轉變不僅發生在俄羅斯,也不僅發生在歐洲。“OBERIU”宣告了人文範例的終結,理性理解人性主題的終結。而哈爾姆斯的戲謔風格不過是一種策略,用以展示人性現實的黑暗成分。作品中無法理解的失蹤事件,和漫畫式的暴力場面與20年代社會人性的實質行相不悖。暴力和荒誕描寫貫穿其所有人性主題,其喧鬧的風格表象下,潛藏著作家將其嘲諷美學解構與其後更為黑暗的成分相結合的高度技巧。
國際書界近十年來開始關注哈爾姆斯。喬治·吉卞1997年出版的文選《穿黑外套的人——俄羅斯荒誕文學》和最近出版的尤金·奧斯塔申夫斯基的《OBERIU,俄羅斯荒誕文選》填補了哈氏研究的空白,但同樣也造成一些誤解,因為哈爾姆斯同歐洲戰後興起的這一文學和哲學流派並無共同之處。在新選集《今天我什麼也沒寫》的前言中,譯者小心翼翼地提醒讀者,不需將作家的意圖看成狹隘的政治性抗議,以避免過度簡單化的圖解。“過去的讀者將哈爾姆斯的寫作看成荒誕派文學或政治寓言,這種出自意識形態習慣的‘取景器’自動判定文本的寓意,在哈爾姆斯的作品上附加了太多潛在的誤解。”如果讀者超越了這種扭曲力,則不難發現哈爾姆斯的詩文中真正讓人不安的生命真實,其直接的筆觸會讓讀者誤以為是突發奇想。滲透到簡短文本中的暴烈成分雖然看似隨意,但依然十分可信,正如《街上的一次事故》("An Incident on the Street")開頭的一句:“一個人有一次跳下了電車,但他跳得很糟,讓車給撞上了。”接著,作者用一整頁的篇幅寫了一系列關聯鬆散的類似事件,直到:“最後一切都又正常起來,伊萬·謝苗諾維奇·卡爾波夫甚至落進了一個自助咖啡廳。”在結尾句才第一次提到伊萬·謝苗諾維奇·卡爾波夫,但這並不要緊。事實上,哈爾姆斯意在說明沒有什麼真正要緊,無論是文字上的,還是在現實中,除非我們一定要為之賦予某些意義。又或者,就像哈爾姆斯在系列警句《藍色筆記本》中所說:“旅行時,不要把自己丟給白日夢,要自己幻想,留意每件事情,哪怕是最不起眼的細節。”哈爾姆斯對那些“不起眼的細節”有種宗教般的投入。如果用量合適,這種投入可能令人歡欣鼓舞,或驚恐萬狀,當它延展開來,又可能讓人變得完全麻木。《今天我什麼也沒有寫》集合了哈爾姆斯的詩、戲劇小品、雜文、軼事。譯者說,對西方讀者中不斷擴充的寫作軍團來說,當然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閱讀,以追摹哈爾姆斯所知所感的現代性。
文學作品的魔力需要時間的陶冶歷練,重讀哈爾姆斯的精短篇什,或許會喚醒讓現代人身上感知生活的特殊觸角。
作品欣賞
第10號藍色筆記本有一個紅頭髮的人,沒有眼睛和耳朵。他也沒有頭髮,因而人們是假定地稱他為紅頭髮的人。
他無法說話,因為他沒有嘴。鼻子他同樣也沒有。
他甚至沒有手和腳,肚子他也沒有,後背他也沒有,脊骨他也沒有,任何內臟他也沒有。什麼都沒有!因而不明白這裡談的是誰。
最好我們還是別再談他了。
“真有你的,”門衛大量著一隻蒼蠅,說。“如果給它塗上些乳膠,那它大概就要完蛋。事情就這樣!就用普通的膠水!”
“喂,你這該死的!”一個戴黃手套的年輕人向門衛喊道。門衛馬上就明白了這是在叫他,但他仍繼續看蒼蠅。
“沒聽見正跟你說話嗎?”年輕人又喊。“畜生!”
門衛用指頭按死蒼蠅,並未向年輕人轉過頭來,說:
“喊什麼,你這不要臉的?我聽見哪。用不著喊叫!”
年輕人用手套撣了撣褲子,彬彬有禮地問:
“請問大爺,怎么從這兒上天?”
門衛看了一下年輕人,眯起一隻眼,然後眯起另一隻,然後捋了捋鬍子,又看了一下年輕人,說:
“去,這裡沒什麼好呆的,您一邊去吧。”
“對不起,”年輕人說。“我這是來半件急事的。那兒連房間都替我準備好了。”
“好吧,”門衛說。“出示你的票。”
“票不在我這裡;他們說這兒會放我進去的。”年輕人說,直盯著門衛的臉。
“真有你的!”門衛說。
“怎么?”年輕人問。“您放我進去?”
“好吧,好吧,”門衛說。“您進去吧。”
“怎么走呢?往哪去?”年輕人問:“我不認路哇。”“您要去哪?”門衛說,做出一副嚴厲的面孔。
年輕人用手掌掩住嘴,非常輕地說:“上天!”
門衛傾身向前,為了站得更穩些又邁出了左腿,他仔細地望了一眼年輕人,厲聲問:
“你幹嘛?裝什麼蒜?”
年輕人笑了一笑,抬起戴著黃手套的手,在頭頂上方一揮,就突然消失了。
門衛聞了聞空氣。空氣中有股羽毛燒焦的味。
“真有你的”門衛說,他敞開短大衣,撓了撓肚皮,朝年輕人站過的地方啐了一口,又慢慢走回自己的門房。
科拉特金去找季卡凱耶夫,碰上他沒在家。
而季卡凱耶夫這時正在商店裡,他在那兒買了肉、糖和黃瓜。科拉特金在季卡凱耶夫的門前轉悠了一陣,已打算寫個條子,突然他想到,季卡凱耶夫本人正走來,手裡提著一個漆布口袋。科拉特金見到季卡凱耶夫,就向他喊道:
“我已經等了您整整一個鐘頭!”
“不對,”季卡凱耶夫說。“我離家總共才二十五分鐘。”
“這我不知道,”科拉特金說。“反正我已經等了整整一個鐘頭。”
“別撒謊!”季卡凱耶夫說。“撒謊可恥。”
“最仁慈的閣下!”科拉特金說。“勞請您換副表情。”
“我以為------”季卡凱耶夫剛開頭,科拉特金就打斷了他。
“如果您以為------”科拉特金說,可季卡凱耶夫立即打斷了他,說:
“就你好!”
這句話惹惱了科拉特金,於是他用手指按住一個鼻孔,用另一個鼻孔向季卡凱耶夫噴鼻涕。這時季卡凱耶夫從袋子裡掏出一根最大的黃瓜,用它向科拉特金的腦袋打去。科拉特金雙手抱住腦袋,倒下,死了。
如今商店裡就賣這樣的大黃瓜!
一位老婦人由於過分的好奇從視窗墜落下來,摔傷了。
從視窗探出另一位老婦人,她開始向下望那摔傷的,但由於過分的好奇也從視窗墜落下來,摔傷了。
然後從視窗墜落下第三位老婦人,然後是第四位,然後是第五位。
而第六位老婦人墜落時,我已厭倦看她們,於是我去了馬爾采夫斯基市場,在那兒,據說,有人給了一個瞎子一條針織頭巾。
謝苗*謝苗諾維奇戴上眼鏡,望著松樹,他看見:松樹上坐著一個農夫,正向他揮舞拳頭。
謝苗*謝苗諾維奇摘下眼鏡,望著松樹 ,看見松樹上並未坐著誰。
謝苗*謝苗諾維奇戴上眼鏡,望著松樹,看見松樹上坐著一個農夫,正向他揮舞拳頭。
謝苗*謝苗諾維奇摘下眼鏡,又看見松樹上並未坐著誰。
謝苗*謝苗諾維奇又戴上眼鏡,望著松樹,又看見松樹上坐著一個農夫,正向他揮舞拳頭。
謝苗*謝苗諾維奇不情願相信這一現象,他認為這一現象是視錯覺。
從前有一個木匠。他叫庫沙科夫。有一回他離開家,去一家小鋪想買些乳膠。
化凍了,大街上非常滑。
木匠走了幾步,腳下一滑就摔倒了,磕破了腦門。
“唉!”木匠說著,站起來,來到藥房,買了塊膏藥貼在腦門上。
但當他走到大街上,剛走幾步,他腳下一滑又摔倒了,磕破了鼻子。
“唉!”木匠說,來到藥房,買了塊膏藥貼在鼻子上。
然後他又來到大街上,又腳下一滑摔倒了,磕破了腮幫。只好又來到藥房,用膏藥貼上了腮幫。
“這樣,”藥房掌柜對木匠說。“您經常摔著磕著,我建議您多買上幾貼膏藥。”
“不用,”木匠說。“我再也不會摔倒了。”
但當他走到大街上,腳下一滑又摔倒了,磕破了下巴。
“可惡的冰!”木匠叫道,又跑回藥房。
“瞧見了不是,”藥房掌柜說。“您又摔倒了。”
“不!”木匠叫道。“我什麼也不想聽!快給我膏藥!”
藥房掌柜給了膏藥;木匠貼上下巴,跑回家去。
可是家裡的人認不出他,不放他進屋。
“我是木匠庫沙科夫!”木匠高叫。
“隨你說去!”屋裡的人回答,並用掛鈎和鐵鏈鎖死了門。
木匠庫沙科夫在台階上站了一會兒,啐了一口,又向大街走去。
一個細脖子的人鑽進一隻箱子,隨後合上蓋,開始有些喘不過氣來。
“瞧,”細脖子的人一邊艱難地喘氣一邊說。“我在箱子裡喘不過氣來,因為我的脖子細。箱蓋合上了,空氣進不到我這兒來。我會憋死的,但我無論如何不打開箱蓋。我將慢慢死去。我將見到生與死的搏鬥。在同等條件下正在進行不正常的戰鬥,因為死亡自然會獲勝,而注定死亡的生命只是枉然地在與敵人搏鬥,直到最後一分鐘也不放棄徒勞的希望。在此刻進行著的這場搏鬥中,生命會知道自己取勝的方式:為此生命應當強迫我的雙手去打開箱蓋。我們看著:誰勝誰負?只是這樟腦味實在難聞。如果生命獲勝,我就把菸草散在箱子裡的東西上------開始啦:我再也無法呼吸,我死了,這很清楚!我已經沒救啦!已沒有任何崇高的東西在我腦子裡,我正在窒息!------”
“哎喲!這是什麼?此刻是出了什麼事,但我無法明白究竟出了什麼事。我看見了什麼或者聽見了什麼------
“哎喲!又出了什麼事?我的上帝,我喘不過氣來,。看樣子我正在死去------
“這又是什麼?為何我在唱歌?仿佛,我的脖子痛------可箱子在哪裡?為什麼我看到了我房間裡的一切?好象我正躺在地板上!而箱子在哪裡?”
細脖子的人從地板上爬起來,看了看四周。哪兒也沒有箱子。椅子上和床上堆滿了從箱子裡掏出來的東西,可箱子哪兒也沒有。
細脖子的人說:
“就是說,生命以一種我所不知的方式戰勝了死亡。”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米亞索夫在市場上買了根燈芯,攥在手裡往家走。半路上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丟了燈芯,就去商店買了150克波爾塔瓦香腸。然後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又去牛奶公司,買了一瓶牛乳酒,然後到小攤上要了一小杯克瓦斯,喝完了便去排隊買報紙。隊伍很長很長,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排了不下二十分鐘,可他排到報販子跟前時,報紙剛好在他眼皮底下賣完了。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原地踱了一陣,才起步回家,可路上他丟了牛乳酒,於是折回麵包房,買了一隻法國白麵包,結果又丟了波爾塔瓦香腸。
現在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動身回家了。可他在路上跌了一跤,丟了法國白麵包,還摔斷了自己的夾鼻眼鏡。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回到家時非常惱火,一下倒在床上,但久久未能入睡,而他剛一睡熟,就又夢到自己似乎弄丟了牙刷,正在用一隻燭台刷牙。
馬爾科夫扒掉靴子,喘了口氣,躺倒在長沙發里。
他很想睡覺,可他剛閉上眼睛,睡覺的願望就立刻消失了。馬爾科夫睜開雙眼,伸手去取一本書,可這時睡意又向他襲來,於是書還沒夠著,馬爾科夫就躺下身重新合上了眼睛。誰知眼睛剛閉上,睡意又一次消失了,馬爾科夫的意識變得格外清晰,甚至能心算二元方程的代數題。
馬爾科夫難受了半天,不知乾什麼好:睡還是不睡?他痛苦不堪,既恨自己,也恨自己這間屋,不得已,他穿上大衣,戴好帽子,抓起手杖,來到戶外。習習清風使馬爾科夫定下神來,他感到心裡高興了些,想回到自己屋裡去了。
一邁進房門,他立刻感到一陣愜意的疲倦,直想睡覺。
可是他剛躺進沙發合上眼,——睡意頃刻間化為烏有。
馬爾科夫不勝狂怒,從沙發里跳起來,沒顧上穿衣戴帽,就朝塔夫利切斯基公園方向奔去。
費佳在奶油缸跟前徘徊了很久,終於瞅準妻子彎下腰去修腳趾甲的空隙,飛快地一下從缸子里摳出全部奶油,塞進自己嘴裡。合上缸蓋的時候,費佳無意間弄出了響聲。妻子立刻直起腰,看到缸中空無一物,就用剪子指著空缸,厲聲問:
“缸里的奶油沒了,哪兒去了?”
費佳現出吃驚的模樣,伸長脖頸探頭看了看缸子。
“奶油在你嘴裡,”妻子用剪子指著費佳說。
費佳搖頭否認。
妻子說:“啊,你光搖頭不哼聲,是因為你嘴裡塞滿了奶油。”
費佳睜大了眼睛,朝妻子擺動雙手,仿佛在說:“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沒有的事!”可妻子說:
“你撒謊。張開嘴。”
費佳只是。
“張開嘴。”妻子又說了一遍。
費佳叉開手指,嘴裡一陣嗚嚕,似乎在說“噢,對了,我完全忘了;現在就去”,然後站起身,打算走出房間。
“站住!”妻子一聲大喝。
但是費佳加快腳步,消失在門外。妻子起身去追,但到門外停下,因為他赤身裸體,這副樣子是不能到走廊上去的,那裡常有這套房子裡別的住戶來回走動。
“溜了,”妻子坐在沙發上說道,“滾他的蛋!”
費佳呢,他順著走廊來到一扇寫有“嚴禁入內”字樣的門前,推開門走進屋去。
費佳走進的這間房子又窄又長,窗戶用一張髒紙遮住。屋裡右側靠牆放著一隻斷了腿的髒沙發,窗前有一張用木版拼成的桌子,它一邊支在床頭柜上,另一頭搭著椅子背,牆上訂著一塊兩合板架子,上面擺的不知是什麼東西。屋子裡別無一物,如果不算沙發上躺著的那個人。此人面有菜色,身穿一件又長又破的咖啡色長禮服和一條黑色土布褲,從褲筒里伸出兩隻洗得乾乾淨淨的赤腳。此公沒有睡覺,凝神望著來人。
費佳鞠了一躬,併攏腳跟行了禮,用手指從嘴裡掏出奶油,遞給躺著的人看。
“一個半盧布”。房間主人說,沒改變姿勢。
“少了點兒”費佳說。
“不少。”房間主人又說。
“那么好吧。”費佳說著,從手指上扒下奶油,放到架子上。
“明天早晨來拿錢。”房間主人說。
“噢,您這是說什麼!”費佳叫起來。“我可是現在就要用錢呀。再說總共才一個半盧布------”
“你滾吧。”房間主人冷淡地說,於是費佳踮著腳尖跑出房間,小心地隨手關上了門。
“哎,我說,你的鼻子別使勁呼哧!”潘金對拉庫金說。
拉庫金皺起鼻子,不樂意地看了潘金一眼。
“看什麼?不認識嗎?”潘金問。
拉庫金吧嗒一下嘴,在圈椅里氣憤地轉過身去,看著另一個方向。潘金用手指彈著膝頭,說:
“這個傻瓜!真該照後腦勺給他一悶棍。”
拉庫金站起來朝外走,可潘金迅速地跳起來,趕上拉庫金說:
“站住!往那兒跑?最好還是坐下,我給你看一樣東西。”
拉庫金停下腳步,將信將疑地看著潘金。
“怎么,不信?”潘金問。
“信。”拉庫金說。
“那你就坐在這,坐在這把圈椅里。”潘金說。
於是拉庫金坐回自己那把圈椅。
“瞧你,”潘金說,“幹嘛像個傻瓜似的坐在椅子上?”
拉庫金挪動著雙腳,飛快地眨巴起眼睛來。
“別眨眼。”潘金說。
拉庫金不再眨眼,卻弓起背,把頭縮進肩膀里。
“坐著嘍。”潘金說。
拉庫金繼續弓著背坐在那裡,腆起肚皮並且伸長了脖子。
“哎呀,”潘金說,“真該給你一個耳光!”
拉庫金打了一個嗝兒,鼓起腮幫,然後小心地把氣從鼻孔呼了出來。
“嘿,我說,鼻子別呼哧!“潘金對拉庫金說。
拉庫金把脖子伸得更長,又飛快地眨起眼睛來。
潘金說:
“拉庫金,你要是再眨眼睛,我就踹你的胸口。”
為了不再眨眼,拉庫金扭著下巴,同時把脖子伸得更長,腦袋朝後仰去。
“呸,你這副樣子多讓人討厭,”潘金說,“嘴臉像母雞,脖子發青,簡直是個醜八怪。”
這時,拉庫金的腦袋往後仰得越來越厲害,終於失去控制朝後折去。
“這是什麼鬼名堂!”潘金大叫起來。“這又是在變什麼戲法?”
如果從潘金那個角度看著拉庫金,你就會感覺到,拉庫金坐在那裡,像是根本沒有腦袋。拉庫金的喉結朝上凸起,你不由得會把它當成一隻鼻子。
“哎,拉庫金!”潘金說。
拉庫金一言不發。
“拉庫金!”潘金又喊了一聲。
拉庫金沒有回答,繼續一動不動地坐著。
“是這樣,”潘金說。“拉庫金咽氣了。”
潘金劃了個十字,踮起腳尖走出房間。
14分鐘之後,從拉庫金的軀體裡鑽出一個小精靈,它惡狠狠地看了看潘金不久前坐過的地方。可這時從帽子下面走出高大的死神,它一把拽住拉庫金的靈魂,引著它直穿過房間和牆壁不知所往了。拉庫金的靈魂跟在死神後面奔跑,惡狠狠地、一刻不停地四處張望。但這時死神加快了腳步,於是拉庫金的靈魂蹦蹦跳跳、磕磕絆絆地消失在遠方拐角處。
彼得羅夫:哎,卡馬羅夫!咱們捉蚊子吧!
卡馬羅夫:不,我還沒這份打算。咱們最好來捉貓!
竟有這樣一件事!我不知道該怎么辦。我完全搞混了。根本無法弄清楚。
你們自己來判斷一下吧:我當了貓舍的看門人。
他們給了我一副皮手套,以防貓抓破我的手指,還命令我把貓安置到各自的籠子裡,並在每個籠子上標明——此貓叫什麼名字。
“好吧,”我說。“那么這些貓都叫什麼名字呢?”
“你看,”他們說,“左邊的那隻貓叫做瑪什卡,挨著它的這只是普羅恩卡,下只叫布邊奇克,這隻叫楚爾卡,這隻叫穆什卡,這隻叫布爾卡,這隻叫什圖卡圖爾卡。”
剩下我一個人和貓在一起的時候,我想,我先抽支煙,然後再把這些貓裝進籠子。
於是我一邊抽菸,一邊望著貓。
一隻貓在用爪子洗臉,另一隻望著頂棚,第三隻在房間裡散步,第四隻失聲怪叫,還有兩隻貓兒在互相埋怨,只有一隻走到我跟前,咬了我的腳一口。
我跳將起來,連菸捲都扔了。
“好啊,”我大叫,“真是只壞貓!你甚至連貓都不象。你是普羅恩卡還是楚爾卡,也許你是什圖卡圖爾卡?”
我突然明白過來,我已經把所有的貓搞混了。哪一隻叫什麼名字我根本不知道了。
“嗨,”我大叫,“瑪什卡!普羅恩卡!布邊奇卡!楚爾卡!穆爾卡!布爾卡!什圖卡圖爾卡!”
可是貓們一丁點兒也不理會我。
我沖它們嚷道:
“咪咪咪!”
這下所有的貓都立刻朝我扭過頭來。
可下一步怎么辦?
幾隻貓都湊到窗台上,背衝著我,朝窗外張望。
現在它們都蹲在那兒,可哪只是什圖卡圖爾卡,哪只是布邊奇克呢?
我根本弄不清楚。
我想,只有非常聰明的人才能猜中,哪一隻貓叫什麼名字。
桌上放著一隻箱子。
幾隻動物走到箱子跟前,看一看,嗅一嗅,舔一舔。
箱子突然間——一、二、三——折開了。
從箱子裡面——一、二、三——竄出一條蛇。
動物們大驚失色,四處逃竄。
只有刺蝟不害怕,它朝蛇撲過去,結果一、二、三——把蛇咬死了。
然後它坐到箱子上叫道:“喔——喔——喔!”
不對,不是這么叫的!刺蝟叫道:“汪——汪——汪!”
不對,不是這么叫的!刺蝟叫道:“咪——咪——咪!”
不對,還是不對!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叫的了。
你們誰知道刺蝟怎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