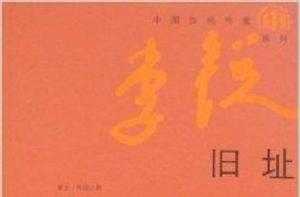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當代作家李銳系列:舊址》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李銳,男,1950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四川自貢。1966年畢業於北京楊閘中學。1969年1月到山西呂梁山區插隊落屍,先後做過六年農民,兩年半工人。1977年調入《山西文學》編輯部,先後擔任編輯部主任、副主編。曾任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現為山西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2004年3月獲得法國政府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自197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迄今已發表各類作品將近兩百萬字。系列小說《厚土》為影響較大的作品,曾獲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並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出版有小說集《丟失的長命鎖》、《紅房子》、《厚土》、《傳說之死》;長篇小說《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銀城故事》;散文隨筆集《拒絕合唱》、《不是因為自信》、《網路時代的方言》。和外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一樣,李銳的作品也曾先後被翻譯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蘭文、越南文等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
文摘
第一章
一
一九五一年公曆十月二十四日,舊曆九月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
那一天上午,英姿勃發的銀城市軍管會主任王三牛師長滿懷激情、滿懷勝利的喜悅,歷史性地舉起手來朝著無邊的濛濛秋雨劈砍過去,用他濃重的膠東口音宣布:
“把反革命分子們押赴刑場!立即槍決!”
不知是被這個命令震驚了,還是對這個過分拗口,過分突兀的膠東口音感到陌生,長江上游銀城市的十萬市民二十萬隻眼睛,一動不動地停在王三牛師長激動而喜悅的臉上。緊接著,行刑隊長劉光弟更加激動的悽厲的口令聲,劃破了這冰冷而陰濕的驚呆。一百零八個反革命分子,一百零八面插在腦後的白色的亡命牌,被胸前掛滿彈匣的威武的解放軍戰士推搡著拖拽著,擁向警戒線包圍著的老軍營校場對面的一截依山而砌的石牆。石牆上濕漉漉地長滿著青苔。剎那問,這一百零八面白晃晃的亡命牌,在那些柔綠的青苔上聚起一股陰森肅殺的鬼氣。一百零八這個數是王三牛師長親自選定的,呈報上來的該殺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單遠遠多於一百零八,也許因為是山東人對於梁山好漢一百單八將的偏愛,王三牛師長親自為這次最盛大的“鎮反”大會選定了這個數字。行刑隊長劉光弟暗自核對過,在這一百零八人當中有三十二個人姓李,幾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當中所有的成年男子。臨行刑的前一天,劉光弟曾向軍管會遞交“請戰書”,要求由他來打響第一槍,親手處決自己的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門人李乃敬。隨著劉光弟清脆嘹亮的第一槍,大義滅親的子彈從美式卡賓槍的槍口中無情地呼嘯而出,李氏家族掌門人李乃敬的天靈蓋像一塊破碎的瓦片,飛進到青苔遍布的石牆上,“瓦片”上飛旋的亂髮沾滿了鮮紅的血和粉白的腦漿。緊隨其後,是一模一樣的一百零七次的塗染,那長長的一段石牆變得仿佛霜染秋林似的斑斕……順著這段石牆向右走不遠,就會看見穿城而過的銀溪,河水沿著山腳拐了一個彎,留下一潭靜靜的墨綠。山壁上有詞聖蘇東坡手書的三個大字:聽魚池。當槍聲大作的當兒,聽魚池平靜的墨綠上瞬時泛起一陣細碎而倉皇的銀白。而後,一夜秋雨洗淨了牆上黏糊糊的血紅和粉白,也洗淨了那令人膽戰心驚的一百零八顆子彈的呼嘯聲。李氏家族在銀城數百年的統治和繁衍終於結束。遍布銀城街頭巷尾的幾十座李氏家族的大大小小的功德坊、進士坊、節孝坊,從此失去了往日的榮耀和威嚴,面對著行人大張著驚恐而醜陋的嘴。後來,這個刑場被改建成了燈光籃球場,可是嘭嘭落地的球聲,和為了搶球而扭成一團的人體,總是讓李氏家族的女人們想起卡賓槍的轟鳴和那一百零八具橫陳的屍體;總是讓她們想起一九五一年公曆十月二十四日,舊曆九月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
這一天,李氏家族中惟一的一個成年男子沒有面對行刑隊,他的名字叫做李乃之,和被槍決的李乃敬以堂兄弟相稱。當年李乃之曾做過一任中共地下黨銀城市委書記,以後又升任過省委書記。此刻,他完好的額頭上戴著一頂蘇式的呢制鴨舌帽,正帶領著新中國第一個拖拉機手訓練班的第一期畢業生,在北京東郊坦蕩的原野上駕駛著“史達林”55型拖拉機,在震耳欲聾的馬達聲中翻開新中國的沃野。巨大的鏵犁翻起沉睡的土地,把一張張欣喜若狂的黃色面孔擺滿在爽朗的秋陽當中。兩架攝影機和許多架照相機,正匆匆忙忙地把這個“鑄劍成犁”場面納入鏡頭,這些鏡頭後來果然作為新中國建設的歷史性成果而載人各種各樣的文獻。
當這些人在轟鳴和忙亂之中被歷史性地納入鏡頭的時候,李乃之的長子,李氏家族按族譜記載的第六十九代子嗣中的一個兒子,降生在實驗農場簡陋的醫務室的木床上。他還沒有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已經給他起好了名字,不再按照李氏祖上選定的那十個字起名排輩,那都是封建老一套,如今革命勝利定都北京,這孩子不論是男是女都叫李京生。在李京生呱呱落地的當兒,實驗農場水塔上的兩隻高音喇叭,為了慶賀新中國第一批拖拉機手的畢業,正以最高、最大的音量播送著一支充滿了濃厚的時代氣息,充滿了勝利的喜悅和激動的歌。歌里唱的是“土改”勝利,分到地主財產的農民的快樂:
三頭黃牛,一呀么一匹馬,
不由我這趕車的人兒
笑呀么笑哈哈。
往年,這個車呀,
咱窮人哪會有呀,
今年呀嘿,
大軲轆車呀,軲轆軲轆轉呀,
大軲轆車呀,軲轆軲轆轉呀,
轉呀轉呀轉呀
嘟——噠,
轉到了咱們的家!
後記
從冬天到冬天
別人寫長篇是因為篇幅長,我不是,我寫長篇是因為時間太長。一部不足二十萬字的長篇,從冬天寫到冬天,斷斷續續地花了一整年的時間。於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帶進到小說里來,文字之間仿佛也有了四季的節奏和差別。但因為是從冬天開始,又是在冬天結束的,小說結尾的時候我一直沉浸在寒冬之中;真冷,是那樣一種心脾寒徹的冰冷……看著我的人物一個個地在筆下死去,看著我慘澹的故事在冬天的寒風中結束,難禁的悲哀深深地浸泡在時間的冷水之中……
我沒有想到這場和祖先與親人的對話竟是這么長。
我沒有想到這場對話竟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天。
我沒有想到當這場對話結束的時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屬於每一個活著的和死去的中國人。
有人說:冬天既然來了,春天也就不會遠了。可我的故事卻是在冬天開始,又是在冬天結束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於家中
追逐白馬
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0年有個叫公孫龍的趙國人,給世人出過一道難題,說是“白馬非馬”。公孫龍在世的時候,曾做過平原君趙勝的門客,深得平原君的厚愛。但作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孫龍在中國歷史上一向不大被人看重,連莊子也說他是“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但事實上,在公孫龍以後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人時不時的要陷入在“白馬非馬”的尷尬之中。每當人們像貓一樣咬著自己的尾巴旋轉起來的時候,就會在那“魔圈”的外邊聽見公孫龍犀利詭譎的冷笑聲。
白馬非馬。白馬真的不是馬?那紅馬、黑馬呢?那到底什麼才是馬?我們不能問,再問下去就又會聽到那個悠長的兩千多年的冷笑聲。
中國文人曾經在“西方”還是“中國”,“現代”還是“傳統”之間旋轉了一個多世紀。我們說這個文化不好,那個文化好。為此,我們鍥而不捨,舉出種種言之鑿鑿的論據,在對“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們終於發現自己奔波在一條環形跑道上。這個發現有些令人尷尬。當我們汗流浹背氣喘吁吁地相互打量的時候,就會聽見有個人在笑,笑得犀利而又詭譎。
他一邊笑,一邊說:白馬非馬。
近一個世紀以來,在這條環形跑道上,也跑著我們這弄文學的一群。大家的體力、姿勢各異,穿戴著的衣帽鞋襪也各異,心裡懷著的目標還是各異。但因為是弄文學的,就不免比別的奔跑者多了些舞文弄墨的姿態,多了些文人中慣有的爭吵,多了些騷客間常見的互嘲。爭吵和嘲笑的中心,不外乎你弄的不是好文學,而我是;不外乎真正的文學或文學的革命自今日始,自本人足下始,而非自昨日,自他人足下始;不外乎老子今天第一,爾等小子們差矣!當大家這樣爭吵,這樣嘲笑,這樣排一論二的時候,都忘了那是一條環形跑道,大家都在這條環形跑道上指著對方說“爾非馬也”。可當吵鬧與喧囂的熱浪翻滾過去之後,在那條環形跑道的上空就會聽見一聲悠長而又犀利的冷笑。這笑聲並非是對誰先誰後誰對誰錯的裁判。
他一邊笑,一邊說:白馬非馬。
其實,冷靜下來想一想,在這條環形的跑道上,原本就沒有什麼競賽。有的只是我們自己和自己長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難辨的足跡,重重疊疊,模模糊糊,不分你我,無論先後。看著那足跡,我們只能知道,有許多人曾經走來,又有許多人曾經走去。公孫龍說:白馬非馬。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於家中
序言
這套叢書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從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開始,到最近的一些隨筆為止,大致選了二十年以內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嚴格的說,我的文學創作也是從《厚土》開始的。在這之前的十二三年雖然也寫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學習和準備。
我為自己的寫作定下一個標準: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但是,為什麼在全球化的時代強調使用方塊字?怎么才能算是深刻?用什麼樣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自己?這幾個問題一問,就知道這個看似簡單的標準,其實很苛刻。用這個標準衡量自己這八本書,我不能說真的做到了,只能說還算是一種自覺的追求。
本來文學創作是個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於類似和獨創的不同。但是我相信,無論多么獨特、獨創的寫作者,他都無法使自己分身於歷史和時代之外。從某種意義上說,寫作常常是對歷史和時代的反省與反抗,是獨自一人對生命深情的抒發和挽留。諷刺的是,歷史會讓反抗和反省變得多餘,生活會讓抒發和挽留變成自作多情。因為,無動於衷是歷史的基本屬性,變幻無常是生活的本來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後的“新時期文學”一起成長起來的。當我們在一波又一波的主義和潮流中模仿和“創新”的時候,身邊的這個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從天安門廣場上高舉毛主席語錄本狂呼萬歲的紅海洋,到燈光廣場上揮動螢光棒淚流滿面的追星族;從千百萬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到億萬農民像潮水一樣湧向城市去打工;從所謂的國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崗工人、沒了土地的農民;從排著長隊用糧票、布票購買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滿目的超級市場、名品專賣店;從“深挖洞,廣積糧”的自我封閉,到高樓林立、汽車塞路的國際化流行病;這一切都是我們親歷親見的歷史和生活。眼前的這個世界變化之大,之劇烈,之深刻,說翻天覆地沒有半點誇張。在所謂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國,讓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見絀。我們已經從狂熱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獄,一步跨進了權力和金錢的狂歡節。在這個狂歡節上被權力剝奪的精神侏儒們,卻又同時依靠金錢變成了消費巨人。有人宣稱,這是一個歷史終結於消費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經典被讀物取代,獨創被複製取代,欣賞被刺激取代。總之,在“作者死了”之後,文學的死期也就不遠了。可是在我看來,文學是人記錄自己生命體驗和想像力的一種本能。這種本能,在沒有文字之前被人們口口相傳,在有了文字之後人們就用文字記錄。就像食慾和性慾一樣,這樣的生命本能並非專屬於某一時代。真正的文學從來都是出於內心的渴望和需要,權力的剝奪,金錢的驅使,或許可以得逞於一時,甚至得逞於一個時代,但它們從來也沒有能得逞於永遠。刻骨的生命體驗,勃發的想像力總是會從岩石的縫隙中生長出來,總是會在大漠的腹地匯聚成茂盛的綠洲。真正的創作者從來用不著向歷史撒嬌,非要要求一個適合文學生長的“盛世”。生活本來就是泥沙俱下的,歷史也從來就不可能幹淨。唯其如此,才滋養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學。
在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幾十年來除了讀書就是寫作,很單純也很單調。寫的東西也簡單,除了小說就是散文隨筆。如此這般,在單純和單調之中一晃三十載,眨眼間,曾經的熱血青年忽然白髮雜生。真快。快得來不及感嘆。所謂的反省和反抗,在落到紙面的同時,也漸漸變成一個人的獨白。到這時候才體味出什麼叫“創作是個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個人把沙子扔進黑夜,也很像那隻銜來石頭填海的笨鳥。
牢記著歷史無動於衷的基本屬性。我不想給自己的選擇塗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個道德的高台階站上去。義無反顧的自生自滅是用不著宣言的。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於草莽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