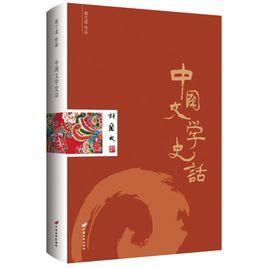內容簡介
胡蘭成於1974年受聘到中國文化學院講學,1976年返回日本僑居。彼時,仙枝、朱天文、朱天心等一群年輕人正通過胡蘭成的書信指導,在文壇領袖朱西寧的直接引導下,辦起了文學刊物《三三集刊》,開始追求文學理想。為了鼓勵青年寫作者,胡蘭成親自撰文指導,遂有此書《中國文學史話》,實際上是胡蘭成給仙枝、朱天文等年輕弟子的文學教材。
作者簡介
胡蘭成(1906—1981 ),出生於浙江嵊縣胡村,卒於日本東京。青年時代曾於燕京大學旁聽課程,後在浙江、廣西等地任教。抗戰時任《中華日報》總主筆等職,期間與張愛玲結婚。1974年受聘為台灣中國文化學院終身教授,其文學才能影響深遠,日本和中國的部分作家頗受其影響。晚年與唐君毅、錢穆、牟宗三、徐復觀、岡潔、湯川秀樹、川端康成等人過從甚密。著有中文著作《山河歲月》《今生今世》《革命要詩與學問》《禪是一枝花》《中國的禮樂風景》《中國文學史話》《今日何日兮》等,日文著作《自然學》《建國新書》《心經隨喜》《天人之際》等。
讀者評價
——我很喜歡看胡蘭成講魯迅,他說魯迅那會兒批判中國,等於姑娘早上梳妝打扮,梳著梳著突然不高興,覺得鏡子裡不好看,覺得不開心。這個對極了。魯迅看了一定會覺得給他說中了。(畫家陳丹青)
——胡蘭成的《中國文學史話》是所有從事文學寫作者的必讀書。(詩人、作家侯磊)
編輯推薦
第二次大戰後,世界性的產業國家主義社會的龐大物量,最後把人的智慧與感情都壓滅,家庭之內斷絕,人與人斷絕,對物的感情斷絕,連到言語的能力都急劇地退化了。文學上已失了在感情上構成故事的才能,只可以犯罪推理小說的物理的旋律來吸引讀者。連這個也怕麻煩了,繼起的是男女肉體的穢褻小說,但這也要過時,因為穢褻雖不用情,但也要用感,現代人是連感官也疲憊了。
目錄
代序/小北
上卷
禮樂文章
天道人世
對大自然的感激
忠君
好玩與喜反
中國文學的作者
文學與時代的氣運
堯典與虞書
文體
魁星在天
論文的時代
新情操的時代
士弱民猶強
今日何日兮
文學的使命
論建立中國的現代文學
下卷
周作人與路易斯
路易斯
周作人與魯迅
論張愛玲
張愛玲與左派
隨筆六則
閒記
評鹿橋的《人子》
來寫朱天文
讀張愛玲的《相見歡》
關山月
女人論
小北序
代序
原要請陳丹青先生作序,惟出版在即,丹青先生又忙。三三諸人,也各有所忙,亦恐等不及。
去年冬天,木心先生講述的《文學回憶錄》出版影響頗大。此前,我費盡心思尋求胡蘭成先生1976年夏天在朱家隔壁為一群文學青年講述《易經》時的授課錄音,遂因此聯絡上許多親炙過胡蘭成先生的弟子。可惜時至今日,錄音資料多已不存,而三三諸君當年都年輕,筆記也無。
遲後的1989年,木心在紐約為陳丹青等一群旅居海外的藝術家講述世界文學史。這在精神血緣上,與胡先生之與三三後學幾近相似。這部《中國文學史話》雖不是授課記錄,但也算那一段時期里胡先生對文學的反省。如今得以再版,可與《文學回憶錄》成為雙壁。胡蘭成的套路,自與木心有別,但他們兩位身上流淌著的都是傳統的血液,似有一種相應。一在日本,一在美國,在文學的闡述上遙相呼應而又互相彌補。這在我看來,即是陳丹青先生所謂的文學上的血親之緣。
因蔣經國不容,胡蘭成先生於1976年11月返回日本僑居。此後,他與台灣的年輕人書信往返不斷,通過他的書信指導,朱天文、仙枝、馬叔禮等年輕後輩由朱西寧直接指導,創辦《三三集刊》,追求起文章建國的大志。為激勵青年,胡先生親自撰文指導,遂有此書《中國文學史話》。實際上此書亦可說是胡先生寫給三三後學的文學教材。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士志於道而游於藝,中國文明向來是“道藝一體”。此所以胡蘭成先生常說禮樂文章,既言文章華國,又說文章小道,志士不為。前此,北京晨報一記者問我:“你覺得胡蘭成與當下的作者有什麼不同?”其實這本沒有可比性,但要說胡蘭成身上的光亮,更多的在於他對傳統的一脈相承,並能夠隨處翻新。不用說當下的作者,就是民國以來的近代知識分子,亦鮮少有人能真正如胡蘭成這般將文史哲諸學問熔於一爐。所以胡先生雖談文學,豈又止是就文學談文學?
“詩言志,歌永言。”文章不過是興,文學亦不過是個載體。胡蘭成先生念茲在茲的是中國的乃至世界的文藝復興,而所謂文藝復興亦仍不過是人世的大興,為的是要藉此施展他遠大的政治抱負。所以“三三”,其實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文學組織,甚至胡先生原要的並不是文學。它是《苦竹》還魂,是《風動》之延續。
胡蘭成一生關心的是政治,而他一生際遇離不開文學。1944年10月,胡蘭成與張愛玲在南京創辦《苦竹》月刊,除張愛玲、炎櫻、路易士等人的支持,其餘文章皆胡先生一人化名撰寫,所談者無非國事。《苦竹》月刊因戰亂及胡張二人感情的變化僅維持到第三期。
至1971年,由胡蘭成主導的梅田學堂機關報發行,他為之題名,並意氣風發地寫下創刊說明:“‘風動’出自‘四方風動’,即風席捲四方,變成大風,將撼動世界。”此年胡已六十六歲,卻仍是滿腔沒有名目的大志,天下事猶未晚似的。他在《風動》創刊號上發表《天下有新事》,縱論國際政治問題。此後《風動》每一期必有胡蘭成先生的高論,乃至他與數學家岡潔的《世紀的對談》都在此連載發表。《風動》月刊自1971年至1973年發行到第二十九期。(之後更名為《いき》,與胡之關係漸遠。)
胡先生的弟子們所辦的《三三集刊》雖不是他親自參與,卻仍是昔年理想的延續。他說中國文學的作者,一種是士,一種是民。士的文學即是道藝一體的文學,文學不光是小情小調的抒發,而是要為古來的修齊治平所用。所以在胡蘭成的構想中,三三有著士的胸襟與抱負,在日漸西化的時代里,他仍堅信“喚起三千個士,中國就有救。”所以他通過三三的文學活動,廣結善緣,曾寫信給三毛、陳若曦等人。
胡蘭成先生從小就有一種士的情懷。他出身於江南農村,祖父是太學生,父親頗有詩才,又自幼受他母親的民間詩教。《詩經》言興,民間最無名目的口頭吟唱,卻是最好的興。如他母親的順口所念,胡不相干,無邊無際,卻是音韻俱足。青年時代的胡先生崇拜過魯迅,但他能毫不間然地平視魯迅,他之能淡然地評魯迅,皆在於他有高過魯迅的士人情懷。他的早期文章,私淑梁漱溟,而他日後與梁漱溟相交,也能視如平人。前此有人問,同是紹興人,胡蘭成與周作人、魯迅之差別在哪裡,我以為他們最大的分別在於士的情懷。周作人與魯迅是典型的近代知識分子,是城裡人。而胡蘭成是農家子弟,正因為在民間的底處,卻更好地保存了士的元氣,沐浴了五四新風,而沒有受五四之害。
《中國文學史話》開篇即辯明了東西文學之始分,他說“中國文學是人世的,西洋文學是社會的。”學界有人批評胡先生妄議西方,而他真正是西洋人的知音。他說“人世是社會的升華,社會惟是‘有’,要知‘無’知‘有’才是人世。”這樣的話咋聽似不對,細細品味,卻要驚為天人之語。胡先生引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則”,一下子解明了文章之道。大自然的法則,即是文明的法則,亦即是人世運行不悖的法則。“有限的社會而涵無限的風景,這是人世。”
書中談及日本的部分,加上之前《建國新書》的《文章篇》,是近現代以來,中國人對日本文學最高的評論。而胡蘭成先生對中西文學所持的態度,正和他的文學史觀一致,有著極高的境界,非盡能被傳統割裂了的今日文學者所能接受,但縱使今日的文學者亦沒有足夠的底氣來反駁他。書中收錄他評魯迅、周作人,及評張愛玲諸篇,於今日而言,也都是一流的評文。
小北
二〇一三年端午於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