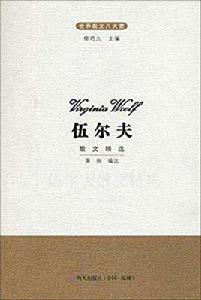叢書特點
該叢書特點歸納起來有三點: 一、在形式上第一次冠名出版。雖然以上八人的散文作品單行本國內出版不少,但以“八大家”之名統一出版則是第一次。 二、名主編、名譯者。主編柳鳴九先生為我國著名學者、翻譯家,在我國學界享有盛譽;各卷的翻譯者(如馬振騁、蒲隆、楊武能等)均為我國著名翻譯家,在業界多有影響。這些著名學者的擔綱編譯是本套叢書水平的有力保障。 三、在內容上的編選上,並不局限於散文傳統意義上的“記敘、說理、抒情”等,有的卷別加入了歷史論著、政論演說、文藝評論等內容,拓寬了散文的範疇。
內容簡介
《世界散文八大家:伍爾夫散文精選》為柳鳴九主編的“世界散文八大家”叢書之一,它囊括了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的英國女作家伍爾夫的隨筆精華。
作者簡介
黃梅,1950年生。1957—l968年在北京上學。1968年底從北京赴山西雁北“插隊”。1973至1989年間先後在山西大學外語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外國文學系和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英語系學習,獲得碩士、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論著有《女人和小說》、《灰姑娘夢的演變》(英文,在美國出版)、《不肯進取》、《推敲自我:小說在十八世紀的英國》、《雙重迷宮》等。編著有《現代主義浪潮下》;譯著有《浪漫派、叛逆者和反動派》(與陸建德合譯)等
圖書目錄
總序:散文的疆界在哪裡
選本序:維吉尼亞·伍爾夫和她的隨筆
笛福
簡·奧斯丁
現代小說
《簡·愛》與《呼嘯山莊》
俄國人的觀點
保護人和番紅花
現代隨筆
切斯特菲爾德勳爵的《教子書》
伯尼博士的晚會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
多蘿西·華茲華斯
傑拉爾丁和簡
《奧羅拉·李》
伯爵的侄女
“我是克里斯蒂娜·羅塞蒂”
托馬斯·哈代的小說
輕率
蛾之死
果園裡
笑的價值
安達盧西亞的小客店
夜行記
論戴·赫·勞倫斯
小說的藝術
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
婦女和小說
沃爾特·羅利爵士
斯特恩
詹森的一位朋友
狹窄的藝術之橋
記一位忠實的朋友
自己的一間屋(節選)
附:維吉尼亞·伍爾夫年表
序言
維吉尼亞·伍爾夫和她的隨筆
◎黃梅
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20世紀最重要的英語作家之一,她在文學寫作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伍爾夫原名維吉尼亞·史蒂芬,出生在倫敦的文學世家。父親萊斯利·史蒂芬爵士(1832~1904)是有名的傳記作家、學者和編輯。史蒂芬的原配妻子是名作家薩克雷之女,他們育有一女。維吉尼亞為續弦夫人所生,而她母親與史蒂芬結縭以前也嫁過人並生養了三個孩子。因此,維吉尼亞有好幾個異父或異母的哥哥姐姐。大家庭中兄弟姊妹關係比較複雜,而且有過傷害身心的經歷,這些在維吉尼亞敏感脆弱的心靈上留下了長久的印記。
維吉尼亞沒有正式上過學。她的父母不但為女兒延請了家庭教師,而且親自主持她的某些科目的學習。此外,由於哈代、羅斯金、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等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化人都與她父親過從甚密,維吉尼亞可說是在文化精英的圈子裡長大的,自幼飽讀詩書。父母去世後,她隨家人遷居倫敦布魯姆斯伯里區。維吉尼亞和姐姐瓦尼莎通過哥哥和弟弟的關係與一批學識卓異的青年才俊(大多畢業於劍橋大學)密切交往,其中包括日後名聲遠播的小說家愛·摩·福斯特(1879~1970)、畫家兼藝術批評家羅傑·弗賴伊(1866一1934)、作家戴維·加涅特(1892~1981)、利頓·斯特雷奇(1880~1932),經濟學家凱恩斯(1883~1946)等——後來人們習慣於把他們稱為“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自1904年年底起,維吉尼亞的文章開始見諸報刊。在她本人的印象中,所得第一筆稿費為l鎊10先令6便士。她用這筆小小的收入買了只波斯貓,並且(如她自己後來所說)變得“有點雄心勃勃”,萌生了寫小說的念頭。1912年她和批評家兼經濟學家倫納德·伍爾夫(1880~1969)結婚。伍爾夫夫婦為了支持嚴肅文學而在1917年創辦了霍加思出版社,出版社的辦公室很快就成為青年作家的聚會地點。T.S.艾略特說:維吉尼亞·伍爾夫“不是一夥初出茅廬的試筆者的核心,而是倫敦文學生活的中心”。
但是這種生活也極大地耗費了伍爾夫的體力和心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她憂慮重重,更深地陷入了精神病態。她並沒有因為不時發病而中止寫作。小說處女作《遠航》於1915年問世,描寫一個英國姑娘赴南美洲的經歷;此後,她又陸續完成了《夜與晝》(1919)和《雅各的房間》(1922)。後者描寫幾名親友來到一位在大戰中陣亡的青年的房間,睹物傷情,從各自的角度追思逝者。該書題材的選取顯然與作者對自己英年早逝的哥哥索比的印象相關。小說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寫實的,卻採用了間接敘述的方法和濃烈的印象主義風格,引起文壇的注意。這部小說和稍先於它出版的短篇集《星期一或星期二》(1921)標誌著作者在主題和技巧上的新嘗試。
20世紀前期是西方文化發生某種轉變的時刻。在20年代,伍爾夫加入了批評傳統寫實手法的論戰。她嘲笑阿·本內特(1867~1931)、赫·喬·威爾斯(1866~1946)、高爾斯華綏(1867~1933)等關注“講故事”的作家“偏重物質”的描寫手法,認為它只觸及表象。同時,她讚揚了“不顧一切地去揭示內心最深處火焰的閃光”的戴·赫·勞倫斯(1885~1930)、多蘿西。理查遜(1873~1957)、喬伊斯(1882一1941)等人。她主張表現人的頭腦在日常生活中每時每刻接受的“千千萬萬的印象”。這與洛克、休謨的英國經驗主義傳統是一脈相承的。當時一些歐陸作家的作品對她也多有啟發。大約在1922年前後她讀了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並參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譯工作,她盛讚這些作家重視表現人的內心,“所寫的一切徹底地純粹地關乎心靈”。
1925年出版的《達洛維太太》充分體現了伍爾夫的藝術追求。這部小說被認為是“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在《達洛維太太》一書中可明顯辨認出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1922)的影響。它包括兩條平行的敘事線索,分別記述屬於上層社會的達洛維太太和因戰爭經歷而精神失常的下層職員、退伍兵塞·史密斯一天的生活。這種“生活”完全是通過人物——特別是達洛維太太——的內心活動來表現的,可以說是由內及外,主要藉助時間(以倫敦大本鐘的報時鐘聲為標誌)的分割來組織空間的轉換。兩個中心人物的生活軌跡並無交叉點。作為議員夫人的達洛維太太從容出入於熱鬧街頭或豪華住所,籌辦晚會、處理家務或沉思休憩。她與蝸居陋室、生活無著的史密斯毫無關聯,只是在小說結尾時,她聽一位前來參加晚會的客人偶然提到小人物史密斯的自殺。這一訊息深深觸動了她心中的某種恐懼和焦慮。雖然從表面看,兩個中心人物像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天地里,但是他們卻又共同經歷著多少相似並多少相關的精神危機,即對英國社會所代表的世界秩序以及對人生價值含有絕望意味的懷疑與追問。兩年後完成的《到燈塔去》(1927)也常被看作是作者最優秀的作品。小說的三個部分猶如三個樂章,描述拉姆齊一家在海濱別墅的,經歷和體驗。無私的拉姆齊夫人是秩序與和諧的化身:她照料孩子、幫助客人、鼓勵丈夫。她許諾要帶小兒子去看燈塔卻未能實現。後來發生了戰爭,帶來了死亡和衰敗。多年後小兒子長大成人,終於和父親一起去參觀了燈塔,他們所感悟到的,是已故拉姆齊夫人某種照耀的心靈之光。對於他們的朋友女畫家莉麗,這一段經歷變成了藝術的靈感。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感人力量,恐怕不在於藝術上的精心營造更勝一籌,而在於字裡行間流露出了對中心人物的某種深刻理解和真摯感情——伍爾夫本人說,拉姆齊夫人是以她的母親為原型的。
繼這兩部成功的“實驗”小說後,伍爾夫一直沒有中斷各類虛構作品的寫作。《奧蘭多》(1928)是一部獨特的戲擬作品,作者讓那位時而男身、時而女身的主人公一活就是幾百年,從伊莉莎白女王統治的時代一直活到20世紀,歷盡近、現代英國社會文化生活的種種變遷。隨後又有《海浪》和《歲月》分別於1931年和1937年與讀者見了面。不幸的是,自母親去世後,自幼體弱的伍爾夫一直斷斷續續地受到神經系統病症的侵擾。小說《幕間》完稿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正在蔓延。伍爾夫在重重內外壓力下感覺自己精神瀕臨崩潰,未能等到《幕間》出版(1941年7月),就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投水自盡了。
伍爾夫的小說富於詩情樂感,在文體和結構安排上都煞費苦心,為小說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她的意識流筆法也被廣泛模仿和移植。儘管如此,仍有許多人更偏愛她的短小散文。本書譯者之一劉炳善教授認為,至少在中國,伍爾夫的散文可能比她的小說擁有更多的讀者和更大的影響。筆者也贊成這種看法。
在20世紀前期諸多從事英語散文(Essay)寫作的人當中,維吉尼亞·伍爾夫是最引人注目者之一。如果說她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寫給小說家的,刻意雕琢的痕跡較重,她的散文書話則如她一個文集的標題所示,大抵是作為“普通讀者”並且為了“普通讀者”而寫就,行文深入淺出,從容幽默、,絕少學究氣,令人耳目一新。她是20世紀英語散文創作的傑出代表,也是第一位取得了與哈茲利特們“平起平坐”地位的女性隨筆寫家。
伍爾夫的散文可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涉及個人生活經歷和體驗的短文。本書收入的《蛾之死》、《夜行記》等即是。讀者未必能分辨出這類文字與她的短篇小說《牆上的斑點》有什麼本質區別。確實,伍爾夫在不斷試探文學體裁的邊界,不願做形式和規則的囚徒。在文字的星空,她有意識地自由放飛心靈,無拘無束地徜徉於虛構與非虛構、詩歌與散文之間。這些短文既含對世界和生命本質的思辨,也描繪了小小的一景一物。文字清新,娓娓道來,仿佛作者靜坐在一旁,等待著讀者的心與自己共同顫動那一刻。
第二類為有關文學、文學理論、作家和作品的感想和評論,也即我們所說的“書話”。這是伍爾夫散文的大端,也是本集遴選的重點。伍爾夫曾為不少文學期刊做特約撰稿人,她的很多文章最初刊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耶魯評論》、《大西洋月刊》等重要報章雜誌,後來才陸續收入文集。其中《普通讀者》(一、二集)在她生前已經問世,還有一些則是在她去世後由她丈夫倫納德蒐集編輯成書的。在這類文章中,《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現代小說》等面世之時就對創作界有相當的影響,而今己成為了解研究20世紀前期小說藝術的必讀名篇。她對作家的評議和介紹往往獨具慧眼,亦莊亦諧,精彩紛呈。值得著重說明的是,這些評說常常對傳統有所突破,在被湮沒的歷史幽暗地帶挖掘思想或藝術的珍寶。比如,在紀念家喻戶曉的名著《魯濱孫漂流記》問世200年的文章里,伍爾夫卻濃墨重彩地討論了作者另外兩部以女性為主人公的小說。她的努力不但拓展了同代人的眼界,修養了他們的心性,也為文學史的改造投入了一己之力。
伍爾夫的第三類散文是有關婦女問題的文字。她被不少後來的女權/女性主義者看作是卓有成就的前驅者。她的聞名遐邇的小冊子《自己的一間屋》出版於1929年,是根據她本人以《婦女和小說》為題在劍橋大學紐納姆及格頓(女子)學院所做的兩個報告而撰成。該書深入討論了歷代婦女在社會、經濟和教育諸方面受到的歧視、排斥和壓抑,回顧並高度評價了女性文學的傳統。伍爾夫還進一步論證說,婦女必須享有隱私權和經濟獨立,才能自由並出色地寫作。她追述了英國女性數百年來涉足寫作的艱難歷程,虛構了士比亞妹妹的遭遇。這本書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知識婦女的心。固然,伍爾夫所關心的主要是中上階級受過教育的女性。她曾就當時出版的一本工人婦女紀事集感嘆說,像她這類人不摸洗衣盆也不切肉,不可能了解勞動婦女的處境。不過,雖說有這樣那樣的局限,《自己的一間屋》及其姊妹篇《三枚金幣》(1938)有關婦女性別角色的言說的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女權運動的經典之作。它們既推動女性自覺意識的覺醒,又主張更上層樓地超越女性意識,所探討的問題至今沒有過時。
當然,上述第二類和第三類文章多有重合——因為任何區隔劃分都不是絕對的。伍爾夫對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女性作家的親切描述和中肯議論常常是她最優秀而有趣的篇什,構成了她的書話的“半壁江山”。
本書擷選了伍爾夫散文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或章節,以議論英語文學作品和作家的書話為主,也兼收若干抒情、記事或論爭的文字。共分為三組:第一組選自《普通讀者》(一、二集);第二組選自其他文集;第三組為《自己的一間屋》一書的第二、三、四章。譯文出自多名譯者。伍爾夫的散文雖然平易近人,但是翻譯起來還是有相當難度的。這主要是因為她對英國歷史文化往事徐徐道來、如數家珍,語間又多含揶揄嘲諷,譯者實在難以一一鉤沉索隱,理解起來難免會有偏差,更遑論在不同的語言文化系統中找到恰如其分的對應表達。此外,她的風格比較口語化,卻又不屬於市井語言,而是大量採用一種知識女性信馬由韁、邊思邊說的長句型。因而,譯者在把握文體時會常常感到進退兩難;不同譯者在具體處理中分寸也必有差異。儘管譯者都勉力求“信”,譯文仍不可避免有錯漏或不妥之處,還懇望讀者批評指正。
圖書試讀
俄國人的觀點
既然我們經常懷疑,和我們有這么多共同之處的法國人或美國人是否能夠理解英國文學,我們應該承認我們更加懷疑,英國人是否能夠理解俄國文學,儘管他們對它滿懷熱情。至於我們所謂的“理解”究竟是什麼意思,可能爭辯不休無法肯定。人人都會想起那些美國作家的例子,特別是那些在他們的創作中對我們的文學和我們本身都具有最高識別能力的作家;他們一輩子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最後通過合法的步驟成了英王喬治陛下的臣民。儘管如此,難道他們了解我們了嗎?難道他們不是直到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刻還是些外國人嗎?有誰能夠相信,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是由一位他所描繪的那個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人寫的,或者,有誰能夠相信,他對於英國作家的批評是出於這樣一個人的手筆,他曾經閱讀過莎士比亞的作品,卻一點也沒有意識到把他的文化和我們的文化分隔開來的大西洋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兩三百年歷史?外國人經常會獲得一種特殊的敏銳性和超然獨立的態度,一種輪廓分明的觀察角度;但是,他們缺乏那種毫不忸怩拘束的感覺,那種從容自如、同胞情誼和具有共同價值觀念的感覺,這些感覺有助於形成親密的關係、正確的判斷,以及迅速交換信息的密切交往。
使我們和俄國文學隔膜的不僅有這一切缺陷,還有一個更加嚴重得多的障礙——語言的差異。在過去的十年里欣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作品的所有讀者之中,能夠閱讀俄文原著的也許不超過一兩個人。我們對於它們品質的估價,是由評論家們作出的,他們從未讀過一個俄文字,或者到過俄國,或者聽過俄國人說俄語;他們不得不盲目地、絕對地依賴翻譯作品。
那么,我們等於是說,我們是丟開了它的風格來對整個俄國文學作出判斷。當你把一個句子裡的每一個字從俄文轉換成英文,從而使它的意義稍有改變,使它的聲音、分量和彼此相關的文字的重心完全改變,那么除了它的意義的拙劣、粗糙的譯文之外,什麼也沒有保留下來。受到了這樣的待遇,那些偉大的俄國作家好比經歷了一場地震或鐵路交通事故,他們不但丟失了他們所有的衣服,而且還失去了一些更加微妙、更加重要的東西——他們的風度,他們的性格特徵。英國人以他們讚賞俄國文學的狂熱性來證明,那劫後餘生遺留下來的東西,是十分強有力、感人至深的;然而,考慮到它們已經是殘缺不全的,我們就不能肯定,我們究竟有多大把握可以相信我們自己沒有非難、曲解這些作品,沒有把一種虛假的重要性強加於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