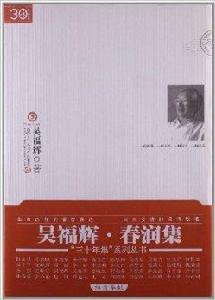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三十年集"系列叢書:春潤集》寫到,編訂完這本“三十年集”,掩卷想來,從內心最深的一個角落裡禁不住發了一聲嘆。這嘆息確有放鬆的意思,便如平日每在書室里鄭重做完一件事情後的感覺。不過隨之這體味就加了分最,沉重起來,並想起在一段時間裡桕熟的老作家蕭乾。蕭老活到九十虛歲,一生有三個“三十年”:最初的三十多年寫出他全部的小說和報告文學作品,中間三十年空白,像我輩一樣要等到1980年代來臨,遂不失時機拿起筆來,寫散文,搞翻譯,竟是寫出他整個文學生涯中三分之二的東西!兩頭高,當中低,他是匹能在沙漠中行舟的雙峰駱駝。我與他相比,“三十年”的空白同樣觸目,卻是只單峰駱駝。我能有蕭乾那么幸運嗎?雖然至今我還在寫,沒有封筆,但已覺高峰逝去,寫篇短文還算順風順水,面對正在參與的一種新型文學史的寫作便常感筆下枯窘,累了。“三十年”會不會即是我的一世呢?
作者簡介
吳福輝(1939—),浙江鎮海縣人(今寧波市江北區)。生於江南上海,長於關外遼寧。1959年始在鞍山任中學教員。1978年人北京大學中文系讀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1981年畢業,即參與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1985年後於萬壽寺老館期間,歷任研究室主任、副館長。2000年完成轉移芍藥居新館工作。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國茅盾研究會副會長。現為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治中國現代文學史,專攻1930年代文學、現代市民文學和京海派文學,偶涉學術散文。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沙汀傳》、《帶著枷鎖的笑》、《且換一種眼光》、《遊走雙城》、《深化中的變異》、《多稜鏡下》等。
序言
編訂完這本“三十年集”,掩卷想來,從內心最深的一個角落裡禁不住發了一聲嘆。這嘆息確有放鬆的意思,便如平日每在書室里鄭重做完一件事情後的感覺。不過隨之這體味就加了分最,沉重起來,並想起在一段時間裡桕熟的老作家蕭乾。蕭老活到九十虛歲,一生有三個“三十年”:最初的三十多年寫出他全部的小說和報告文學作品,中間三十年空白,像我輩一樣要等到1980年代來臨,遂不失時機拿起筆來,寫散文,搞翻譯,竟是寫出他整個文學生涯中三分之二的東西!兩頭高,當中低,他是匹能在沙漠中行舟的雙峰駱駝。我與他相比,“三十年”的空白同樣觸目,卻是只單峰駱駝。我能有蕭乾那么幸運嗎?雖然至今我還在寫,沒有封筆,但已覺高峰逝去,寫篇短文還算順風順水,面對正在參與的一種新型文學史的寫作便常感筆下枯窘,累了。“三十年”會不會即是我的一世呢?
第二種想法:這種編年體的集子是很不留情面的。它好比一幅幅穿開襠褲的童嬰照片,使你無處遁形。它看來看去都屬“少作”,欠成熟,無所謂“悔”與“不悔”,只得一律示眾。雖然也可做些遮掩,比如哪年多選啦,哪年不選啦,但總抹不去大的足印。而且是把你行過的道路、脈絡,毫髮不爽地勾勒了出來。當然,這即是一面鏡子,有一分耕耘,便留下一絲痕跡。自己的文章按年序排將下來,何時是摸索期,由重新打量左翼諷刺到驀然瞥見京派諷刺,直至海派作家進入全視界;何時進入發現期,提出“京海兩難”和“京海衝突”的文化結構,深入探究海派,在中國城鄉大環境下俯視都市文學,至市民文學;何時由個別到綜合,有了三種現代文學形態或更多形態的多元共生文學史的觀念,並從合力寫作文學史到獨力完成文學史,實現夙願,等等,均清晰可見。個人的命運機遇、點滴積累的用力、研究個性的張揚,風雲際會,與新時代的學術結合了,明白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什麼是能夠渴望的,什麼是達不到的,這些統構成了一部對自己不可須臾離開的學術生命史。由此我想,編年體的集子,縱使再顯出我的淺近、淺顯、淺陋,令人汗顏,只要能像魯迅評價劉半農時說的,做到“淺清”二字,不是一攤泥潭,也就可以安心走剩下的路了。
重讀這些選文也不免感慨,並對我在許多文章里侈談自己一代學人的過渡性質,有了新的領悟。若說吾輩“承上啟下”不假,但依我看更多的是具承上性吧。試看這些選下的文字,從觀點形成、史料運用、理論方法到文體風格,哪一項不是與今日學子迥異的?這裡並無對或不對的是非價值判斷。聽說也有個別年輕人表示喜歡我的行文格調,一冊《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一宿就讀完了,不知道那是何種類型的青年。時光不能倒流,在這個電腦手機通用、網上遊戲網上用語迅速讓爺爺奶奶成為“傻子”的時代,即是像五四那個使三四十歲保守者變為“遺少”的社會大拐彎時段,人們的表現仍可各各不同。有赫赫有名的螳臂當車者,也有甘做土石奠基或看路拉車者,我能心儀後一種人也就不錯了。
這裡所列的文章,是按照代表性(將個人和學術紀年都計在內)、初刊狀態(不予修改)、混合編組(長短論文兼搭配散文隨筆)幾項原則遴選的。我平時就偶寫隨筆,大體有人物回憶、學科漫談和因史料引發的雜文這樣三類,最近更在某學術刊物上開了一個“石齋語痕”的欄目,出版社提出的體例是混編以使讀者養眼,這正投我之所好。但較長的論文與散文我覺得不能不忍痛割棄。其中的兩篇:一是我的學位論文《中國現代諷刺小說的初步成熟——試論“左聯”青年作家和京派作家的諷刺藝術》,它的刪節本發表在1982年的《北京大學學報》上,也足有兩萬字,全文收入了我的第一個集子《帶著枷鎖的笑》;另一篇是《融入我的大學——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斷》(都是長名字,全文也不短),發表在《中華讀書報》,幾乎占了一版,收入我2010年出版的集子《多稜鏡下》。這么說似有點扔在筐外都是好貨的味道,讀者自可去辨認。附錄里應有篇回顧文字,因我這幾年被邀寫被採訪的此類文字已有多篇,加上往日所寫序跋也多涉此,不能再嘮叨了,便選了《我也穿過鬆緊不同的鞋子》以充數。
我要感謝復旦大學出版社各位的盛情,邀我來編此書。我與復旦有多方面的友情,不是一句話說得盡的。大學教育對人的一生究竟有多么重要,我這個自學出身的人應該有點發言權。本書的書名就來自我讀研究生的母校,因了我最尊敬的並得到過耳提面命的兩位先生:王瑤先生當年住在北大鏡春園,吳組緗先生的寓所地處朗潤園,我便將“鏡春”、“朗潤”各取一字,成“春風化雨,潤物無聲”之意,以示我的紀念。這在我本是一件私案(非“公案”也),大約編《且換一種眼光》的時候我就想用此集名,在序言中曾做過說明。那時的出版發行部門都深恐書名太雅,我便做了妥協。現在是挾了我們這套學術著作不但不忌書卷氣,還唯恐不足的雄風復辟了。天緣在此。
2012年2月4日於京城小石居,是日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