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皮埃爾·洛蒂
皮埃爾·洛蒂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路易-瑪麗-朱利安‧維奧(Louis-Marie-Julien Viaud,1850—1923)的筆名,出生於法國西部夏朗德河口羅什福爾市一個職員的家庭,他從小迷戀大海,早就夢想作為水手週遊世界,後來他果然成為一名海軍軍官,從事海上職業達四十二年之久。他走遍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海地帶,到過美洲、大洋洲、土耳其、塞內加爾、埃及、波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支那、日本、中國……豐富的閱歷源源不斷地給他提供寫作素材,他甚至不需要多少想像力,僅用白描手法記下沿途見聞,便足以構成使讀者著迷的奇幻畫面。一八七九年,洛蒂發表了記述土耳其風光及其戀情的處女作《阿姬亞黛》,翌年又在報刊連載了《洛蒂的婚姻》,這兩部小說奠定了他的作家聲譽,默默無聞的海軍軍官一躍而成為文壇名人。他幾乎以每年一書的速度相繼出版了十二部小說、九部紀實隨筆(其中包括記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北京的末日》)以及若干自傳性的作品。
這十二部小說包括:《阿姬亞黛》(1879)、《洛蒂的婚姻》(1880)、《一個非洲騎兵的故事》(1881)、《厭倦之花》(1882)、《我的兄弟伊弗》(1883)、《北非三貴婦》(1884)、《冰島漁夫》(1886)、《菊子夫人》(1887)、《水手》(1892)、《拉慕珂》(1897)、《梅子太太的第三度青春》(1905)、《醒悟》(1906)。九部隨筆包括:《秋天的日本》(1889)、《在摩洛哥》(1890)、《東方的怪影》(1892)、《浪跡天涯》(1893)、《耶路撒冷的荒漠》(1895)、《北京的末日》(1902)、《英國人治下的印度》(1903)、《走向伊斯巴罕》(1904)、《吳哥的進香者》(1912)。
在這些小說中。他客觀地描述愛情故事,每次艦隊拋錨靠岸時,他都試圖以愛情滿足自己的夢想和消除自己憂鬱心情,有時候還把自己寫進書中,如一個小孩的故事和少年,愛與死在他的書中占有重要地位,透露出他對感情生活消逝的深切失望。
評價
 皮埃爾·洛蒂
皮埃爾·洛蒂(作者:艾珉)由於職業提供的便利,洛蒂能夠見識到和描述出同時代其他作家所不可能描繪的絢麗多彩的景色,反映出不同民族千差萬別的文化觀念,給予讀者一種新鮮和強烈的印象;但也由於職業的局限,他不大有條件深入法國或其他任何國家的社會生活,很少有機會切實地觀察、研究各個階層的人物及其相互關係。從這個角度講,他的視野又相當狹窄,因而我們不能指望他的作品反映出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和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微妙的矛盾衝突。但他對異域風光和異域民族文化的記述是如此生動、逼真,足以大大吸引對海外世界充滿好奇心的法國公眾,且恰好適應了法國當局推行海外擴張政策的需要,因而他幾乎是輕而易舉地贏得了官方和民眾的一致讚賞,並於一八九一年當選為法蘭西學院四十位不朽者中的一員。
不過洛蒂在藝術上確有其獨到之處,主要是景物描寫方面,他具有一種真正的藝術家的才能,特別是他對海的描繪,可以說至今沒有第二個法國作家可與之匹敵。正如二十世紀的聖埃克絮佩里由於本身是飛行員,因而對太空的觀察與感受達到了其他作家所不可能達到的境界一樣,皮埃爾·洛蒂以他四十餘年的海上生涯,獲得了描繪大海的絕對的、無可爭辯的優勢。正是由於這方面的突出成就,使他有別於那些曇花一現的時髦作家,而在文學史上占據了一席不容忽視的地位。
法國著名文學史家朗松把皮埃爾·洛蒂歸結為夏多布里昂式的浪漫派作家,稱讚他是“文學領域的偉大畫師之一”,認為他“描繪動的景物和自然界奇異現象的精細和準確”,完全可以“與夏多布里昂媲美”。
實際上,洛蒂的風格比夏多布里昂質樸得多。夏多布里昂即使寫景也常有誇張和虛構,以致他書中描寫的自然,和真正的自然相去甚遠;洛蒂卻忠實地記錄他所目睹的一切,而且從不堆砌詞藻,很少用華麗而誇張的形容詞。他的文字平易,幾乎全是普通的用語,他的辭彙簡單到近乎貧乏,但令人驚異的是,他竟能用一些極普通的辭彙,描繪出大自然的千變萬化,而且給人以強烈的印象。他的描述是那樣精確、細緻,給人以那么親切的實感,所以有的批評家認為,洛蒂的藝術主耍來自直接的觀察和逼真的描摹,本質上仍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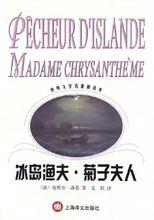 冰島漁夫·菊子夫人
冰島漁夫·菊子夫人然而洛蒂的景物描寫較之一般意義的現實主義細節描寫帶有更多的印象派色彩,他更強調旅行者對外界景物的主觀感受,並賦予自然界以人的靈魂,而且總能在不同的瞬間攫住新的意境,從這個角度看來,洛蒂的藝術又是非常浪漫的。和更多布里昂一樣,他的作品的基調常常是難以排遣的痛苦和憂鬱。他所從事的職業對他這種氣質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由於與那變化莫測的大海朝夕相伴,由於經常置身於戰爭的氛圍之中,他的思想經常被生死無常的念頭所纏繞:人的生命是那樣脆弱,命運又是那樣的無情,每一個人在今天都難以預料明天等待他的將是什麼。他到過無數的國家,見識過各種類型的生活方式,接觸到不同膚色、不同面貌、不同信仰的人種,在這一切變化多端的形態之下,他感到一切都是相對的、短暫的,只有死亡才是絕對的,一切都將被永恆的死亡所吞沒。幾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重複著這同樣的感受:時間的流逝、人世的短暫和感情的無常。是否正因為如此,他才經常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及時行樂?是否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勤於筆耕,以儘可能留住這不斷流逝的人生,儘可能地保存一部分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