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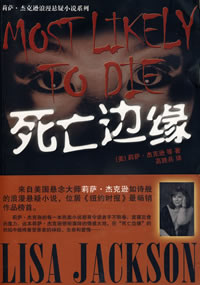 死亡邊緣
死亡邊緣來自美國懸念大師莉薩·傑克遜如詩般的浪漫懸疑小說,位居《紐約時報》最暢銷作品榜首。莉薩·傑克遜的每一本熱賣小說都有令讀者手不釋卷、廢寢忘食的魔力。這本莉薩·傑克遜領銜演繹的情感大戲,在“死亡邊緣”的烈焰中燒烤著受害者的神經、生命和愛情……
內容簡介
《死亡邊緣》為美國懸疑小說大師莉薩·傑克遜等人的浪漫懸疑小說之一。二十年前,受到眾多女同學愛戀的傑克·馬爾科特在情人節舞會上被弩箭射死,掛在一棵老橡樹上。傑克的女友克尼斯頓、琳賽、拉切爾等互相猜疑誰是真正的兇手?十年後即將舉行同學聚會,兇手對她們的言行了如指掌,而她們卻對兇手毫無覺察。克尼斯頓等人身處“死亡邊緣”,誰將不幸成為犧牲品?誰又能僥倖逃脫,並且擺脫傑克的陰影,重新找回屬於自己的愛情?
作者簡介
莉薩·傑克遜,出生於美國俄勒岡州的一個小鎮,美國著名暢銷書作家,憑藉希爾胡特圖書公司1983年出版的小說《命運之結》(A TWIST OF FATE)一舉成名。她創作出版了六十多部小說,作品銷量在《紐約時報》、《今日美國》、《出版者周報》及亞馬遜網站等主流媒體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這些作品一版再版,並被翻譯介紹到多個國家。其中,莉薩創作的浪漫懸疑小說系列:《極度戰慄》、《絕對恐懼》、《死亡邊緣》、《終極尖叫》、《致命烈焰》等更是穩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推崇,形成穩定的莉薩·傑克遜冬粉團;加之作者強烈的個人風格,使得她的暢銷小說作家地位更加穩固。莉薩·傑克遜是美國懸疑小說協會、國際驚悚浪漫作家協會中一顆耀眼的明星。
媒體評論
莉薩·傑克遜、貝弗莉·巴頓、溫蒂·柯希·史妲博,時下被《紐約時報》評為最暢銷的三位作家,本書是她們三強聯手的最新力作 ——豪斯·維萬特
我讀過L.傑克遜,讀過B.巴頓,讀過W.K.史妲博,但是《死亡邊緣》讓我一次享受到這三位大廚精心烹製的驚險浪漫的盛宴,二十年前的愛情和二十年後的聚會,未曾偵破的兇殺案和接踵而來的新死亡,當年的痛不欲生和此刻的死亡追殺,在保衛生命的同時重新鑄造幸福的愛情這一切驚險極了,美妙極了…… ——梅克阿普·瑙特(田納西)
《死亡邊緣》有一切暢銷書的潛質:驚險,懸疑,浪漫;但它更有打動人心的永恆主題:只有愛才能征服罪惡,只有美好才能收穫美好,只有對生命的熱愛才能驅除對死亡的恐懼。 ——辛·萊科桑(文學評論家)
書摘
第一章
俄勒岡州,波特蘭市
2006年3月
“這么說,我就難辦了,你說的是這樣嗎?”克尼斯頓坐在辦公椅子上向後靠著,手機穩定在耳朵和肩膀之間,她的頭痛又要上來了。雖然時間一定是浪費了不少,但她抱有希望:她的朋友奧婁拉找到了其他某個人安排那該死的二十年一次的聚會。“沒有人願意接管這件事嗎?”
“你是致畢業告別辭的學生代表,成績最好。如果你不想帶頭搞聚會,當年你應該至少有一門不拿優,不是嗎?諸如體育課程、微積分課程或其他什麼課程。”奧婁拉·澤菲爾開著玩笑並隨之笑了起來。頓時,克尼斯頓能想像出她露齒的微笑和心照不宣的淺褐色的眼睛。奧婁拉是她多年來一直保持聯繫的一位聖伊莉莎白中學的同學。
“如果我知道會有這樣的事,我會那樣做的。”
“不可能了。不要消極吧,搞聚會也會有趣的。”
“對,不錯。”
“什麼使你不愉快嗎?你曾經是知道怎樣使自己快樂起來的,還記得嗎?”
“快樂起來……”克尼斯頓質疑地嘟噥著。
“你要為你很久以前就認識的夥伴們籌辦一次大型聚會了。著手開始吧,不願意嗎?”
克尼斯頓嘆了口氣,一下靠在了辦公桌上,說:“我只是盡力迴避和聖伊莉莎白學校有關的事。”
“我知道,因為傑克。我們都有同感。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事情已經二十年了,它已被時間淹沒了。掩埋過去,振作起來吧。”
“我盡力。”
“哈利路亞、阿門,我的姐妹。”奧婁拉祈禱著,克尼斯頓於是笑了。
“我已經召集了不少志願者。”奧婁拉補充道,“還記得海勒·斯旺森嗎?”
不就是那個堅持傑克謀殺了伊思·帕爾斯的神經病嗎?她不可能忘記的。“她也參加了?”
“是的,還有曼迪·金,她的姓現已改為斯圖斯了。”
曼迪·金是克尼斯頓中學時沒有好感的另一個女生。
“還有其他一些人到時也會參加的,我已讓他們相互轉告,把訊息發出去。人越多越好。我甚至也打電話給琳賽·法雷爾和拉切爾·艾爾賽思,但是她倆住得太遠了,來不了。”
“我知道。”克尼斯頓每年仍收到一些應該是她最好的女性朋友的聖誕賀卡,這些賀卡傳遞著有關朋友們新變化的信息。
“琳賽已是紐約一位相當成功的專案策劃人,拉切爾是……哎呀,等一等……我知道……”
“她已嫁給了阿拉巴馬州的一個警察。”
“是這樣的。”奧婁拉慢慢地說道,“像她的老父親,也在波特蘭警局待好多年了。”
克尼斯頓感覺脖子後面肌肉在拉緊。邁克·艾爾賽思曾是處理傑克·馬爾科特謀殺案的偵探之一。儘管他和他的警局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丘比特的兇手”案最終還是不了了之。克尼斯頓還聽說,偵探艾爾賽思因為無力偵破他女兒好友的謀殺案而被迫提前退了休。
傑克·馬爾科特的陰魂籠罩在每個人的心頭上。
自從畢業以後,克尼斯頓既沒見過琳賽也沒見過拉切爾。她還記得畢業
那天她們都戴著帽子、穿著長袍,面帶笑容,不知為什麼都眼淚汪汪。六月的那天顯得格外熱,在等著做畢業告別演講時她滿身出汗。隨後修女涅瓦院長給她頒發了畢業證。畢業典禮後,她找到了琳賽和拉切爾,她們抱在一起、照了相併信誓旦旦地說日後保持聯繫,但是她們並沒有做到。上大學前的那個夏季都沒聯繫,後來也並無聯繫。
因為傑克。
許多事都改變了,就是因為傑克。
克尼斯頓在椅子上把頭往前傾著,看著電腦顯示器上的屏保養魚缸的動漫。畫面上,天使魚正被飛奔的氖光鐵拿魚在長短不一的海草中追逐著。
“奧婁拉,你應該主辦這次聚會而不是我。”
“沒商量餘地,你不要推脫了!我想我能幫你草草開個頭,整個聚會就像你的嬰兒,全靠你啦。”
“行,”克尼斯頓妥協了,“為什麼不能推脫?信不信由你,我已做了一些事。如果確實選在聖伊莉莎白學校舉行,我已聯繫了兩個舉辦地。”
“太好了,我們是最後一屆女子班畢業生,現在學校又要關閉了。在其他地方舉辦是沒有理由的。我問過了我開始接觸的幾位同學,她們基本上都主張在聖伊莉莎白學校舉行。”
“就按你說的辦吧。”
“好。我等會給你發封有附屬檔案的電子郵件,告訴你目前我所做的事。以後的事就拜託你了。兩小時後再見。”
“你得逞了。”
克尼斯頓掛了電話,吃了兩片阿司匹林以防即將到來的頭痛,然後埋頭幹活了。她在潤色一個富有人情味的故事,故事講的是一個男人和他的狗花了一年的時間從密蘇里途經俄勒岡鐵路走到俄勒岡。在潤色稿件的同時,她成功地在腦子裡把關於聖伊莉莎白學校的事整理出來。她把故事稿件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傳給了她的編輯,然後在工作間裡抬頭看了一眼。辦公桌上方的牆壁上掛著個埃爾維斯時鐘,埃爾維斯的兩腿在搖擺著,當時鐘計時時,埃爾維斯國王的手在老式刻度盤上移動。現在,埃爾維斯指出:已將近六點鐘了。克尼斯頓像往常一樣又要晚點下班了。她檢查了一下郵件,發現了奧婁拉的郵件,她便列印出來了,那是一份表格文檔,記錄了同學們的信息比她原先想像的要多。
挎上手提包,克尼斯頓站了起來,伸伸懶腰。她的這個工作間是在一間比較大的新聞辦公室改裝時分到的。她在波特蘭的克萊利恩公司工作已十五年了,這樣長的工齡實際上能夠確保有一間辦公室了——但似乎“上司”對她關注不夠,所以這樣的待遇就不能確保了。
“我下班啦。”克尼斯頓關上筆記本電腦,同剛才的表格文檔一起放進電腦包。
“今晚有重要約會嗎?”薩布麗娜·拉菲問道,她相隔克尼斯頓兩個工作間。此時,她把喝空了的雙倍加濃咖啡杯翻轉過來,用長長的手指捏扁後扔進了垃圾桶。
“對。”克尼斯頓一邊說著一邊在手提包里找鑰匙,找到了那一大串鑰匙後便朝門口走去。當她在穿過克萊利恩新聞室迷宮似的辦公桌、會議桌及椅子時,薩布麗娜跟了上來。這是克尼斯頓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她只是把這份工作當做向更大、前途更光明的大傳媒公司邁進的奠基石。雖然多年來她在公司的情況改變了——慢慢地放開了手腳,漸漸地一切在進步並有了質的變化——但這不能說明她肯定老老實實地在這兒待下去。
“你該出去找個男人,找些快樂。”薩布麗娜建議著。她有兩隻褐色大眼睛,梳著玉米壟式的髮型,戴著金屬首飾。
“我已結婚了,你忘了?”
“你們已分居一年了,上次我聽說你打算和羅斯那渾蛋離婚。”說話時薩布麗娜美麗的眉毛彎成了弓形。
“是的,是的。說著容易做起來難。”
“喔……我已離過三次婚了。”
“可能萬事開頭難。”
“不試試永遠也不知道。”薩布麗娜在通向休息室的過道前停住了。
“我已有孩子了。”克尼斯頓提醒著。
“基本上是誰在養?”
克尼斯頓哼了哼說:“沒人問,她已十六歲了。”
“你就這樣告訴她的?”
“天天都是這樣說的。不過,今晚我碰巧真有一個約會,只不過是和二十年都沒見面的一二十個女性老同學的約會。我被推選為籌辦那該死的中學聚會的負責人。”
“不要乾。”
“被推選的,”克尼斯頓強調道,“我不是自願的。”
薩布麗娜皺了皺長鼻子:“難道你就不能溜之大吉嗎?”
“我希望今晚能把責任委託給一個更能勝任的人。”
“祝你好運。”薩布麗娜大笑著,慢慢走過大廳。
克尼斯頓推開報社大樓的玻璃大門,迎面撲來了夾雜著河水和廢氣味的寒氣。烏雲已籠罩在波特蘭市高大建築的尖頂上,當她匆忙走過兩個街區來到停放她那破舊不堪的本田汽車的停車場時,開始下雨了。輕彈著夾克衫的帽子,她快步來到車前。車子看上去和她一樣疲憊,不過,快樂正要開始啦。
克尼斯頓無奈地搖搖頭。對她來說,中學時代在情人節舞會的那晚便結束了。剩下的中學時光稀里糊塗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在記憶中仍是不清楚。但是很明顯,她作為全班畢業告別辭演講者,收穫之一便是她現在不得不組織班級聚會。
她近二十年來都成功地逃避了這種責任,但是這次不行了。奧婁拉一定要舉辦她們八六屆班級二十周年聚會。
唯一一個好訊息便是有望下次聚會她能把這責任推給別人,如果有一個……
她慢慢地開著車,一邊從包里摸出手機。一隻手開著車,另一隻手快速撥了家裡電話,同時她打開了擋風玻璃的刮水器。在電話第二次振鈴時,接通了錄音電話。當錄音電話提示音響時她說話了:“麗莎,如果在家,回電話.可以嗎?”停了一會兒,沒回音。“麗莎,你在家嗎?”仍沒有一絲回應,沒聽見她女兒的聲音。很明顯她女兒不在家。“聽著,如果知道我給你打了電話,請回話,我二十分鐘後到家。”她掛上了電話,繼續撥通了女兒的手機,隨後聽見:“你好,我是麗莎,你知道該怎么做了。留下你的號碼,如果你幸運,我會克尼斯頓掛了電話,毫無疑問她女兒看見了她的電話號碼。來電顯示就是這樣令人痛苦。“煩人!”她嘀咕著,同時發現她的車已出了停車場,進入了緩慢的車流,慢慢地走出市區。她很生氣她女兒不待在家。那傢伙難道不知道“我已罰她在家”嗎?但願我等會離家前能見到她。她在哪兒?外出不到一個小時嗎?“上帝啊,救救我吧!”她低聲說著,腦子裡想著今晚還有一個聚會籌備會的第一次碰面會。
車速甚至總是低於每小時二十英里,克尼斯頓徐徐向西上了凱尼奧恩大道,這條大道穿過西山林區那陡峭的山崖間。她還要經過通常被稱作自殺之橋的威斯坦大道的高架橋下,每次經過那八十年之久的石制弓形橋下時,她卻想到那些人就是跳到她正開過的道路上而死的,於是她不寒而慄,看著大滴的雨水落在擋風玻璃上細細散落著。很快她到了去她家的岔路口,她猛踩了一下加速器,小車沿著一條不可思議的彎彎曲曲的環山路向山上開去。這條路經過道拉斯杉樹林的停車場蜿蜒到山頂,它的終端是條小小的私家通道直通克尼斯頓的家。她的家是長滿雪松和綠草的“當代西北家園”,它建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據說可鳥瞰遠在山腳下的城市全景。
今夜她寧願穿上舒服的線衣,生上火,蜷縮在窗戶下看一本自己喜歡的書。最不想做的事是再次離家和一些老同學打交道。杳無音信的二十年過去了,她已沒有了與那些抑或是朋友、抑或是敵人、抑或是不熟悉的人交往的激情。世上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事了。
到家門口時,她突然意識到她犯了多大的錯誤:聚會籌備會不是她“不願做的事”的清單上的第一位。排在第一位的、可怕的事是與她將要離婚的丈夫相處。今夜看來又有一場酣戰了,因為她看見了羅斯那龐然大物般的黑色卡車就停在前面的通道上。
“給我力量。”她在街對面停車時暗暗祈禱。
那天很快變得越來越糟糕了。
“太好了。”她嘀咕著。她暗自祈禱要有足夠的耐力與丈夫較量。他們是大二時結婚的,對她來說,那是個魯莽、倉促的決定,她已後悔不已。要不是他們的唯一女兒,也就是現在“電話也聯繫不上”的小麗莎,那他們的婚姻則是個徹頭徹尾的巨大錯誤。
她已沒有毅力、心情、時間或精力去結束這一切了。
他似乎也是這樣。
離婚手續也沒辦。
到現在仍然沒有辦。
“好戲在後頭呢。”當她從信箱里拿出郵件時自言自語。腳下橙色的斑貓差點把她絆倒。她穿過車房開著的門,經過路旁放著的割草機、梯子以及垃圾桶,來到了通向廚房的門,看見了廚房裡待著個大活人,是她的丈夫羅斯坐在拐角的咖啡桌旁,一邊品著他的淡啤酒一邊在看報紙。
他們在一起的日子裡,他一直是這個德行。
他在瀏覽經濟版塊。他穿著白色的襯衫,上面兩粒扣子開著,兩隻袖子給卷了起來,領帶隨意地扔在椅背上,錢包和鑰匙放在桌子上。
“待了一會兒了吧?”當羅斯抬起頭像往常一樣用灰色的眼睛審視她的時候,她問道。
有趣的是她原有對抗的想法有些失靈了。雖然他們一起生活許多年,戰鬥過多少次,並不是同一路的人,但她仍然覺得他很性感、有魅力。她欲罷不能。
“我想帶麗莎吃飯,但她不在家。”
“僅此而已?”
“對。”
她驚嘆道:“你沒想到打電話給她?”
“想到了,”他吞下了一口酒,靠在椅子上看著她說,“但後來改變了主意。”
“為什麼?”
他聳聳肩說道:“我想你說的有一定的道理。要么,如果你願意的話,我現在打個電話給她,這很容易。”
“你就這樣自己進屋了?”
“房子我有一半,我也有自己的鑰匙。”他那可惡的眼神直刺著她,向她挑戰,但她沒迎上去,她沒有時間和精力吵架了。
“她去哪兒了?”
“我原以為你知道。”他舒展了一下身體,肩膀和手臂處的縫線被拉得緊緊的。他腦後的頭髮有點長了,在領口處皺摺著。
頓時,克尼斯頓心煩氣躁:“麗莎應該放學後直接回家。”
“你和她講過?”
“對,是這樣的。”今早不悅的場景她還記憶猶新。她和女兒麗莎吵架了,主要是麗莎生她的氣,因為克尼斯頓看了她的學習進度報告。在麗莎看來,即使進度報告的信封上是寫給羅斯·戴爾摩尼科先生和夫人,但是有關不及格的情況只是她自己的事不關任何人的事。她發了一通火併拒絕吃早飯。她灰色的眼睛極像她爸爸,發出了怒火,氣沖沖地小跑出了門,與男友一道坐上了車。“我懲罰她是因為她的學習進度報告。”克尼斯頓解釋道。
羅斯抬起了眉毛等待著克尼斯頓繼續講下去。
“她化學、德語不及格。”克尼斯頓從餐桌上拿起學習進度報告遞給了他。
“不及格?”他說著,眼睛看著老師的評語。
“她聲稱這是個重大的錯誤,老師沒有把那兩門成績輸進去。所以我叫她核實一下,讓漢森夫人和契爾多斯先生打電話給我、或寫便條給我、或發電子郵件給我。但直到現在,我沒收到任何老師的信息。我想成績不上去,她什麼地方也去不了。”
“這樣的生活不有點像狄更斯筆下悲慘的生活嗎?”
“你有更好的辦法?”她並不需要丈夫關於養育孩子的任何建議,他多年來都是婚姻生活中的幽靈,整天總是工作。當羅斯沒回答時,她繼續說:“我不這樣認為。”
“她還和澤克一起上學嗎?”克尼斯頓點著頭自言自語著。此時羅斯令人生氣地說道:“我聽著你似乎不是在罰她待在家裡。”
“我要晚點了,因為我……”克尼斯頓立刻停了下來,牙關緊咬著,她瞪著羅斯說道:“我憑什麼要和你解釋?我不像你,我總在她身邊惹她生氣。”
“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我。”他針鋒相對地說。這話確實沒錯,是她要他搬出去的,而他就照辦了。現在他在椅子上挪動了一下,面對著克尼斯頓,從而克尼斯頓看見了他方形的下巴,覺得他還和她約二十年前遇見他時一樣剛健有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