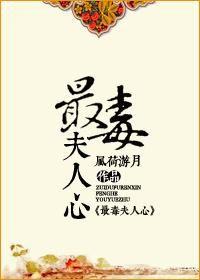圖書內容
廣靈郡主性格驕縱,暴力乖張,是闔府上下都頭疼的小麻煩精。 誰都奈何不了她,唯獨當今魏王江衡。 論輩分她得喊江衡一聲舅舅。 雖不情願,但這根大腿還是要抱的,誰叫他日後有大作為呢?但是,等等……江衡,不是這樣抱的!
初章試讀
第1章 心疾
才過端午,天氣益發悶熱起來。
樹上蟬鳴啾啾,燥熱的氣息透過綃紗傳入室內,就連丫鬟舉著團扇打出的風都是熱的。
陶嫤臨窗而坐,手持一支紫毫宣筆,認真地描繪院外盛開的火紅石榴花。大抵是天兒太熱了,她的眉頭越蹙越緊,細嫩的額頭滲出絲絲汗珠,末了煩躁地將紙張揉成一團,向窗外擲去。
“不畫了不畫了,一點意思也沒有。”
左右兩旁丫鬟見狀,打風的力道更加快了一些。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這位小祖宗不痛快。
大丫鬟玉茗掏出絹帕,輕輕地拭去她鬢角水珠,“郡主可是累了,不如休息會兒吧?”
陶嫤搖了搖頭,目光固執地落在那棵石榴樹上。
她櫻唇微抿,似是要把它看出個究竟。碧清妙目瀅瀅渟渟,好一會兒才別開,“今天什麼日子?”
玉茗靜了靜,“六月初三。”
初三,距離她阿娘殷氏的忌日還有兩天。
殷氏於明徽十五年逝世,至今已有七年。她是陶嫤的生母,嫁給宰相陶臨沅後育有一子一女,正要生第三胎時,卻因體弱氣虛,最終沒能平安順產,一屍兩命。
陶嫤托腮,若有所思地望向庭院,眼裡露出幾抹落寞。
其實阿娘不是難產,彼時大夫都看得好好的,何況她和大哥生產時都很順利,怎會說難產就難產呢?究其原因,不過有人從中作梗罷了。
當時她小,不知道好好保護阿娘,眼睜睜地看著她香消玉殞,卻無能為力。
長安的天氣一天賽一天地熱,跟被巨大的炭盆烤著似的,即便她只穿一件輕薄的散花綾,也招架不住這股悶熱之感。
陶嫤膚色雪白,有如雪峰上最晶瑩剔透的顏色,偏偏這種白還曬不黑,不知羨煞多少豪門貴女。她不是頂漂亮的女郎,卻因為生了一張乖巧稚嫩的臉龐,給人一種天真的錯覺。唯有最親近的人才知道,這姑娘其實一肚子壞水兒,並不如表面那般無辜。
要她有心,能把你整得苦不堪言。
翡翠珠簾被挑起,白蕊端著一碗冰鎮糖蒸酥酪過來,掀開月白釉碗蓋,“郡主吃幾口酪解解暑吧。”
這是陶嫤最喜歡的食物,她舀了一口,清涼乳酪入口即化,冰冰爽爽確實消除不少熱氣。
吃著吃著,她忽然擱下,“外面怎么如此吵鬧?”
白蕊微滯,惴惴地覷一眼她的表情,“稟郡主,是相爺帶回來的兩位侍妾,正在往府里搬東西呢。”
陶嫤不悅地抿了下唇:“哪來的侍妾?”
白蕊的聲音低不可聞:“聽說是向陽侯送的,目下住在金露軒中。”
金露軒里住著十來名侍妾,陶嫤對這地方並不陌生,這些年陶臨沅不斷地往裡頭添人。他除了朝堂辦公外,最常做的便是倚翠偎紅,醉生夢死,對兒女的事不聞不問。這幾天尤其過分,徹夜不歸,也不知宿在哪家娘子房中。
陶嫤坐起,換了身湖色織彩百花飛蝶紋高腰襦裙,重新梳了個倭墜髻,金翠孔雀簪襯著她皎如明月的面龐,明亮生輝。她看了看外頭太陽,已經漸漸西斜,不如午時那會兒悶熱了,遂叫上玉茗白蕊二人,“去金露軒瞧瞧。”
……就知道會是這么回事,玉茗白蕊相視一嘆,簇擁跟上。
這會兒相爺恐怕還在那裡,郡主選擇這時候過去,無疑是準備給他添堵。
金露軒位於相府西南一角,是個兩進的庭院。院內亭台樓閣,假山流水,景致勉強稱得上雅致。然而走得近了,那股脂粉味兒越來越濃,陶嫤嫌惡地皺了皺鼻子,問院內當值的丫鬟,“左相呢?”
自從殷氏走後,她從未喊過陶臨沅一聲阿爹。
這兩年陶嫤來過此處幾次,每次都鬧得驚天動地,是以院裡的丫鬟看到她很是畏懼,縮手縮腳地回答:“在、在鶯眉閣二樓吳氏房中。”
陶嫤沒有多言,轉身往二樓走去。
院裡原本歡鬧說笑的侍婢,這會兒都緘默不言了。她們好不容易等太陽下山,氣溫稍微涼快一點兒,想要下樓透透氣,誰想會遇到這位小祖宗。惹不起還躲不起么?還是趕快回房去吧。
吳氏是陶臨沅今天帶回來的兩位侍妾之一,房間在二樓東面第三間。
陶嫤推開鏤空菱花門,一陣濃郁的酒味撲面而來。窗戶朝西,借著落日餘暉能看清房間光景。
酒杯滾落一地,朱漆螺鈿小几擺著幾壇佳釀,一襲黛紫錦袍的男子依偎在女人懷中,醉意酣然。那位女子頭戴珠翠,態度殷勤,正不斷地往他的杯子裡續酒。
陶嫤蹙了蹙眉,上前奪過陶臨沅的酒杯,“你要喝到什麼時候?”
吳氏被她突如其來的到訪嚇一跳,因著頭一天來相爺府,沒見過廣靈郡主尊容,還當她也是金露閣的侍妾,當即一聲不滿:“相爺正在興頭上,你是何人,為何要來打攪?”
陶嫤朝她看去,“你也配同我說話?”
那眼裡,分明含著輕蔑與諷刺,不加掩飾。
吳氏一驚,被侮辱的怒意襲上心頭,“你……”
行將反駁,埋在她胸口的男人抬起頭,睜開醉醺醺的雙目,看清來人後略有詫異,“叫叫,你怎么來了?”
叫叫是陶嫤的乳名,小時候她咋咋呼呼,吵鬧得很,是以殷氏便給她起了這么個乳名。
如今聽來,很是諷刺。
“我為何不能來?”陶嫤後退半步,許是被他身上的酒味熏著了,“我如果不來,怎么看到你這副模樣?怎么讓我阿娘知道,她死的一點也不值得?”
陶臨沅瞳孔緊縮,心臟似被狠狠揪了一下,他闔上雙目,年邁英俊的臉上滿是痛苦。他忽地舉起桌几上的一壇酒,不要命往嘴裡灌,溢出的酒灑在他的脖子上、衣服上,他卻渾不在意。
如果醉了能好受些,他情願一輩子都糜爛至此。
陶嫤看不過去,奪去他手裡的酒罈狠狠擲在地上,酒液四濺,弄濕了兩人的鞋襪,“別喝了!”
陶臨沅神色迷離,喃喃道:“你阿娘也不喜歡我喝酒……”
說罷悔恨地蜷成一團,竟像個無能為力的孩童。
吳氏聽見那句“阿娘”,有如醍醐灌頂,這才知道面前的女郎不是什麼侍妾,而是身份尊貴的宰相之女。
她是皇上親封的廣靈郡主,是楚國公殷如的寶貝外孫女,方才她差點對她不敬,真是不要命了。
陶嫤睇向陶臨沅,只覺得他的話好笑,“你也知道我阿娘不喜歡?”
她長袖一揮,桌上的酒悉數打翻,蹙眉質問:“你為何現在才知道?我阿娘在世時,你在誰的懷裡喝酒?”
陶臨沅掩住雙目,嘶啞道:“叫叫,別說了。”
“我也不想說,我只是替阿娘不值。”陶嫤重新審視這個男人,年輕時他玉樹臨風,英挺瀟灑,如今看來,不過空有一副好皮囊罷了,“你配不上我阿娘。”
她踅身離去,菱花門闔上,腳步聲越來越遠,陶臨沅悔恨的面容被掩在門內。
重齡院前種著兩排石榴樹,每逢夏天開花時,遠遠看去火紅一片,花團錦簇,霎是喜人。
尚未走近,玉茗便驚訝道:“周郎君來了!”
陶嫤抬眸看去,果見石榴樹下立著個蒼色葡萄紋錦袍的男子,身形瘦高,面帶笑意。
直至陶嫤走到跟前,他抬手指了指金露軒的方向,露出關心之色。
陶嫤大約明白什麼意思,對此事不想多說,“沒什麼事,你不必為此跑一趟。”
說著便要步入院內,被他有些無措地攔下了。周溥又指了指自己心口,看她的眼神毫不掩飾關懷。
陶嫤一愣,心裡柔軟了些,“我沒事,這些天都好好的。”
周溥是她十年前買下來的官奴,後來見他舉止不凡,不似一般奴籍出身的僕人,陶嫤便有意讓人調查了下。這才知道他原本是揚州刺史之子,後因父親被人彈劾,涉嫌貪污,闔府獲罪。周刺史死後,他被編入奴籍,無意間落到她手中。
陶嫤覺得他身世可憐,便單獨讓他住了一個院落,平常沒什麼粗重的活兒,在屋裡看看書寫寫字就行了。
陶嫤自幼患有心疾,這兩年頻頻發作,他方才是在問她情況如何。
得知她沒事,周溥顯然鬆一口氣。他不能說話,兩人在這兒乾站著委實尷尬,他便識趣地拱了拱手,告辭離去。
陶嫤未做挽留,舉步朝院內走去。
鶴鹿同春影壁後傳來丫鬟窸窸窣窣的聲音,她一走近,那聲音便驀然停住了。幾個丫鬟戰戰兢兢地立成一排,“郡主。”
陶嫤乜去一眼,將她們的話聽了個大概。
原來今日是魏王江衡大捷歸朝的日子,城內城外圍滿了人,都想一睹魏王風采。
魏王江衡是當今皇上次子,出類拔萃,卓爾不群。自從十八歲被封王后,至今領兵勝仗無數,是整個大晉的英雄。
論輩分她得喊江衡一聲舅舅,可是陶嫤怕他,無論如何都喊不出口。
這次他從松州回來,聽說皇上有意退位給他。此事在長安引起軒然大波,無論重臣豪紳,或是尋常百姓,紛紛關注著朝中的一舉一動。
不過這事與陶嫤無關,夜裡吹熄了油燈,放下銷金妝花幔帳,她縮在錦被裡平靜地睡去。
睡到一半心口遽痛,壓抑得穿不上氣。陶嫤想出聲喚外面的丫鬟,奈何發不出聲音。她從小就有心疾的毛病,身上都會帶著藥丸,然而偏巧上回吃完了,丫鬟又沒來得及送上新的,未料想晚上就犯了病。
這一次來得比以往都強烈,她連呼救的力氣都沒有,眼前一黑,陷入混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