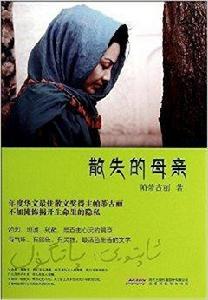內容簡介
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是怎樣在作用於一個人?語言怎樣爭奪著舌頭?文化怎樣爭奪著思維方式?故土怎樣爭奪著遊子的身體?母親與孩子的散失,兄弟姐妹間的散失,身體與靈魂的散失,自己與自己的散失,生命的無常帶給我們怎樣的人生思索與心靈感悟? 帕蒂古麗不容錯過的尋根之旅,如小說似寓言般的原生態非虛構散文,以細銳如刀的文字刻寫文化差異背後深刻的生命體驗。
作者簡介
帕蒂古麗,女,維吾爾族,文壇近年嶄露鋒芒的散文新銳,1965年出生於新疆沙灣縣老沙灣鎮
大梁坡村,現居江南,浙江《餘姚日報》記者,近年有40多萬字的作品見諸《人民文學》《散文選
刊》《上海文學》《青年文學》等刊物,已出版散文集《隱秘的故鄉》《跟羊兒分享的秘密》《混
血的村莊》等。
帕蒂古麗出生成長於天山下一個多民族共居的村莊,父親是來自新疆喀什的維吾爾族,母親是
來自甘肅天水的回族,近鄰多為哈薩克族,自幼就讀漢族學校,因而能熟練使用維吾爾語、哈薩克
語、漢語。帕蒂古麗用漢語寫作,雖非母語,帕蒂古麗卻憑藉過人的語言天賦,將漢語運用得熟稔
自如,出神入化。
帕蒂古麗的寫作,以散文見長,多民族融合文化下的獨特視角,使得帕蒂古麗的散文具有獨有
的特質和異樣的氣息,而多年職業記者的身份,又使得她的文章,對生命和文化有著深刻的思考。
所獲獎項:
2012第四屆在場主義散文新銳獎
2012《民族文學》年度文學獎
2012《散文選刊》年度華文最佳散文獎
2013“我的一封信”全國散文大賽一等獎
作品入選:
《中國散文年度佳作2012>
《2012中國散文年選》
《2013中國精短美文精選》
《中國散文年度佳作2013>
媒體推薦
帕蒂古麗揭開了一座新疆多民族共居村莊的塵封記憶。她的文字飽含對新疆這塊土地的複雜感情。優秀的文字都在撥開塵土,讓沉睡的事物重見天日。
—— 作家、《一個人的村莊》作者 劉亮程
帕蒂古麗的文字雜糅,撕裂,柔美,有狂歡與悲傷,信仰與苦難,神跡與幽默,這不是漢人眼裡的獵奇與風景,她用西方文學手法寫出了巨大的藍色蒼穹下十二木卡姆騰躍黃塵的新疆。
—— 作家家鮑爾吉·原野
一擊即中,直抵內心,卒讀不忍,罷讀不能,繼《隱秘的故鄉》後,帕蒂古麗再度以筆為刀,細緻、老道地剖解生活的核心。
——作家、評論家 楊廷玉
圖書目錄
混血的大梁坡
002混血的村莊
013大梁坡的氣味
018巴依居瑪的牧羊神鞭
036葬埋
大梁坡難以言說的人和事
044帕麗達:和老蘇家的雞肉談了一場戀愛
047黑皮:全大梁坡的女人,他誰都不愛
050瑪利亞:一年一年又一年隆起的肚子
053司馬義:他的老婆每天都拴在褲襠里
057那些曾經跟羊兒分享過的秘密
影子在時間裡行走
064夢裡紅樓
075影子在時間裡行走
082瘋長的紅柳林
088仇敵的咒語
怒放的凋零的古麗
092肉孜家的古麗
097吾爾古麗
100烏拉英家的古麗
親戚·舊事—我遺留在大梁坡的鮮活記憶
110不像驢的大黑驢
121繁密的西紅柿
124馬和驢,生出的是騾子
128早夭的大舅
131姑姑來了,姑姑走了
生命是一場散失
144生命是一場散失
155父親的罵聲
159致命的愧疚
163來自天國的棉花
174散失的母親
192送埋
生命中雜糅交錯的印痕
200傷痕累累的葫蘆
206施與受
210被語言爭奪的舌頭
224詞語帶我回到喀什噶爾
編後記
後記
在一場場散失中重生
王水
在編輯《散失的母親》過程中,帕蒂古麗另一本書《隱秘的故鄉》在南京簽售,原想陪古麗去玄武湖、夫子廟、1912等地轉轉,但見面後,哪都沒去。時值江南四月,窗外細雨飄飛,室內燈光閃爍,不合晝夜地聽古麗講新疆的故事,講家族的往事,聽她構思著將要出版的下一本新書。
“古麗”,在維吾爾族語言中是花兒的意思,草原或大漠長大的女孩兒,這個名字挺常見,就像藏族女孩兒起名“卓瑪”。但我最初稱呼她“帕提”,英文是Fatima。她是我認識的第三個Fatima,另兩個分別是埃及和沙特姑娘,都有一段難忘的同學情誼。Fatima這個名字,來源於先知穆罕默德最心愛的女兒“法蒂瑪”,據說她是德行最完美的穆斯林女性。
我們的這個帕蒂古麗,從新疆到江南,一路走來,人生的種種際遇,使她自己就成為一本本總也讀不完的書。這樣的經歷,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對生命的歷練和解讀,也是生長作家的最好的機緣。因為,作家只有經歷了廣闊的、超經驗的、無界限的空間,才能更好地實現精神活動和精神世界對世俗生活的超越。這位孤獨的行者,一直悄悄但有力地堅持自己。這在她的作品中也有體現,《生命是一場散失》《影子在時間裡行走》《被語言爭奪的舌頭》等等,皆是既觸動心弦又思想深刻的文章。建立在身份認同之上的親情、愛情,與之相關的困惑、糾結、和解,則是貫穿她作品的主題。她用凝練的語言、豐富的知識和人生體驗,把自己獨特的經歷和體驗高度集中,摒除所有外在的干擾,她的作品因而獲得獨特的印記。
現代人面對的生活變遷,是超越地域、民族、性別等身份標籤的。帕蒂古麗從一個位於大西北的維吾爾家庭,繞行廣州、鄭州,最終抵達浙江省餘姚市安身。這裡是河姆渡文明的發祥地,而這裡,仍不是最後一程,現在她意氣風發的兒子在天津讀大學,女兒從江南大學畢業定居寧波,家族的旅程仍在延續。
在古麗的多篇文字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疆老沙灣的大梁坡村開始的旅程,伴隨著怎樣的身份糾纏和困惑,糾集著怎樣的割合和包容。其實,類似的旅程,在我們許多人身上也在重複出現。都市化進程持續加速,幾千年的傳統生活方式和以血緣、地緣關係為紐帶的鄉村社會,在短短几十年內瀕臨瓦解,各種充滿遺失感的思鄉、回憶或者分析社會變遷的文章,都反映著我們這個時代的大背景。
帕蒂古麗不是特殊的,她是我們當中的一員。身份焦慮是持續不斷的困惑,這不是古麗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許多人共同的問題,它甚至和人類尋求更美好的生活、尋找自身終極意義的歷史,同樣漫長。
離開故鄉,我們往哪裡去?我們在這裡嘗試,又到那裡嘗試,種種嘗試,種種機緣,種種錯失,在生活壓力的慣性牽引或驅動下,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芳華逝去,在不知不覺中散失一個又一個旅伴,散失我們的一個又一個親人。走回故鄉,走在味道已經開始陌生的街上,我們找不到那些熟悉的老人,他們多已在祖墳里安息;我們甚至也不容易找到少年的玩伴,他們多已在異鄉漂泊。但是,也許在街頭遇到的哪個小孩,我們也許能從他們的面容、眼神中,叫出他們父母的名字。你看,生命是一場場散失,這樣的散失又何嘗不是為了一場場新的相聚?
當對身份困惑的時候,說明我們還在旅程中。而旅程,正是生命直接的證據。我們來了,我們活著,我們終會離去。人生就是這樣,有些人注定要散失,有些路程注定無法回返,但我們的情懷和對生命中美好事物的眷戀,繼續在途中以文字的方式散播種子,它因為一場場的散失,反而得以重生。
序言
撩人心旌的靈魂剖白
一個偶然機遇,我閱讀了維吾爾族女作家帕蒂古麗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的散文集《隱秘的故鄉》,並在浙江餘姚出席了這部作品的研討會。我一直揣測,既然帕蒂古麗早已安居江南水鄉,緣何又飽含深情,用細膩獨特甚至“刀子般犀利”的筆觸,對遙遠故鄉新疆大梁坡那些散發著苦澀和艱辛的生活境遇,來一番心情複雜的回眸和追溯?當我閱讀帕蒂古麗這部依舊由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的新作《散失的母親》之後,我覺得我最初的揣測不無來由,或者更確切說,我最初的揣測得到了印證。我篤信,帕蒂古麗其實是在下意識地尋找和確認自己的精神家園。雖然起伏顛簸的生活之舟,將她這位天性敏感的維吾爾族女子陰差陽錯載進山清水媚的河姆渡文化發祥地,而且那裡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對她又有那么強大的感染力,但連她自己都不得不承認,她的精神淵藪和心靈錨地,其實依舊縈繞在遙遠的大西北——新疆大梁坡,依舊牽繫在那個奇異的“羊跟羊混著放,狗跟狗混著耍,雞跟雞混著喂,牛跟牛混著養,驢跟馬混著配,人跟著人混著活”,世世代代麋聚著哈薩克族、維吾爾族、回族和來自甘肅、四川、河南、江蘇、山東諸多省份漢族人的獨特區域。
我依稀記得帕蒂古麗在《隱秘的故鄉》中那番自述:“往事就是我棄在野地上的尾巴,我會從現在的生活中停下來回望,等待丟失的尾巴找到我,接合在我的身體上”。很顯然,縱然帕蒂古麗的眉眼中早已氤氳著浙江餘姚的蔥蘢文氣,但在她靈魂深處依舊為那個遙遠的大梁坡保留一個無可替代的顯赫位置,仿佛一粒基因健康的種子,只要條件適宜,就會胚胎髮芽破土而出。古麗在《散失的母親》一書中,已將她的心靈軌跡草蛇灰線般勾勒出來。其中在《被語言爭奪的舌頭》一篇里,古麗有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描寫:“在烏魯木齊二道橋的街頭,我用漢語問一位榨石榴汁的維吾爾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錢一杯?’大娘兩隻灰綠色的眼睛在我身上從頭到腳滾了一遍,不緊不慢地反問:‘你明明是維吾爾族,為什麼對我說漢語?’我以為她不會認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剛從南方來,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徵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歲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麼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驚多於尷尬。我沒想到的是,這樣一個同族老大娘用詰問的方式,將多年來游離於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歸還給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鏡子前,清晰看見了那個被這片土地認可的自己。”
這段看似順手拈來的細節,恰好披露出古麗久別故土的漂泊心態和重返家鄉的意外驚喜,一種失而復得的情愫似乎令她那顆多年來躁動不安的心靈暫時安頓下來。如果說《隱秘的故鄉》是帕蒂古麗石乞石乞追尋自己精神淵藪和心靈錨地的上篇,那么《散失的母親》無疑是這種砣石乞追尋的下篇。耐人尋味的是,“故鄉”和“母親”,這兩種意象在本質上是那么高度疊合,而且前者已成“隱秘”,後者已然“散失”,這兩種意象無意中生髮出來的象徵意緒是那樣頑強地引發我們的無盡慨嘆和沉思。當下的人類不也正好處於這種惶惑的窘境?“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雖然當年被貶謫的韓愈黯然神傷的是自己的多舛仕途,但“家何在”的困惑卻是人類面臨的共同主題。從這個角度去打量帕蒂古麗這部新作《散失的母親》,我們會發現,這無疑是一部凸顯普世價值和美學特徵的上乘佳作。
姑且讓我們跟隨作者的筆觸,走進那雖然苦澀、艱辛、沉重卻又不乏樂觀、頑強、向上,雖然真實得仿佛伸手可及卻又散發著某種魔幻色彩的新疆大梁坡以及與之毗鄰的多民族聚居地。
這是一個瀰漫著濃濃民族融合氣息的棲息地。無可否認這裡的貧窮和落後,但也無可否認這裡世俗生活的獨特和新奇。
且看下面這段文字:
“河南人的麵疙瘩被四川人學了去,四川人的麻辣燙被甘肅人攪到了鍋里,山東人乾脆把甘肅酸菜味、陝西陳醋味、四川麻辣味一鍋燉三省,江蘇人嘗嘗味道也不錯,照著做好,再在裡面撒上一把糖,吃得很香。大梁坡人做飯的時候,聞一聞漢族莊子飄蕩的飯菜味,就是一股濃濃的大梁坡‘轉子’味”。
這個“轉子”就是古麗筆下的“混血”。如果說漢族莊子這種“混血”氣息已經很鮮活了,在民族莊子裡就更濃郁。古麗這樣描寫:
“哈斯木家的辣椒炒茄子,哈尼帕家的豇豆炒雞蛋,烏斯曼家的土豆燒洋蔥和回族人家的白菜蘿蔔燉粉條,飯菜雖是在各家的鍋里翻炒攪和,卻是你家的菜里有我家的肉,我家的菜里有你家的調料,他的飯里有我家的油鹽,這飯菜也是‘混血’的。”
大梁坡的少數民族人家,油、鹽、醬、醋、茶、奶、蛋很少有置備齊全的,多數是互相接濟、串換。一家宰了羊,全村人家的菜里就都多了葷腥。明明五口之家吃的飯,說不定呼啦啦來了四五位客人,無須現張羅,早有準備,一樣夠吃。來自江蘇太湖之濱的南方人蔣氏夫婦,硬是用南方人酷愛的魚腥改造了大西北的羊膻,本來到處飄著羊膻味的大梁坡,一下子變成了羊膻和魚腥味道混合的村莊。乍看去,諸多生活場景和生活細節的逼真描繪,將一個雖然偏僻、貧瘠但卻充滿淳樸、友善、和諧的大梁坡惟妙惟肖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顯然是溫馨、友善、和諧的溫暖場景,是真實生活的一個側面。
當然也還有另一面。
素有“牧羊神鞭”之稱的巴依居瑪兒女們的婚事有喜有憂,令人嘆惋。
老蘇家大兒子伊斯馬爾的愛情則有點讓人哭笑不得。愛上插隊女知青帕麗達的伊斯馬爾煞費苦心地用肥美雞肉吸引意中人,虔誠地期冀美麗的姑娘會成為自己的新娘。只是隨著知青的返城,這件事成了一樁笑柄。村里老少都覺著老蘇家最終會賠賬,奚落滿身臭皮子味兒的伊斯馬爾想迎娶人家香噴噴的城裡姑娘是狗啃星星心存幻想。村里人計算著,老蘇家為食誘帕麗達先後宰過上百隻雞,有人乾脆稱帕麗達是黃鼠狼,一見她去老蘇家,就戲謔地說她去給雞拜年,待雞吃光了,人也不見了。
這種令人惋惜、同情的故事主角還有“一年一年又一年隆起肚子的”瑪利亞,她的丈夫奈比約拉,以及他們接踵而至來到這個紛擾世上的眾多女兒。古麗這樣描述:“奈比約拉的女兒們像胡麻地里的麻稈子,密密匝匝,細細瘦瘦,一叢叢站在大梁坡上,竟然成了一片風景”。古麗的弟弟考取大學,為了湊夠學費,姐弟倆登門去向奈比約拉討債。“跨進門檻,掀開門帘一看,土炕上橫七豎八躺了滿滿一炕女娃,七個姑娘擠在兩條被子下面,最小的兩個,跟奈比約拉和瑪利亞疊作一團”。面對此景,古麗的感慨呼之欲出:“灰突突的炕上、葦席、氈子、被子似乎被光景拉扯得東破一塊,西爛一片,完整不起來。被面上儘是大窟窿小眼睛。髒污得看不出年份的棉花,碎得一塊一塊的,碎塊與碎塊之間,只有幾根頭髮絲一樣細的棉線連綴著,中間網子露著女孩子們的細皮嫩肉。”這是怎樣細膩傳神又觸動人心的描寫,用人木三分形容真的不為過。
這是苦澀、酸辛、令人扼腕嘆息的另一面。
當然還有幾個名叫古麗的女子的婚姻和愛情,都令人唏噓不已。
也許是大梁坡生活色彩太豐富,古麗隨意捻取的細節和場景,不僅有令人欣慰的溫暖和令人潸然淚下的悲涼,甚至還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當然那種幽默絕不是簡單的調侃逗趣。譬如被稱為“石頭人”的司馬義,他的吝嗇和小精明在整個大梁坡堪稱“翹楚”。古麗選取大量細節,栩栩如生刻畫出他的性格特徵。大梁坡人都曉得,司馬義有一塊很大的吸鐵石,出門時就用草繩拴著,一路走去,將地面上的鐵傢伙全都拎起來。玉努斯家拖拉機的螺絲,木那瓦爾腳踏車上的鋼蛋,吾拉別克馬蹄上的半個鐵掌子,還有不知從誰家驢車、馬車上掉下來的鐵釘子,扔在路邊的廢鐵絲,全都被司馬義的大磁鐵一掃光。村里人只要一見司馬義出來“掃路”,都趕緊把自家的鐮刀、鐵叉、坎土曼、鐵鏟、鋤頭都收起來,就連剪刀、菜刀、錘子、鉗子、錐子、鐵盆、鐵罐,也都不敢隨便放在院子裡。最令人想笑卻又笑不出的,還有司馬義居然獨出心裁,給自己設定一個物件,代替所謂的“老婆”,解決男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那個軟塌塌地垂在松垮垮褲襠里的油光光的木頭圈”,竟是司馬義“拴在褲襠里的老婆”——他之所以要這樣,竟是因為他不願討老婆,因為“多個女人多雙筷,還要給她買衣服穿!”這幾乎令人難以置信的荒謬理由,我想人們閱讀之後,該會先是捧腹大笑,然後笑聲也會漸漸變成嗚咽吧。人們不免質疑,難道司馬義僅僅是因為吝嗇才不討老婆么?吝嗇的起因常常因為貧窮,人們實在是窮怕了!
雖然,大梁坡的人祖祖輩輩都在貧窮的泥淖中掙扎,然而他們卻活得有尊嚴,有人格,重情義。譬如書中篇幅不長的《葬埋》,平實質樸的文字中濃濃充盈著人格的力量和友情的純真。故事的起因是文革中的大梁坡代銷店大鐵鎖天黑被人撬開,丟了些紅糖和棉布。造反派懷疑一位叫尹文福的會計監守自盜,偷了代銷店的東西給坐月子的老婆和剛出生的孩子。不堪凌辱的尹文福居然用刀抹了脖子,以此證實自己的清白。這固然有些走極端,但尹文福重視個人名節的性格毫髮畢現。也許正是他這種性格,他生前結識了一位肝膽相照的朋友,古麗的父親伊布拉音。伊布拉音為他挖掘一個碩大的墳坑。因為做一口棺材需要三天,為了防止死者的屍體被餓狼野狗撕扯吞噬,伊布拉音甘願被蚊蠅叮咬,竟在尹文福橫屍的麥地里,看護了死者三天三夜。埋葬死者那一天,伊布拉音在他挖的大墳坑邊沿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嘟嘟囔囔:“稀里糊塗就往裡面填土,你們看清楚了沒有?下葬的是我!你們埋錯人了,躺在坑裡的明明是我,你們咋把我活埋了!”說完蹲在墳坑前放聲大哭。這是何其撩人心旌的描寫。我還記得我曾在《隱秘的故鄉》研討會上說,帕蒂古麗的語言是刀子,是裹在棉花里的鋼針,倘若讀者諸君讀了《隱秘的故鄉》對我這樣的評論尚存疑義,不妨翻閱古麗這本新作《散失的母親》,我想讀後該會對我的這個感覺抱持同感。
恕我連篇累牘引用帕蒂古麗筆下的片段,因為我覺著多少鑑賞文字都沒有《散失的母親》若干文本來得更恰切更精彩。
當然最能表現帕蒂古麗這部新作題旨的,還是她對因為精神失常而一朝走失便一世訣別的母親的深情描寫。因為篇幅所限,我在這裡簡要轉述帕蒂古麗關於母親走失的若干文字。古麗剛滿四歲時,她的母親就患上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病因竟是一把刀,就是上文說的尹文福刎頸自殺用的那把刀。因為被造反派懷疑偷盜代銷店的紅糖和棉花,尹文福這個從內地下放到大梁坡,把臉面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知識分子悽然刎頸自盡。下葬那天,也許是出於對死者的哀痛和保留物證的動機,古麗的父親伊布拉音竟悄悄地將那把斷絕生命鏈條的刀子,用手帕包著,放在大衣口袋帶回了家。晝夜擔驚受怕的古麗母親發現了這把刀子,無邊的恐懼立刻攫住了這位善良怯弱的回族女子,她瘋狂地將刀子投進灶火,又將烤紅的刀子舉過頭頂,丟進距家很近的老河壩,隨即自己也跳了下去。雖然因為河水不深,母親被救了上來,但從此之後,她就變得瘋瘋癲癲。雪上加霜的是,母親瘋癲之後,挨過所有生活重壓的父親,在兒女們長大成人後,也撒手人寰。這個風雨飄搖之家,由古麗孱弱的肩膀吃力地扛起來。古麗將大梁坡的老房子交託給鄰居,用拉石頭的拖斗車,將對這個世界失去理性感知的母親,拉到距離大梁坡千里之外的塔城,那個令古麗日後魂牽夢縈的“紅樓”,在那兒一住就是三年。每逢寒暑假,古麗求學的弟弟妹妹相繼回“紅樓”和母親團聚。然而那是怎樣淒涼的團聚?母親對這個世界已經無法正常感知,對曾在她母腹中懷胎十月的孩子們已經無法傾注正常的母愛。她的身體和靈魂散失了,她也終會因此與自己的孩子們散失。古麗刻骨銘心地記著,母親第一次走失只有一天,她自己找了回來,臉被曬黑,嘴唇乾裂,臉上似乎還有一絲悔意。第二次走失時間略長,整整三天,就在古麗焦慮萬分之際,母親被一個好心的司機從塔城郊區一個牧場送了回來,甚至還穿戴得整整齊,乾乾淨淨,似乎她的神志已經清醒。古麗在痛苦的追憶中,一直心存疑惑,難道母親的前兩次走失竟是有意進行的預演?難道她是暗示可憐的女兒,她終究要徹底與她散失,不想繼續拖累女兒?總之那個寒冷的冬天,母親突然不見了,真的與她的兒女們散失了,這一次不再是一整天,不再是三整天,而是整整二十年!其後的日子裡,古麗和她的弟弟妹妹們,幾近瘋狂地尋找自己的母親。他們找遍那個不大的城市的每一條路、每一條河、每一條街道、每一個角落,找遍塔爾巴哈台山腳下的鄉村牧場、邊防哨卡……在電視、報紙、電線桿上遍發尋人啟事,都換不回母親的一絲信息。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這個世界跟古麗和她的弟弟妹妹開了一個惡毒的玩笑,將他們善良可憐的媽媽藏到了不可知處……
我一直在想,古麗之所以繼《隱秘的故鄉》之後,又情緒飽滿推出這部閃耀著她心靈光環的力作《散失的母親》,其實正是那種對母親、父親難以名狀的深深眷戀而轉化生成的巨大能量推動所致,也是人類追尋對精神家園的普遍認同和靈魂歸屬感的巨大動力牽引所致。正如她自己的真情告白:“這些年,我用母親的聲音禱告,我用文字把亡人跟我的生命連線,我一直用另一個人的身份生活,什麼都不做時,我偶爾回來,身份可疑。我抱住自己的身體時,感覺抱著父親蜷曲的骨骼,我想事做事的架勢很古怪,憤怒的時候是我爹,疑神疑鬼的時候是我媽,對我的孩子不得其解的時候,感覺那是來自父母血緣裡面的東西。疲憊時,我時常感覺媽媽在我身體裡呻吟,我不敢用她的嗓音說話,怕把自己嚇著。我不是我自己的時候,反而更像我自己,像記憶中小時候的我自己,那時候多好啊,那時候,我也是一個有母親的孩子。”
我嘆如泣如訴的心靈告白!古往今來,多少帝王將相、功名富貴,很快便是白骨荒丘,過眼雲煙,不朽的只有薪火傳承的聖潔情感和綿綿不絕的人文精神。“不假良史之詞,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我想帕蒂古麗回眸故鄉大梁坡的系列作品,將會以其獨特的藝術品位將這種聖潔的情感和綿綿不絕的人文精神傳承下去。
雖冗長,猶覺言不及義。是為序。
楊延玉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