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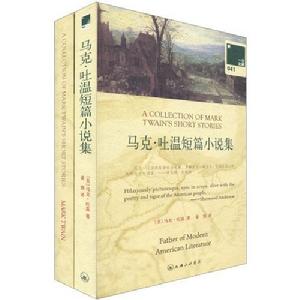 馬克吐溫短篇小說集
馬克吐溫短篇小說集一個朋友從東部來了信,我遵照他的囑咐去拜訪了好脾氣、愛絮叨的西蒙·惠勒,打聽我朋友的朋友利奧尼達斯·W·斯邁利的下落。這件受人之託的事究竟結果如何,我來做個交代。
我見到西蒙·威勒的時候,他正在荒廢的礦山屯子安吉爾那家破舊的酒館裡,在酒吧間的火爐旁邊舒舒服服地打盹。
“利奧尼達斯神父,嗯,利奧神——嗯,這裡從前倒是有過一個叫吉姆·斯邁利的人;可是不管怎么樣,這兒再也找不出一個比他更奇怪的人了。無論碰到什麼事情,只要能找到一個人在對方下賭注,他就和人家賭上了;如果人家要換一邊下賭注,他也樂意。要是碰上賽馬,收場的時候他不是贏得滿滿當當,就是輸得一乾二淨;如果斗的是狗,他賭;斗的是貓,他賭;斗的是雞,他還賭;嘿,就算有兩隻鳥落在籬笆上,他也要跟你賭哪一隻先飛。要是他看見一隻屎克螂朝哪裡開步走,他就跟你賭它多久才能到——不論到哪兒都行;只要你接茬,哪怕是去墨西哥,他也會跟著那隻屎克螂,看看它到底去不去那兒,路上得花多長時間。
“有一天,他逮著一隻青蛙帶回家去,說是要好好訓一訓;足足有三個月,他什麼事都不乾,光呆在後院裡頭教那隻青蛙蹦高。果不其然,他把青蛙給訓出來了。
“斯邁利拿一隻小籠子裝著那青蛙,時不時地帶著它逛大街、設賭局。有一天,一個漢子——是個外鄉人——到屯子裡來,正碰上斯邁利提著青蛙籠子,就問:
“‘你那籠子裡頭裝的是什麼呀?’
“斯邁利愛理不理地說:‘它也許該是只鸚鵡,也許呢,該是只雀兒;可它偏不是——它是一隻青蛙。’
“那漢子拿過籠子,轉過來轉過去,細細地瞅,說:‘嗯——原來是只青蛙,它有什麼特別的呀?’
“‘噢,’斯邁利不緊不慢地說,‘它就有一樣看家的本事,要叫我說——它比這卡拉維拉斯縣裡的哪一隻青蛙蹦得都高。’
“那漢子又拿過籠子,再仔仔細細地看了好半天,才還給斯邁利,不慌不忙地說,‘是嘛,’他說,‘我怎么沒瞧出來這隻青蛙比別的青蛙能好到哪兒去。’
“‘你也許瞧不出來,’斯邁利說,‘別管你怎么看,我心裡有數,我賭四十美元,就賭這青蛙比卡拉維拉斯縣隨便哪一隻青蛙都蹦得高。’
“那漢子琢磨了一會兒,有點兒犯難:‘呃,這兒我人生地不熟的,也沒帶著青蛙;要是我有一隻青蛙,準跟你賭。’
“這時候斯邁利說:‘好辦——好辦——只要你替我把這籠子拿一小會兒,我這就去給你逮一隻來。’就這樣,那漢子拿著籠子,把他的四十美元和斯邁利的四十美元放在一起,坐下等著。
“這漢子坐在那兒想來想去,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從籠子裡頭把青蛙拿出來,扒開它的嘴,接著掏出一把小勺來,給青蛙灌了一肚子打鵪鶉的彈子——一直灌到齊了青蛙的下巴頦——然後把青蛙放到地上。斯邁利呢,他上窪地的爛泥裡頭稀里嘩啦趟了一氣,到底逮住只青蛙。他把青蛙抓回來,交給那漢子說:
“‘行了,你要是準備好了,就把它跟丹尼爾並排擺著,把它的前爪跟丹尼爾的放齊了,我喊口令。’然後他就喊:‘一——二——三——蹦!’他和那漢子從後邊輕輕戳了戳那兩隻青蛙,那隻新來的青蛙蹦得特有勁,可是丹尼爾吸了一口氣,光聳肩膀——就這樣——像法國人似的。它壓根動不了,跟生了根一樣,像座教堂似的巋然不動,連挪挪地方都辦不到,就像拋了錨。斯邁利既納悶,又惱火;當然啦,說什麼他也想不通這到底是怎么一檔子事。
“那漢子拿起錢就走。斯邁利呢,他站在那兒撓著頭,低著頭盯著丹尼爾看了好一會兒,最後說:‘真鬧不明白這青蛙怎么栽了——鬧不明白它犯了什麼毛病——不知怎么搞的,看起來,它肚子脹得不輕。’他揪著丹尼爾脖子上的皮,把青蛙拿起來掂了掂,說:‘它要沒五磅重才怪呢!’他把青蛙頭朝下,結果青蛙吐出滿滿兩大把彈子來。斯邁利這才明白過來,他氣得發瘋,放下青蛙就去追那漢子,可再也追不上了。然後——
(這時候,西蒙·惠勒聽見前院有人喊他的名字,就站起來去看找他有什麼事。)不過,對不住了您吶,我想,再往下聽賭勁十足吉姆·斯邁利的故事,也打聽不到利奧尼達斯·W·斯邁利神父訊息呀,於是我拔腿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