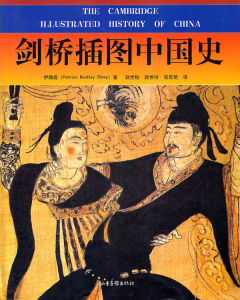簡介
 《劍橋插圖中國史》
《劍橋插圖中國史》《劍橋插圖中國史》探討了中華文明形成的諸多基本問題,涵蓋了中國歷史上的藝術、文化、經濟、社會、對婦女的態度、對外政策、移民以及政治等方方面面。尤其側重考察了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及其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為了避免外國學者闡釋中國歷史的局限性,作者儘可能地參考了中國各界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發展走向的闡釋。
《劍橋插圖中國史》闡釋了8000年的中國文明史——從史前時代到儒學、佛教的興起,從王朝帝國到現代共產主義國家。
本書由美國著名漢學家撰寫,配有珍貴豐富的歷史圖片。它探究了各種不同因素和力量觀念和發明、歷史事件和領袖人物在中國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它追蹤王朝的興衰、佛教的傳入、技術的進步、人口爆炸和“文革”動亂——它內容廣泛,從有影響的史學家、詩人、作家,到對中國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哲學、宗教、家庭模式以及外族的入侵……
本書翔實、生動、形象,是對中國歷史及其社會文化感興趣的讀者的必讀書籍。
本書前言
最初讓我寫作本書是為出版一套世界各國的圖說歷史,面對的是英美的一般讀者。它必須很簡明,要避免出現太多讀者不熟悉的名詞和術語,儘可能好地利用圖片資料。儘管我以前作為研究唐宋史的專家寫過學術性的著作,也為大學裡學習中國史的學生編過資料,但我此前從未試圖為普通讀者撰寫關於中國的書。為了讓那些隨時都會會上書的成年讀者興趣盎然,我試圖著重勾畫一兩個有關中國的最緊要的問題:它的巨大和歷史連續性。這十多億人口――比東歐、西歐和北美人口的總和還多――逐漸認為自己擁有相同的文化,享有認同感,這是怎么發生的?為什麼他們沒有像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那樣,因在方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的差異而分裂成一個個相互猜忌的群體?在本書中,我試圖表明,有幾個因素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其中包括中國的地理位置、它的形聲書寫系統,以及強大統一政權的長期經驗。以比較的視野來看,中國歷史的長期性也是很突出的。多年來,中國史學家集中解釋了王朝的興衰,但在世界上多數其它地方卻不是王朝而是整個文明此興彼衰。人們發現,現代史家可以從當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思想或制度,追溯到埃及人、蘇美爾人、希臘人、羅馬人、馬雅人、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但沒有哪一個現代西方國家是這些文明的直系子孫。人口隨著連續不斷的移民和人侵浪潮而變化,新的宗教則創造了與過去一刀兩斷的意識。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類型的例外?難道中國從未遭受過同樣的毀滅性的打擊嗎?新民族的涌人從未有這樣大的規模?新的思想或宗教對於人們的認同感從未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或是中國人在別的民族注意非連續性的地方選擇留心連續性?儘管我不會離開中國歷史經驗的特殊性質,但在本書中,我更強調中國文化,在其他文化注意非連續性的地方注意連續性的趨勢。 在寫作本書時,我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就是對付這些問題而且不會非要有個所以然不可。因為我相信歷史充滿了偶然性。我已試圖表明在各個時期,在創造我們稱之為中國的這個社會的進程中,中國人如何利用他們繼承的遺產,以及他們在拚命發現意義與和平、強加他們的意願或與對手競爭、倖存和發達、關懷其家庭及履行其責任的時候,如何提出新思想、進行新實踐。依我看,中國的今天植根於一個複雜的、多層次的、有活力的歷史之上,它總是具有潛力,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發展,這意味著每一個階段都是故事的精華部分。我希望,這個譯本的中國讀者會發現我作為一個外人的興趣所在。儘管研究中國史的西方學者利用的史料與中國史學家的相同,但他們提出的問題卻迎然不同。我期望著能從中國讀者對我的努力的反應中獲得教益。文章節選
對中國文化和體制的再評價・
在古代,當中國人初次對其在世界上的地位進行思考時,思想家們很自然地將中國視為沙漠中的文化綠洲,世界上惟一有文字、城市和先進制造技術的地方。唐朝時,這一觀點已不再令人信服。因為在幾個世紀中,香客和僧侶經常往來於中國和印度之間,他們使中國人了解到印度的書寫傳統足以同中國相匹敵。此外,中國的近鄰也不再是原始部落:高麗、渤海(位於東北)、南詔(位於雲南)、吐蕃和日本都建立了國家。它們都有統一的宗教,有書寫文字(有的發明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城市井進行長途貿易。在很多方面,中國可以自認為優於其它國家,但不能再以惟一的文明之邦自居。初唐時,各國均承認中國在政治、體制和文化諸方面都有傑出的建樹。實際上,朝鮮和日本的君主往往照搬中國文化和政治體制,以求建立其本國強大的政治中心。然而在晚唐時,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危機感,此種危機感使許多有識之士對中國政治和文化的基本問題進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此過程中,儒學得到了復興。杜佑(735年一812年)和韓愈(768年一824年)這兩位著名文人的觀點,可以作為這一思潮的代表。
杜佑出身於名門望族,曾在地方和朝廷擔任要職。801年他將《通典》一書上呈君主。《通典》為一部長篇典章制度史,共200卷(今版約5000餘頁)。當時,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危及朝廷的權威,杜佑編纂《通典》是為了尋求扶危解困之道,目的是為了改革朝政,加強朝廷的權威,使君主能夠干預地方事務。當然,絕大部分朝官相信君主為國中第一人,是一切的中心。但是,杜估認為,官吏們有關朝廷體制的觀點已陳腐過時。他們強調君主受命於天,主持禮儀慶典,但忽略了政府運作之道。就體例而言,《通典》一反傳統的寫法,不始於宮廷禮儀,卻以食貨、人民生計、政府財源為首要。在討論賦稅時,杜佑對隋朝官員高領稱讚備至,高�G根據均田制實行輸籍法。在北朝時,戰亂不斷、暴君庸吏、重稅搖役迫使百姓尋求地方豪強的庇護。但在隋朝建立後,百姓發現政府租稅大大少於豪強所奪,於是他們紛紛向政府登記戶籍。因此杜估認為,賴高�G之力,隋朝才能在全國建立財稅制度,百姓才能安居樂業。正如事後我們所看到的,晚唐政府對經濟的不干預政策有其積極意義,但依杜佑之見,計畫嚴密的政府控制要比對百姓放任不管好得多。
杜佑尤其反對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他們認為政府應該效法經典中所敘述的古制。杜佑駁斥說,在遠古時期,中國同現在邊境附近的一些蠻族一樣落後。他認為在漢唐時臻於完善的郡縣行政制度優於周代的分封制,因為郡縣制有利於長治久安,人口增長。為《通典》作序的學者說,杜佑認為位尊者應該認識到,其主張目的在於使國家有序,而使國家有序則在於行事有成,行事有成又在於能學習過去,學習過去又必須根據時勢的需要因時而變。
杜佑的同代人韓愈比杜佑年青,他更多地從文化方面來審視中國的問題。韓愈極力推崇儒學,力主儒學經典為教育和寫好文章的根基。根據簡明實用的古訓,韓愈贊成樸素的文風。像杜佑一樣,韓愈也關注軟弱無力的朝廷,但他相信復興儒學可以使國家強盛。他上疏皇帝,反對皇帝參拜佛祖的遺骨。在上疏中他將佛教稱為蠻族的信仰,說佛骨是污穢不祥之物,不應觸摸。他爭論說,皇帝尊佛是鼓勵百姓信奉佛教而不務正業、不盡社會義務,這樣便減少了稅收,對國家不利。在另一篇幾乎同樣有名的文章中,韓愈討論了道的起源。韓愈認為,一脈相承的正統儒學,從周公傳到孔孟,然後這一傳統就中斷了。在某種意義上,韓愈主張為復興“聖人之道”必須讀《論語》和《孟子》,以發掘真正的儒學。像杜佑一樣,韓愈用非常寬泛的概念對中國文明進行了綜述,但敘述簡明扼要:中國文明始於聖人,聖人救百姓於危難,教他們獲衣食,退野獸,習禮樂,教他們創立政治制度來抵禦敵人,肅清罪惡,但是道教和佛教的興起卻使中國文明墮落了。最後,韓愈主張讓佛僧道士還俗,焚毀佛經道經,將廟宇改建成家庭宅院。
當然,杜佑和韓愈的看法在很多方面相左。杜佑堅持應了解變化,了解具體實踐的細枝末節。而韓愈更強調一成不變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認為在政策層面上應重視德行,君主應掌握“聖人之道”。杜佑主張循序漸進地追溯歷史的發展,而韓愈則以為可以將中間的幾個世紀一筆抹煞而一下躍回到遙遠的古代。然而,二者確乎在某些問題上頗為一致。例如,他們都對自漢朝以來廣為流行的君主受命於天的理論不感興趣。而且,他們分享一種基本的樂觀主義精神,認為只要好人在世上有所行動,一切就會變得更好。他們的這一觀點為很多同代人所贊同,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活躍了當時思想界的論爭。
根據中國人的歷史觀,統一與擴張遠比分裂與收縮對中國人有利。因此,唐朝上半葉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之一,而下半葉則被認為是它不幸的餘暉。按照中國傳統史學家的看法,朝代的進步基於可以預料的道德原動力,因此唐朝的由盛而衰也就並不出人意料。像唐朝這樣輝煌的朝代是由精力充沛、意志堅定的君主建立的,他們因為民謀利益而受命於天。他們創立了高效率的政府,租稅既低且公平,他們清除了很多前朝的積弊:諸如地方割據和貪污腐敗。但他們的皇位繼承者並非都是過人之輩,很多繼承者不能避免宮廷中的權力之爭,不能限制防衛開支和地方行政開支的增長,不能保障或增加歲人來源,不能憑藉其毅力和操守而使臣下忠心耿耿。依據這一歷史觀,幹練正直的君主或宰相可以延緩衰落的進程,甚至可以暫時起死回生,但一個朝代必然會由盛到衰,最終滅亡。
傳統的中國史學家認為,並無類似的道德邏輯可以代代相傳,使各朝各代永遠照此行事。所以,當中國史學家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次接觸到歐洲的歷史直線發展理論即從古代到古典、經中世紀到現代文明之時,他們也開始構想中國歷史的宏大分期。正如前文所述,他們注意到漢朝與羅馬的相似之處,大分裂時期與歐洲中世紀的類似之點。但是隋唐時代的一統天下卻無與倫比。在西方,不論是6世紀時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還是9世紀時的查理曼大帝,都未能重建一個如此遼闊而又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帝國。在中國,唐朝更優於漢朝――唐朝能夠抵禦更強大的外來威脅,能夠治理一個更加多樣化的社會,而且建立了更為發達的經濟。
目前,接受中國歷史循環發展這一觀點的史學家,已經為數不多了。這一觀點貶低了中國社會的長期變化,而按照西方模式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個或四個階段的史學家也不多見。一般來說,在探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的時候,史學家們更關注晚唐,並將其看作個十分重要的轉折點,認為這一可悲的衰落時期也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令人振奮的發展階段:知識分子為朝廷無法控制國家而憂心忡忡,因而產生了一直延續到宋朝的聲勢浩大的儒學復興思潮;中央政府無力對經濟嚴加管理,影響了財政收入,但卻使經濟活動更加活躍。由於出現了這么多混亂而且令人頭痛的問題,國家政治和軍事體制的集權化程度比以前降低了,但中國社會承受政治危機的能力得到加強。
作者介紹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在東亞研究領域,她著述頗豐。著有《中華文明史資料》、《中國唐代和宋代的宗教與社會》等著作,其中《屋裡人:中國宋代婦女的婚姻與生活》於1995年獲得約瑟夫・P・利文森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