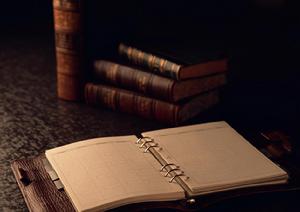 新歷史文學
新歷史文學特點
 新歷史文學
新歷史文學現實性。它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簡單地、表面地連在一起,不是為了說明現實中的某個觀點和某種思想去演繹歷史,更不是借古喻今,而是一種內在的聯繫,是歷史與現實兩個闡釋維度的聯繫。作家對歷史的理解、感覺和激情,說到底是由現實所給定的,他絕不可能離開現實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知識結構的影響。所以說作家的歷史敘述是從現實的社會生活關係中產生出來的。新歷史小說“新”在它包含了新的社會歷史觀念。
深刻性。新歷史小說由於它與現實社會進程有著內在的聯繫,因此它是在一種新的高度上思考過去,是用新的思維詮釋歷史的,是在一個開放的、現代的、新的語境中表現歷史事件的,所以可以做到更準確,更客觀,也更深入。新歷史小說的深刻性包含著新的歷史文化理念和新的歷史文化精神;包含著新的社會價值判斷和新的時代及民族情感。我們通過小說中各種人物的細膩的心理分析,體會到戰爭不僅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而且是文化的鬥爭,是文明的抗爭,歸根結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較量。
重要性。即在當今文學走向中的意義和作用。在文學中提出重寫歷史或重審歷史的觀點和與此相關的寫作已有很長時間了,不乏各種突現個人情感和想像的歷史演釋。但相比之下新歷史小說,或者說新歷史文學更尊重歷史,更看重歷史的本質性特點和基本精神。它們既是對傳統的突破,又是對歷史虛無主義寫作的否定;在批判中體現了繼承,在解構中強調了建構。它把“自我”導入歷史社會激情里,把歷史批判納入到社會重建之中,把對現實的關注融合在歷史的長河裡。它注重歷史的連貫性和統一性,這不僅對歷史文學,而且對整個當前文學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論興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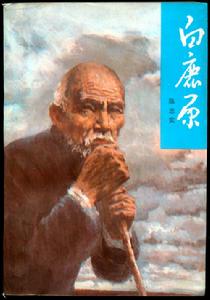 陳忠實《白鹿原》
陳忠實《白鹿原》新歷史小說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有著新的歷史意識的創作思潮。因其與西方的新歷史主義同樣具有新的歷史觀,學術界在對其命名和界定時存有歧異。從對新歷史主義和新歷史小說的歷史精神的分析,可以看出兩者在歷史精神方面有著極大的差異。新歷史小說是在各種思潮影響下,新的創作模式與新的歷史意識相結合的產物,而不是新歷史主義理論的闡釋和說明。
對於新歷史小說產生的原因,研究者們基本上沒有大的歧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認為:新時期文學“經過短暫的修復歷史的敘事”(如《天雲山傳奇》、《大牆下的紅玉蘭》)“隨後進入反省歷史的敘事”(如“人性論”、“人道主義”、“主體論”、“異化””的提出),接著是“對歷史本身進行直接的質疑”。“由此出現了一部分小說重新審視革命歷史年代的故事”(如李曉的《相會在K市》、潘軍的《風》、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陳忠實的《白鹿原》等),“對歷史直接的審視必然導向對歷史觀念本身的質疑”(如格非的《褐色鳥群》、《青黃》等)。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孫先科認為:“新歷史小說正是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出現裂縫和作家文學編碼意識加強的前提下出現的,它直接的思想源頭有三個:尋根小說對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棄而親和世俗性、‘史’'性題材的傾向和先鋒小說的文本戲擬對意義消解的傾向以及新寫實小說向世俗性價值妥協退讓的趨勢。”
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顏敏認為,新歷史小說分為四個階段:“1986年有喬良、張煒、莫言和周梅森;1987年的先鋒作家有洪峰、蘇童、格非、葉兆言;1989年的新歷史主義作家群,包括蘇童、格非、余華、葉兆言、劉恆、方方、池莉、李曉、楊爭光等;1992年之後的家族小說作家是李銳、陳忠實和張煒。”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清華把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勾勒為:作為前提和基礎的1987年以前的啟蒙歷史主義階段。作為主體的1987年-1992年的新歷史主義或曰審美歷史主義階段。這一階段又可以分為1987年-1990年前後的,以近現代歷史背景為空間、以中短篇小說為主的近世新歷史小說和1990年-1992年出現的第一批長篇新歷史主義小說及1992年之後的家族長篇小說三個部分。作為餘緒和尾聲的1992年以後的遊戲歷史主義階段。顏敏、張清華的文章分別刊發於1997年、1998年,可以視其為是對新歷史小說發展過程的一種總結性回顧。但是,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學昕對90年代的新家族歷史小說,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馬相武對90年代更方年輕一代作家的新歷史小說仍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對新歷史小說衰落的原因,研究者們的看法也比較一致。張清華認為,1992年之後,新歷史小說“離歷史客體愈來愈遠,文化意蘊的設定愈加稀薄,娛樂與遊戲傾向越來越重,超驗虛構的意味愈來愈濃。新歷史小說的‘新’似乎正越來越與無數迎合大眾口味與商業規則的‘舊’小說重合,並主動迎合影視大眾藝術的要求與口味,這似乎已標誌著這場歷史與文化烏托邦式的藝術運動的最終衰變與終結”。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從民間立場自身的缺陷這一角度出發,認為:“土匪故事和家族史故事這兩大民問題材是新歷史小說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民間因素並不能保證文學藝術對世俗力量的抗拒,相反,當影視的商業手段利用這兩大民問題材來迎合海外市場的需要時,文學史落到了影視皇帝的‘后妃’的可憐地步。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蔡翔從歷史小說作家新的精神立場的缺失這一角度指出:“如果沒有更為強大的思想和堅定的信念導引,在對現實的妥協與認同中,新歷史小說“很快就會淪落成為取悅大眾並走進大眾消費”。
對於新歷史小說興衰與西方新歷史主義的關係,研究者們論述不多但意見比較一致且十分到位。張清華認為:“在80年代中後期,新歷史主義作為獨立的理論方法尚未得到評介和關注,因而不能想像在國內已經出現了一股以新歷史主義方法為指導的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但是,毫無疑問,作為西方新歷史主義的基本方法的結構主義乃至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在80年代中後期卻已對當代中國的學術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反映在文學的歷史主題寫作中就是對以往的主流歷史採取了不約而同的拆解態度”。同時,研究者們清醒地看到了新歷史小說所體現的與西方新歷史主義相類似的特徵有著中國本土文學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性。張清華認為:新時期第三代詩歌群體“在1986年的詩歌大展中對自己的詩歌理論主張的闡述,實在已遠遠超過了同時期國內理論界對結構主義理論認識的深度”。對於新歷史小說興衰與西方新歷史主義興衰的內在關聯,程蓉有著十分精闢的概括:“由懷疑歷史文本,尋訪歷史真實到歷史真實的陷落,由挑戰權威歷史言說到過分放縱主體,把玩歷史的‘話語嬉戲’,中國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家與西方新歷史主義批評理論留下了一條極其相似的、耐人尋味的軌跡”。
發展走向
 劉震雲《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
劉震雲《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新歷史小說在許多作家的創作下呈現出了新景象。最先是依託“尋根思潮”而再度興起,在文化尋根的過程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對中國傳統家族文化進行探尋,對家族作“歷史記憶”式的展示。從時間跨度來看,對近代現代歷史進行回憶敘述的占主體。許多論者將這類家族題材小說歸為“新歷史小說”,因為在解讀歷史的時候,作品重在對被權威歷史話語所遺忘或棄置的家族(家庭)史和村落史的再現,昭示家族和村落在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80年代中期莫言的《紅高梁》,作品隱隱寫到“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家族記憶,凸現了戰爭背景中強悍的生命意識和久違的民族精神,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比較早的新歷史小說。之後出現的歷史——家族史結合的眾多小說,企圖需求與祖輩們的對話,演繹了“回憶性”或“尋宗覓祖”般的過去時敘述模式。整體而言,這些家族題材小說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以一個村落的興衰作為小說框架展開敘述,如張煒的《九月寓言》、《柏慧》,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等;第二類是敘述了一個個家族歷史變遷的秘密,在寫歷史的時候,更多地注重“野史”、“稗史”和“秘史”,注重人物的複雜的文化心史,歷史被換成了人的“心象”,如張抗抗的《赤彤丹朱》、張煒的《古船》、《家族》,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方方的《祖父在父親心中》等等;第三類是個人化敘事特徵十分突出的先鋒寫作,家族史、祖父、父親等僅僅是作者抒寫個人現代體驗的一種隱喻性的符號,是作家在現代社會繁雜、奔走中尋求的一種安慰,有的甚至從整體上將家族、血緣看成是一種“天意”和“命運”,如格非的《敵人》,歷史常常變成一些任意性的、神秘而怪誕的往事與回憶,歷史的真實“成了一種類似於瓦雷里的純詩一樣的‘純虛構’”。對家族秘史的書寫,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歷史的好奇感和新鮮感,增加了人們對歷史的完整把握。但是,由於後期的一些作品過度強調偶然性的因素並渲染宿命悲觀色彩,對人性中惡的一面無節制的宣洩、暴力、血腥、淫亂等泛濫,沒有提供積極的歷史動因以及人性完善的理想途徑,影響了家族題材小說的縱深發展。德國人類學家豪克指出:“在今天的文學藝術中,如果我們只表現焦慮之夢和絕望的歇斯底里,而不去表現希望和信心,乃至確信的情緒,那么毫無疑問,這只是表現了‘自然’生命的一半。”由此不難看出家族題材小說擱淺的重要原因。
中國家族題材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再度興起,並在90年代成為一大文學景觀,而在世紀之交逐漸退潮,可以從社會文化變革、作家心態調整以及讀者閱讀興趣轉換等多方面去探詢原因:
 王安憶《小鮑莊》
王安憶《小鮑莊》 韓少功《爸爸爸》
韓少功《爸爸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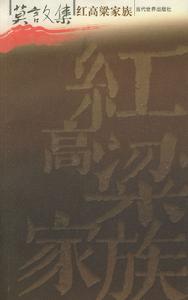 莫言《紅高梁家族》
莫言《紅高梁家族》然而,變動時代人們的心態是不穩定和矛盾的,另一類人群不滿現實的庸俗化,企圖從回憶或者想像中尋找歷史的動因和人性的變動,找尋一些積極的因子和自信的力量。人們不甘消沉於物慾的精神追求,融會著強烈的歷史懷舊情緒,再次造就了家族小說創作的熱潮。因為以家族生活為題材小說或多或少給現代人帶來心靈的撫慰與宗脈的認歸,獲得生命的力量。李光耀先生有一個譬喻能夠說明:“在經歷所有的那些動亂時,家庭、家族、氏族為個人提供了生存之舟。文明崩潰了,朝代為征服者消滅了,但這種生命之舟卻能將文明傳承到新的階段。”但是這時的作家,大都卻將目光投向中國家族中被壓抑的男女性愛畸形以及短缺經濟時代財產爭奪的殘酷性,將物慾、情慾無限虛構和放大。尋找的結果並不樂觀,除了迎合了90年代社會轉型時期讀者的獵奇心態外,大多數的作品染上了濃重的悲觀審美色彩。這種悲觀甚至宿命情緒,也是世紀末人們普遍感到困惑和對現實缺乏信心的表現。在這種情緒影響下,家族題材小說失去了前期宏大敘事時悲壯,多了一份自我無依靠的失落。面對讀者,家族題材小說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歷史的精神本身具有矛盾性,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後性。現實變動雖讓人困惑,卻是社會進步的必然選擇。人類畢竟不能生活在歷史中,只能從歷史中借鑑某種經驗。這就使家族題材小說崛起之後卻又無法應對新潮的個性化創作衝擊的難題。
代表人物
 陳忠實
陳忠實1965年初發表散文處女作《夜過流沙河》。1979年《信任》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2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鄉村》。1992年報告文學《渭北高原,關於一個人的記憶》獲1990年-1991年全國報告文學獎。
陳忠實創作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集家庭史民族史於一體,以厚重的歷史感、豐富的文化意蘊和複雜的人物形象而在同類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代文學中不可多得的傑作之一,被著名學者范曾譽為“陳忠實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書也。方之歐西,雖巴爾扎克、斯坦達爾,未肯輕讓。”,西方學者評價說“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說的技巧來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陸當代最好的小說之一,比之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並不遜色。”,獲得1998年第四屆茅盾文學獎。有的作品本翻譯成英、日、韓、越等國文字出版,其中《白鹿原》已被改編成秦腔、連環畫、雕塑等多種藝術形式,話劇、電視連續劇、電影正在籌備中。
迄今,已出版的作品有《陳忠實文集》7卷、《陳忠實小說自選集》3卷、散文集《生命之雨》、《家之脈》和《原下集》等7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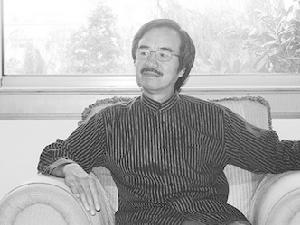 李銳
李銳197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迄今已發表各類作品百餘萬字。系列小說《厚土》為作者影響較大的作品,曾獲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和外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一樣,李銳的作品也曾先後被翻譯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蘭文等多種文字出版。2004年獲頒法國政府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出版有小說集:《丟失的長命鎖》、《紅房子》、《厚土》、《傳說之死》。長篇小說:《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銀城故事》。散文隨筆集:《拒絕合唱》、《不是因為自信》、《網路時代的方言》。另有《東嶽文庫•李銳卷》(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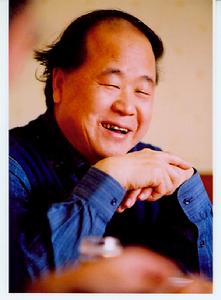 莫言
莫言著有大量中短篇作品《金髮嬰兒》、《爆炸》、《歡樂》、《紅蝗》、《築路》、《雨中的河》、《流水》、《棄嬰》、《貓事薈萃》、《玫瑰玫瑰香氣撲鼻》,小說集如《紅耳朵》及《傳奇莫言》亦先後在台灣推出。
出版有《莫言文集》五卷,長篇小說《紅高梁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 、《酒國》、《紅樹林》、 《檀香刑》,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紅高梁》、《牛》 ,短篇《拇指銬》等。
 劉恆
劉恆1977年發表處女作《小石磨》,至今已發表長篇小說《黑的雪》、《逍遙頌》、《蒼河白日夢》三部,中篇小說《白渦》、《伏羲伏羲》等近二十部,短篇小說《狗日的糧食》、《拳聖》等數十篇,電影劇本《菊豆》、《秋菊打官司》、《漂亮媽媽》、《張思德》等十餘部,電視劇本《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數十集。改編並導演電視連續劇《少年天子》。其中多部作品獲全國或地方文學獎以及國內外電影節和電視節的最佳影片獎、最佳編劇獎。多部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日、意、韓、丹麥等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發行,產生廣泛影響。已有五卷本《劉恆自選集》問世。2004年在“北京文學節”上獲得終身成就獎。他的一些小說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如《伏羲伏羲》、《黑的雪》以及長篇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主要獲獎作品有短篇小說《狗日的糧食》獲全國第八屆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天知地知》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獲第一屆北京市文學藝術獎。
 張煒
張煒主要出版詩集、理論集、散文集和長篇小說各種版本近百部,海內外獲獎30餘次,包括有重要影響的評選:台灣“金石堂最具影響力圖書”(《古船》,1989年);香港“華語小說百年百強”(《古船》,1999年《亞洲周刊》);國內“百年百部中國優秀圖書”(《古船》,2000年,北京大學等);國內“99年代最具影響力十作家十作品”(張煒與《九月寓言》,2000年,上海作協及全國百名評論家);國內“90年代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名列前矛,2000年,中國文化報等);國內“中國百年文學經典”(《古船》、《九月寓言》,1998年,北京大學);國內“百部文學名著名篇”(《古船》、《九月寓言》,2000年,《收穫》);“讀者最喜愛的十位作家”(張煒,名列前矛,1994年,《新華文摘》、《光明日報》等)。
自1987年以來,先後受邀到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國家圖書館、義大利東方大學、香港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一橋大學、台灣國家圖書館等眾多學府講學。自1999年起,長篇小說《古船》被法國教育部和巴黎科學中心確定為全法高等考試教材及必考書目。
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中篇小說《秋天的憤怒》、《蘑茹七種》等,短篇小說集、散文集《玉米》、《融入野地》、《夜思》等。現已出版《張煒作品選》五卷。
 周梅森
周梅森主要作品《周梅森文集》
中篇小說集《莊嚴的毀滅》、《深淪的土地》、《國殤》、《大捷》,長篇小說《黑墳》、《神諭》、《重軛》、《淪陷》、《我本英雄》、《人間正道》、《天下財富》、《中國製造》、《國家公訴》、《絕對權力》、《至高利益》,另有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隨筆多篇。
其長篇小說《人間正道》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第六屆五個一工程獎;二十八集同名電視連續劇獲中國電視飛天獎一等獎,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電視劇獎;長篇小說《中國製造》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第七屆五個一工程獎;中篇小說《軍歌》獲第四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二十二集電視劇本《天下財富》獲首屆全國電視劇本徵文一等獎;長篇小說《黑墳》獲全國煤礦長篇小說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