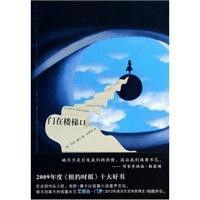內容簡介
 圖書圖片
圖書圖片《門在樓梯口》透過主人公塔西·柯爾津的眼睛,敘述了她二十歲這一年,發生在她自己以及周遭人身上的故事。她來自美國中西部一個農民家庭,父親種植各種形狀可愛的小土豆,賣給芝加哥等大城市的餐館。在鄉村長大的她,從未坐過計程車,從沒吃過中餐,直到上了大學,來到比較自由開放的小鎮特洛伊。
課業之餘,塔西為一對中產階級夫婦照看小孩。這家人的妻子莎拉在鎮上經營一家高檔餐廳,丈夫愛德華是位眼癌研究者,他們領養了一個有一半黑人血統的兩歲女嬰。可其實,莎拉並不叫莎拉,愛德華也不是愛德華,因為過去的一個疏忽,他們被徹底剝奪了為人父母的權利,縱使千里迢迢,從東海岸搬遷到中西部,改名換姓,也抹不掉過去的印跡。真相暴露,女嬰被律師帶走。塔西認識到,這個世界,“光有愛是不夠的”。
在講授伊斯蘭蘇非主義的課上,塔西結識了一個自稱巴西人、卻不會說葡萄牙語的男生。兩人相戀、墜入愛河。可男孩的真實身份令人駭然。不久,他離開小鎮,戀情終結。
塔西的弟弟沒有姐姐優秀的成績,考不上大學,選擇當兵,入伍不到幾個月,莫名其妙在阿富汗喪生。
塔西站在成人世界的門口,目睹和感受著人生的殘酷與悲傷,從政治、種族、戰爭,到愛情、死亡、謊言,這也許是一切成長的必經過程和代價。
編輯推薦
《紐約時報》二〇〇九年度十大好書
在這部作品之前,洛麗·摩爾以短篇小說蠻聲文壇,被與加拿大的短篇女王艾麗絲·門羅相提並論。
名人推薦
洛麗·摩爾是美國當代最讓人無法抗拒的作家:聰穎、悲憫、質樸、溫暖,舉重若輕的抒情文筆,兼具莉莉·湯普琳的風趣幽默。最重要的是,她不只是引發我們的同情,還讓我們痛苦不已。
——喬納森·勒瑟姆
媒體推薦
洛麗·摩爾是美國當代最讓人無法抗拒的作家:聰穎、悲憫、質樸、溫暖,舉重若輕的抒情文筆,兼具莉莉·湯普琳的風趣幽默。最重要的是,她不只是引發我們的同情,還讓我們痛苦不已。
——喬納森·勒瑟姆
摩爾以一種有節制的辛辣筆調書寫嚴肅的情感和政治問題,書中處處閃耀著她那無與倫比的智慧之光。
——《出版人周刊》
備受讚譽的小說家洛麗·摩爾擁有獨特的天賦。她的風趣令人驚愕——幽默之後,接踵而來的是可怖的悲傷——……
——《今日美國》
作者簡介
洛麗·摩爾(Lorrie Moore),一九五七年出生於紐約,十九歲時,在美國青少年雜誌《十七歲》舉辦的小說競賽中獲獎。一九八○年,進入康奈爾大學的創意寫作系就讀;一九八三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自助》(Self-Help),裡面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她在寫作班期間創作的。之後,洛麗·摩爾又相繼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像生活那樣》(Like Life)和《美國鳥人》(Birds of America)、長篇小說《字謎遊戲》(Anagrams)、《誰將開辦青蛙醫院?》(Who Will Run the Frog Hospital?)和《門在樓梯口》(A Gate at the Stairs)。其中,《你也很醜》(You’re Ugly, Too)一篇,被約翰·厄普代克收入他主編的《二十世紀美國最佳短篇小說》中。《門在樓梯口》更是入選《紐約時報》二○○九年度十大好書,並進入二○一○年度橘子獎短名單。她的作品榮獲過歐·亨利短篇小說獎、蘭南基金會獎和美國藝術文學院獎,還有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獎、Rea短篇小說獎和美國筆會/馬拉默德獎。《新聞周刊》評價“她是她那一代最詼諧、最有智慧的作家之一”。
文摘
那年秋天冷得較遲,令鳴鳥們猝不及防。風雪真正開始肆虐之時,太多的鳥已不得不滯留於此,它們未能飛往南方,只得蜷縮在人家的院子裡,膨起羽毛以求一絲溫暖。我當時正在尋找工作。我是名學生,需要找個替人照看小孩的活,故而才走在那些優美然而蕭瑟的小區里,從一個面試走向另一個面試,多得可怖的灰褐色鳩鳥成群啄著凍土,顯得驚恐無助——不過,即便在最好的情形下,又有什麼鳥不顯得有那么一絲無助呢——令人詫異的是,待一周將盡,找工作進行到尾聲時,那些鳥消失了。我不願細想它們到底怎么了。不過那只是一種說辭——出於禮貌,一種虛飾的委婉——因為實際上我一直在想著它們:想像著它們死去,在城外某片致命的玉米地里堆積成山,令人瞠目,或是從空中仨倆掉落,沿伊利諾州州界綿延數英里。那是在十二月,我要找份一月開學時開始的工作。我已經考完試,回復著學生公告欄里那些需要“兒童看護”的廣告。我喜歡孩子——真的!——好吧,其實也還好。有時候他們很好玩。我羨慕他們的精力和童言無忌。我跟他們也很合得來,因為我會對小寶寶做有趣的鬼臉,大孩子我則會教他們玩牌的伎倆,還會用譏諷的戲劇腔說話,令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不過我並不特別善於長時間照看孩子。我會覺得無聊,這點也許像我自己的母親。跟他們玩得久了,我的大腦就會感到飢餓,渴望一頭栽進自己背包里的某本書中。我總是希望他們能早點上床,或是午睡得久一些。
我來自古老的佩里維爾公路邊上的一個小農場,從德拉克羅斯中心中學來到特洛伊這座被譽為“中西部的雅典”的大學城,仿佛剛從某個洞穴里鑽出來一樣,好似我在《文化人類學》上讀到的哥倫比亞某部落的童祭司,那個在黑暗中度過大部分童年時光因而變得神秘的男孩,對於外面的世界只有故事可了解——沒有體驗。一旦被帶入光亮之中,他就會處於一種永遠令他目眩神迷的神奇境地;沒有任何故事能等同於事情本身。而我亦是如此。沒有什麼能讓我真正做好準備。不管是餐廳里的大學資金儲蓄罐、祖父母的儲蓄公債,抑或是那套用舊了的配有國際小麥產量的漂亮彩色插圖和總統出生地圖片的世界百科全書。我父母的農場,那個沒有豬沒有馬的單調綠色世界——它的沉悶,它的蠅蟲,它每日被機器的煙霧和尖銳聲音撕裂的平靜——盤旋著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由書籍、電影和風趣的朋友們構成的絢爛的城市生活。有人替我點亮了燈。有人把我帶出了佩里維爾公路的洞穴。我的大腦因喬叟、西爾維亞·普拉斯與西蒙·波伏娃而火花四溢。一位名叫薩德的年輕教授穿著牛仔褲繫著領帶每周兩次站在滿教室如我一般目瞪口呆的鄉下孩子面前侃侃而談,大談亨利·詹姆斯對逗號的褻瀆。我為之著迷。我以前從沒見過牛仔褲配領帶穿著的男人。
當然,古老的洞穴造就了一個神秘主義者;而我的童年只造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