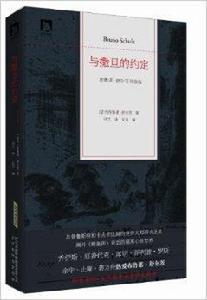內容簡介
揭開《鱷魚街》背後的暗黑心靈世界
珍貴書信+生平圖片首度中文面世
喬伊斯、厄普代克、庫切、菲利普·羅斯&余華、止庵、蔣方舟熱愛布魯諾·舒爾茨。
作者簡介
布魯諾·舒爾茨(1892—1942),波蘭籍猶太作家,死於納粹槍殺。生前職業為中學圖畫教師,出版過《鱷魚街》、《用沙漏做招牌的療養院》兩本小說集。布魯諾·舒爾茨生前默默無聞,死後卻以不可思議的文字征服了包括艾薩克·辛格、庫切、哈羅德·布魯姆、格羅斯曼、辛西婭·歐芝克、余華等在內的大批世界級作家。
布魯諾·舒爾茨被視為與普魯斯特和卡夫卡比肩的波蘭文學大師。他不但是一位作家,還是一位卓越的畫家,在歐洲超現實主義美術和電影領域有著重要的影響。自《鱷魚街》在中國出版以來,舒爾茨及其作品在中國有了眾多的愛好者。本書是布魯諾·舒爾茨生前與自己的朋友、情人以及眾多藝術家的書信集,其中涉及貢布羅維奇、維特凱維奇等眾多歐洲藝術大家,是研究舒爾茨藝術生涯及生平活動的珍貴資料
專業推薦
雖然舒爾茨在外省與世隔絕,但他仍能在城市中心舉辦畫展,以及與志趣相投者通信。在他數千封書信中,有約一百五十六封保存下來,他在書信中傾注了他大量的創作精力。
——庫切
布魯諾·舒爾茨的作品最早都是發表在信件上,一封封寄給德博拉·福格爾的信件,這位詩人和哲學博士興奮地閱讀著他的信,並且給予了慷慨的讚美和真誠的鼓勵,布魯諾·舒爾茨終於找到了讀者。
——余華
不容易把他歸入哪個流派。他可以被稱為超現實主義者,象徵主義者,表現主義者,現代主義者……他有時候寫得像卡夫卡,有時候像普魯斯特,而且時常成功地達到他們沒有達到過的深度。
——艾薩克·辛格
一個無與倫比的作家,世界在他的文字中完成偉大的變形。
——約翰·厄普代克
波蘭書信藝術的最後接觸代表
——耶日·菲科夫斯基
他的每一頁紙上都有生活在爆發。
——大衛·格羅斯曼
圖書目錄
尋找布魯諾·舒爾茨(代序)
第一輯 To他們
致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
致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納齊·維特凱維奇
致斯泰凡·舒曼
致阿爾諾爾德·斯帕艾塔
致安哲伊·普萊西涅維奇
致澤農·瓦希涅夫斯基
致馬里安·雅琪莫維奇
致塔戴烏什·沃伊切霍夫斯基
致塔戴烏什和佐菲婭·布萊扎夫婦
致卡奇米日·特魯哈諾夫斯基
致米耶契斯瓦夫·格雷澤夫斯基
致喬治·羅散貝爾格
致《信號》編輯部
致宗教部等
第二輯 To她們
致羅曼娜·哈爾派爾恩
致阿尼婭·普沃茨基耶爾
第三輯 To他
羅塔·沃蓋爾致舒爾茨
威廉·舒爾茨致布魯諾·舒爾茨
附錄
譯後記
布魯諾·舒爾茨年表
後記
譯後記
我從2010年開始翻譯舒爾茨的書信集。這個想法還是因為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由楊向榮先生從英文翻譯的《鱷魚街》促成的。我本人是學習波蘭文的,在華沙大學進修期間,就曾有願望將這位與卡夫卡齊名,但尚不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作家的作品翻譯成中文。但因為種種原因未能著手翻譯他的作品。當我得知他的作品從英文翻譯成中文後,很是高興,舒爾茨的作品終於在中國問世了。在參加《鱷魚街》的推介會上,結識了這本書的編輯瓦當先生,在他的熱情鼓勵之下,我決定翻譯舒爾茨的書信集,以饗中國讀者。
舒爾茨的這部書信集是在波蘭1975年第一次出版的舒爾茨書信集的基礎上補充整理的第二部書信集,其中有一部分書信在第一次出版時尚未收集到,其中包括舒爾茨朋友們致舒爾茨的書信,這對研究和熱愛舒爾茨的專家和讀者們是一大幸事。
舒爾茨在世的時候,他非常珍惜與朋友們的書信來往,細心地收藏著這些書信,但不知何緣故,他的大部分書信至今令人難以想像地不知去向。但慶幸的是,這部書信集中收集到的信件還能留存至今,這無疑是彌足珍貴的資料,同時也是對希特勒法西斯對人類進行殘酷屠殺後的一個象徵性的紀念。波蘭研究舒爾茨的著名學者耶日·費措夫斯基教授曾在書信集的前言中寫道:“我十分有幸能在六十年的研究和尋找過程中找到這些殘存下來的舒爾茨書信,我認為這不是一些簡單的書信,這首先是作家生平的一部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由於作家過早離世,時間抹去了很多記憶,特別是大多數證人也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因此這部書信集就顯得更加珍貴。這些書信的發現和存留,儘管記錄的只是一些零碎記憶,但這些都給研究和熱愛舒爾茨的人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資料,因為大家知道,就連作家本人的出生日期都有不同的版本。
這部書信集的書信共分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舒爾茨給朋友們寫的私人信件和他給“官方機構”——教育部等部門寫的信件;另一部分是朋友致舒爾茨的信件。此部書信集有幸收集到舒爾茨自1937年至1939年與當時已經成名的波蘭作家貢布羅維奇、維特凱維奇等人的書信,這都是“二戰”結束後在作家住房閣樓上存留的信件。
作家給“官方機構”的信件中我們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東西,譬如舒爾茨請求申請休假的信或者請求幫助的信件,但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舒爾茨生活的一方面,可以了解到作家當時生活窘迫,常常遇到不順心的事情,遇到掙錢養家餬口與創作矛盾等諸多不便;每天的日常工作占據了他的大部分時間,這極大地影響了他的創作,使他內心矛盾重重,致使他患上了嚴重的抑鬱症。這一切都嚴重地折磨著他的內心,因為他不能適應他周圍世界的各種條條框框,內心十分無助,但這些都來源於他對藝術創作的極端熱愛和嚮往。就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想到的首先是拯救自己的作品,而不是生命。
如果沒有戰爭和人類大屠殺,如果舒爾茨沒有被暗殺,那他留給我們的書信集就不會是今天這樣一部殘缺不齊的書信集,那將會是厚厚的、多部頭的書信集,當然舒爾茨留給我們的傑作也就會更多,更豐富。
我覺得,如果舒爾茨的所有書信都能留存到今天,那將不僅是書信集,而應該成為他的文學著作,從舒爾茨給羅曼娜的信中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寫道:“很遺憾,我們相識得晚了一些。以前我能寫非常美妙的書信。我的《肉桂鋪子》創作就來自於我的書信往來。”他在給普萊西涅維奇的信中也曾寫道:“我曾經非常願意寫信,那是我那個時候的唯一創作。遺憾的是,我無法回到那個時候的書信往來的狀態。因為現在我已經不會那樣寫信了。”
1892年7月12日深夜布魯諾·舒爾茨誕生在那時還屬於波蘭領土的德羅霍貝奇的一個猶太商人家庭。那時的德羅霍貝奇是波蘭小波蘭省東部地區的一個小鎮。他是父母所生的第三個兒子,也是家中最小的一個孩子。在他的孩童時代也就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年代,正是德羅霍貝奇工業開始迅速發展的年代。這個小鎮的人口很快發展到幾十萬人,成了石油工業的中心。
他自出生那天起,身體就一直多病贏弱。媽媽對他呵護有加,因為媽媽注意到自己的這個小兒子過於敏感、羞澀、膽怯,如果沒有媽媽跟著他,他連自家的陽台都不敢去,他從不願意與自己同齡的孩子玩耍,他孤僻,喜歡獨處。一個人待在家裡時,他寧願去打秋天在窗戶玻璃上飛來飛去的蒼蠅,並用糖去餵養它們。
1902年他開始在德羅霍貝奇的皇家學校學習。因為他孤僻,他無法與同齡人相處。他對周圍的同學都不信任,同時身體也不如同齡的孩子們健壯。但在學校他是一個優等生,學習總是名列前茅。同學們都很嫉妒他,但老師們很快發現這是一個不同尋常……
今天舒爾茨書信集能夠在作家逝世七十餘年之後得以出版,對研究和熱愛舒爾茨的中國專家和讀者來說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大事,今天我為能有機會把舒爾茨書信集介紹給我國的讀者感到無比榮幸。
烏蘭
2013年6月于波蘭格但斯克
序言
找布魯諾·舒爾茨(代序)
瓦當
I他們
1976年11月的一天,菲利普-羅斯來到艾薩克.辛格在曼哈頓的寓所,向他打聽一個人。“也許我不該說出來,”辛格有些猶豫,“他比卡夫卡棒,因為在他的一些故事中,表現出更高的水平”。
十幾年後,同樣在紐約,在另外一場談話中,達尼洛.基什激動地告訴厄普代克:“舒爾茨是我的上帝。”而後者同樣是舒爾茨的冬粉,他認為:“世界在舒爾茨的筆下完成了偉大的變形。”
就像黑暗中興起的一支秘密教派,信徒的隊伍在迂迴中發展壯大:哈羅德’布魯姆、庫切、辛西婭·歐芝克、大衛.格羅斯曼、余華……冬粉陣營強大到令人咋舌。
據拉塞爾’布朗在《神話與源流》(1991)一書中爆料:當年,詹姆斯’喬伊斯為了讀懂舒爾茨,曾經一度想學習波蘭語。可是,波蘭語哪是那么好學的?它是世界上公認的最複雜的語言之一。比如,它有五種性別結構,七種變格……
辛格對這個比自己整整大一輪的猶太老鄉用波蘭語寫作多有不滿,因為那意味著被同化。他自己堅持用意地緒語——一種瀕臨消亡的古老的猶太語言寫作。“他們不懂意第緒語,我們不懂波蘭語。”辛格說。他強調自己“講任何語言都帶有口音”,菲利普·羅斯則安慰他說:“你講意第緒語沒有口音,因為我修過意第緒語。”
一個用漢語寫作的中國人,不太容易理解這些意味著什麼。這種民族、宗教、語言的超級複雜生態,會孕育出怎樣一顆斑駁的靈魂?面對舒爾茨不可思議的寫作,中國作家余華給出了一種解釋:“猶太民族隱藏著某些難以言傳的品質,只有他們自己可以去議論。”
在20世紀的世界文學史中,卡夫卡和普魯斯特的地位有如神祗。今天當讀者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同兩位神祗並排擺放在一起時,第一反應只能是:怎么可能?特別是,當這個人被認為“輕而易舉地達到了普魯斯特和卡夫卡未曾達到的深度”時,讀者的反應已經不僅僅是懷疑,而是茫然和不知所以。然而在舒爾茨的冬粉們眼裡,這有什麼呢?
舒爾茨在藝術圈裡的影響,絲毫不遜於文學圈。他迥異於常人的精神思維與絢爛奇崛的極致風格,向來深獲先鋒藝術家們的鐘愛,取材於其作品的電影、舞劇、音樂劇屢見不鮮。甚至早在舒爾茨的小說中譯本問世前兩年,以色列現代舞團已經來中國演出了他們的經典舞劇《大買賣》。這部舞劇其實就取材於布魯諾·舒爾茨的《肉桂鋪子》、《鱷魚街》、《盛季之夜》等小說。
遠在1973年,波蘭大導演沃伊采克·哈斯拍攝了超現實主義影片《沙漏療養院》,並獲得了當年的坎城電影節評審會大獎。這部取自舒爾茨同名小說的電影,將舒爾茨很多小說里的內容及其本人的生平經歷融為一體。
英國的奎氏兄弟後來受舒爾茨作品的啟發,拍出了被譽為“史上最偉大的十部卡通片”之一的《鱷魚街》。奎氏兄弟發表了如下的“獲獎感言”:
“當我們讀著他(舒爾茨)的作品時,我們感到那就是我們希望自己的動畫所能走的發展方向……舒爾茨釋放了我們的想法。他是一位有震撼力的作家,我們甚至可以以餘生不斷地圍繞著他的作品進行嘗試和提煉,去理解他的精神宇宙。”
去年冬天的某個夜晚,我在歐盟北京影展活動開幕式上看到一部瑞典電影:《校園規則》。裡面有個看上去落拓不羈的老師在給學生上生物課,為了便於學生理解他講的內容,他比畫著一些鳥類標本說:“就像布魯諾·舒爾茨的小說里寫的那樣……”
哈!我忍不住叫出聲來,像黑暗中認出自己的同志。
II布魯諾·舒爾茨的奇觀 這是一個幾乎無法用語言複述的世界,一個此前從未有人展現過的奇觀。
這裡時空錯落扭曲,幻象層出不窮,處處流淌著隱喻與夢魘,神秘、幽暗、怪誕、栩栩如生、富麗堂皇、驕奢靡逸、匪夷所思……這裡是單純與繁複的迷宮,詭異與天真的花園,夢想與神話的源泉,充滿了數學的精準和音樂的律動,步步為營的詩意美不勝收.令人窒息。舒爾茨筆下的世界根植於人類潛意識深處,根植於原始的尚未成形的宇宙,因此充滿流動不居的無限可能——“每一頁紙上都有生活在爆發”(大衛-格羅斯曼語)。同時,這個世界凝結了難以啟齒的辛澀與羞恥,使卑微之物發出閃光,向著平庸、固化、死寂的現實和歷史開戰。這個世界可以感知,卻無從捕捉。當它如巨大的星團朝我們豁然敞開時,我們感到由衷的眩暈、驚奇,卻不知如何命名和處置。在偉大而縝密的美面前,讀者不得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挪動著腳步,宛如回到了懵懂而滿懷憧憬的童年。是的,只有回到人類童年,才能深入這個魔鏡與萬花筒的世界。
人們習慣於把舒爾茨和卡夫卡相提並論,然而事實上,除了猶太人的身份,除了生辰星座(舒爾茨和卡夫卡同為巨蟹座),除了貌合神離的變形術,除了對待婚姻的態度(訂婚又解約),兩個人的寫作並無多少相似之處,或者說他們只是表面相像。對此,傳記作家傑西·費科斯基的評價頗為精到,他說:“舒爾茨是一個本體收容所的建築者,不可思議地使世界的味道變得強烈;卡夫卡是一種穴居動物,使世界的恐怖增殖……舒爾茨是神話的創造者和統治者,卡夫卡是專制世界的西西弗斯式的探索者。”與卡夫卡相比,舒爾茨像是來自更加偏僻、陌生的某個星球。我們現有的文學經驗無法盛放下舒爾茨的寫作,他旁逸斜出,自成一番天地。他甚至置敘述、結構、故事等小說的基本要素於不顧,單純靠描述奇蹟,便成功地抵達了人們看不到的化外之境。
布魯諾·舒爾茨讓我想到最多的不是卡夫卡,而是費爾南多‘佩索阿、埃舍爾、克里姆特,個別篇章還會讓我想到克爾凱郭爾,甚至萬比洛夫。當然,他跟哪個都不一樣。至於他華美絢爛又極富生長力的語言,以及比喻和想像的豐富盛大、無微不至,筆者恐怕此前只在佛經和《古蘭經》里似曾相識。
在認真閱讀了布魯諾·舒爾茨的全部中譯小說至少五遍之後,我心悅誠服地接受了艾薩克·辛格的判斷:“不好把他歸人哪個流派,他可以被稱為超現實主義者、象徵主義者、表現主義者、現創世的熱情,甚至常常置敘述於不顧,大段大段地闡述宇宙、星空的複雜變化和運行原理。同時,也繼承了父親對女性的膜拜和恐懼。
在舒爾茨關於父親的敘述中,星星點點散落著催人淚下的溫情。年幼的他喜歡站在父親兩腿之間,“抱緊它們像抱緊石柱”,看父親寫信,和父親散步,被父親夾在胳膊下面行走,受父親支使回家取東西……這些平淡無奇的生活細節都變成充滿詩意的回憶。
1915年6月,69歲的雅各布去世了,撫養家人的責任落到了舒爾茨的身上,這其中還包括他寡居的姐姐及她的兩個孩子。父親的死,給舒爾茨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傷痛。在小說《沙漏療養院》中,他將身患重病的父親送往一座用沙漏做招牌的療養院,依靠將時間撥回去維持生命。“你父親的死亡,在家鄉已經擊倒他的死亡,在這裡還沒有發生呢。”舒爾茨的愛使父親得以永生。
在舒爾茨的小說里,父親一次又一次地變形,變成鳥、蟑螂、螃蟹,最終消失得乾乾淨淨。“他遙遠得仿佛已經不是人類,不再真實。他一截一截地、自覺地從我們當中脫身而去,一點一點地擺脫了與人類集體聯繫的紐帶”,“父親既然從來沒在任何一個女人心裡紮下根來,他就不可能同任何現實打成一片”。在不斷消失的“父親”身上,隱含著猶太人在現世中無法安身的處境。也正是基於此,我對他那部謎一般的《彌賽亞》充滿近乎恐懼的好奇,通過書名我猜測並期待裡面有著歷史和神話、現實與預言的完美匯合。
就這樣,當卡夫卡掙扎於父親的絕對威權之下時,舒爾茨創造出了世界文學中最柔軟最有活力也最迷人的一個父親。這是只屬於他一個人的父親,沒有誰敢分享。Vl死亡變形記
在被迫搬人猶太隔離區之前,布魯諾·舒爾茨曾將自己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彌賽亞》的手稿以及數以百計的畫作,託付給外面的一些朋友代為保存。他們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然而這些作品從此如石沉大海,再也沒有露面。
舒爾茨死後不久,一個名叫傑西·費科斯基的波蘭文學青年讀到了他的作品,大為震驚。此後,他以發瘋般的熱情來研究和介紹布魯諾的作品,成為一名“舒爾茨編年史家和考古學家”。半個世紀以來,費科斯基孜孜不倦地尋找挖掘有關舒爾茨的資料,特別是《彌賽亞》的下落。他追蹤每一個在舒爾茨生活中可能出現過的人,不放棄任何細微的線索,但最終只收集到舒爾茨的大約一百封書信,而《彌賽亞》依然只是一個傳說。
2002年《紐約客》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這個“文學偵探”所遇見的“間諜小說”般的情節:
1987年,一個名叫亞歷克·舒爾茨的人,自稱是作家的堂弟,聯繫費科斯基說,一名來自利沃夫的男子,可能是一名外交官或克格勃軍官,曾經表示願意賣給他一包重兩千克的舒爾茨的手稿和畫作。費科斯基馬上同意去確認資料的真偽,然而幾個月後,亞歷克·舒爾茨死於腦溢血,沒有告訴費科斯基如何聯繫那個在利沃夫的神秘男子。幾年後,費科斯基偶然遇到瑞典駐華沙大使,這位大使告訴他,一個“滿滿的包裹”被藏在克格勃的檔案里,裡面裝著舒爾茨的手稿,“《彌賽亞》就放在最上面。”大使是從一個偶然見到那個包裹的“俄國人”那裡聽說這個情況的,它放在一個不知名的波蘭人資料里,那大概就是舒爾茨託付作品的其中一個人。他讓費科斯基陪他到烏克蘭去尋找它,但烏克蘭當局兩次拒絕了這位大使的入境申請,他也在尋找能夠完成前去世了。
更多人加入到偵探的行列中。1987年,辛西婭·歐芝克在《斯德哥爾摩的彌撒》中描寫了一個大屠殺遺留的孤兒.因狂愛舒爾茨,固執地認為自己是舒爾茨的兒子,過著極其荒誕的生活。而以色列作家格羅斯曼在長篇小說《證之於:愛》里直接讓舒爾茨躲過了大屠殺,成為一種“類人魚”,在大海里縱情環遊。
只有一次,舒爾茨真的露出了他神秘的微笑。2001年,一個來自以色列的攝製組在德羅霍貝奇無意間發現了舒爾茨為藍蹈畫的兒童房壁畫,烏克蘭政府當即宣布其為國寶。沒成想,那幾名以色列人將數片壁畫殘片偷偷帶了出去,存放在了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其中的一幅名為“魔鬼”。於是,由此引發了波蘭、烏克蘭、以色列等國家的一場糾紛。
就像他筆下層出不窮的變形與消失的人和物一樣,布魯諾·舒爾茨用自己的生命上演了一出關於消失、變形和死亡的黑暗魔術。落地的種子不死,憑藉永不枯竭的詩意,他已成為死灰復燃的神話和寓言。
2010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