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張一弓[中國內地作家]](/img/4/b6a/wZwpmL4IDM3cDM3EzN0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xczL2M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張一弓[中國內地作家]
張一弓[中國內地作家]男,歷任理論處處長、革委會副主任兼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河南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登封縣文化館副館長,河南省文聯創作員,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文學創作一級。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南省第七屆政協委員。1934年12月生於河南開封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祖籍河南新野縣。中共黨員。1950年於開封高中二年級肄業,相繼在《河南大眾報》、《河南日報》任記者、編輯近三十年,後到登封縣基層工作三年。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五十年代開始小說創作,因短篇小說《母親》受批判而輟筆二十年。198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80年後重新發表作品,《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兒和她的小嘎斯》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流星在尋找失去的軌跡》獲《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相》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還著有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1982年加入中國作協,河南省文聯專業作家。
創作簡況
 《飄逝的歲月》
《飄逝的歲月》 《遠去的驛站》
《遠去的驛站》著有小說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一弓代表作》、《張一弓小說自選集》、《流淚的紅蠟燭》、《死戀》、《火神》、《死戀》、《野美人與黑蝴蝶》、《死吻》等12部,長篇報告文學《正大集團創業史》,紀實散文集《飄逝的歲月》等。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將於近日出版。
獲獎作品
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獲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一等獎,中篇小說《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兒和她的小嘎斯》分別獲全國第二、三屆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相》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集《張一弓集》獲全國第一屆優秀圖書獎。
茅盾文學獎入圍作品
《遠去的驛站》張一弓從一個孩童的經歷和視角,寫出了戰火紛飛的年代裡,“我”的大舅、父親以及姨夫為核心的三個家族所發生的一系列故事。書中有四十多個人物相繼出場,沒有太複雜的關係,也沒有過多纏綿的感情糾葛,只是在大舅的衝動中,在父親的執著中,在姨夫的堅持中,面對敵人,面對情人,面對手足而產生的諸多心靈上的撞擊。作者把人物思想、情感的衝突,心靈的對話描繪得生動感人。
成長經歷
 張一弓
張一弓張一弓,一級作家,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1935年生,祖籍南陽新野縣。父親張長弓原是河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母親是一位高中語文教師,少年時代就受到家庭薰陶,對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1950年,他在開封高中讀二年級時,寫了一首敘事詩,獲得全校文藝比賽第一名。後到《河南大眾報》和《河南日報》任記者、編輯長達30年。1956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秋至1960年,因寫短篇小說《母親》受錯誤批判而輟筆20年。1980年後重新發表作品。先後發表中、短篇小說多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和她的小戛斯》分別獲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有多部小說被搬上電影銀幕。《黑娃照相》獲1981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已出版的中篇、短篇小說集有《張鐵匠的羅曼史》、《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火神》、《流淚的紅蠟燭》、《死吻》、《死戀》、《張一弓中短篇小說集》、《野美人與黑蝴蝶》等。《流星在尋找失去的軌道》、《伏爾加轎車停在縣委大院裡》、《火神》都頗引人矚目。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南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張一弓稱自己是“同時代人的秘書”。深入反思農村歷史道路的曲折,熱情擁抱變革時期的農村現實,努力追蹤農村的變革步伐,使他的小說成為充滿熱情和理想的現實主義創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他的創作轉向對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與尋找等問題的揭示。他偏愛生活中的特異事件,擅長通過戲劇化的手段,造成小說情節的跌宕起伏。舒捲自如的情節結構、在激烈的矛盾衝突中塑造帶有英雄氣質和傳奇色彩的人物、強烈的政治色彩與充沛的文學激情、雄渾悲壯的風格與滑稽幽默的筆調相結合、歐化的敘述語言與充滿鄉土氣的人物語言相融匯,使他的小說具有獨特的魅力。
創作歷程
他不是文壇上炙手可熱的作家,但是他的沉默和潛心寫作,卻總能令人刮目相看。即使時隔多年,他的作品依然能被人們常常提起,甚至流傳海外。2007年,《遠去的驛站》被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到“中國當代名家長篇小說代表作叢書 ”,而加拿大漢學家、維多利亞大學教授理察·金把《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翻譯為英文發表。這時,距離這篇小說的首次發表已經有27年。 驛站上的漂泊者
年過七旬的張一弓,電話里的聲音清晰然而緩慢,他得了嚴重的肺氣腫,呼吸量僅是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右眼又近乎失明。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沒有放棄寫作,仍然為了疾病妨礙了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進程而著急。張一弓說,自己對河南總覺得少了一些歸屬感,說得高雅一點,好像是靈魂的漂泊者。他的老家是三國時代劉備曾經當了幾年縣令的新野縣,但在父親那一代離開了鄉土,故鄉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記憶,也沒有留下屬於他的一座老屋、一棵老樹或是一道低矮的籬笆牆。他出生在開封,並在那裡生活多年,卻只是在那個古城的小巷裡不斷變換住址的房客,這裡也沒有屬於他的“宅基地”。有的作家寫故事,家鄉的一個村莊都寫不完,而張一弓呢,他的童年留下的只是人生驛站不斷飄逝的風景。從抗日戰爭開始,他就跟著在河南大學任教的父親到處流亡,光是國小就換了十多所,沒有溫馨的、穩定的供他回憶的老屋,這是他生命的特點。
張一弓的父親在大學裡教文學,母親是教高中國文的老師,耳濡目染,張一弓自幼受到文學的薰陶,上國小5年級的時候,他就看《聊齋》、魯迅的《吶喊》等經典著作了。10歲那年,他們逃亡到陝西寶雞的一個農村,有一段時間沒學上,張一弓就把童年生活寫成了一篇篇的紀事體散文,他照著父親書架上的書,自己設計了封面,寫上《斑斑文集》(斑斑是他的小名),並在封底註上“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父母看了他的“處女作”就笑了。直到現在,張一弓還清楚地記得,這個“文集”中有一篇是描寫說大鼓書的女藝人怎樣在財主家的婚禮上說唱,自己參加的是募捐隊,為宣傳抗日把她趕下台,女藝人哭著把自己賺的零錢都放在他的募捐袋裡,說:“我弟弟也在前方打老日呢!”那個時期,他描寫的兒童生活已融入民族的命運,只是他自己並沒有這種認識。張一弓的父親看了後直掉眼淚,他說,斑斑在寫大人的東西,他有一點感傷主義。
這是張一弓創作欲望的第一次表達。
新中國建立後,16歲的高中生張一弓成了年紀最小的記者。記者生涯給他提供了廣闊的人生舞台,不斷流動、不斷變幻的生活場景,使他的故事、他的思考和情感不斷增添著豐富而駁雜的內容。他把自己整整30年的生命交給了新聞事業,從見習記者一級一級地提上去,直到晉升為副總編輯。讓他感到困惑的是,幾乎每次政治鬥爭都使他難逃干係,“反右”有他,“反左”也有他。“這是我精神上沉重的一面。但我並不怨恨,因為還有更多的人比我經歷了更多的磨難。相反,恰巧這一點,是促使我走上文學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把果實掛上冬季的枝頭
被稱為“記者娃娃”的張一弓沒有忘記文學。1956年,他的第一部小說《金寶和銀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後,又有幾篇小說發表在湖北的《長江文藝》、河南的《奔流》、《牡丹》刊物上。其中短篇小說《母親》,被定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毒草”,一篇短篇小說招來了20多篇批判文章。張一弓一下子沉默了20年,文學成了天上的月亮。“文革”結束後,他又因“文革”後期擔任了報社的領導職務而受到審查批判,調離新聞工作,被下放到嵩山腳下的登封農村。正是在他下放之前“靠邊站”的時候,他又暗自寫起了小說。1980年1月,《收穫》發表了他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發表之前,《收穫》沒有人知道他是何許人,按照當時的慣例,向作者所在地調查作者情況,徵求意見。主管部門領導認為作者有“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卻又兩次打電話,堅持不同意發表他的作品。是時任《收穫》主編的巴金拍板決定發表了它。在全國首屆優秀中篇小說評獎期間,初評小組一致推舉《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進入得獎名單,又再次收到來自河南有關部門的反對意見。文學評論家閻綱在《悼犯人李銅鐘》(見《隨筆》2001年第3期)中寫道:“評選委員會不得不向評審會主任巴金實情稟報並請示下。巴老不但同意該作得獎,而且力主列為一等獎中打頭的一個。”在評獎二十年以後,張一弓讀了這篇文章,才知道了巴金對他的又一個巨大的支持,他說:“我感謝很多在寫作上支持過我的同志,尤其感激巴金,他是一座大山,扶植並庇護了一棵小草。他使我再次與文學結緣了。”
1983年秋天,當張一弓作為農村的業餘作者,已經獲得3次全國性文學獎項之後,才從農村被調回城市,到河南省文聯文學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他在“不惑之年”以後重操中斷了20餘年的文學“舊業”,一鳴驚人,以中篇小說的形式連續不斷地向文壇發起“衝擊”,以其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和直面歷史的勇氣,以其強大的思想道德力度,唱起蒼涼悲壯的英雄之歌。他以《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連續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像》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進入新世紀以來,他年過花甲之後所寫的長篇小說《遠去的驛站》,又獲中宣部頌發的“五個一工程”的優秀作品獎和新聞出版總署頌發的第六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張一弓並沒有因為屢獲大獎而得意忘形,相反,他卻從中感覺到了蒼涼,他說:“在文學創作上,我是一棵錯過了生長季節的老樹,到了生命的夏季才拚著命抽條長個兒,而試圖把原本屬於夏季和秋季的果實掛上冬季的枝頭。這樣的生命體驗感受是悲劇性的。”
把河南的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
雖然有著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張一弓的作品中卻絲毫看不出任何屬於他個人的委屈和怨尤。他說:“寫作必須具有對人間苦難的悲憫之心。我十分注意不要讓個人恩怨進入文學,不要用‘小我’褻瀆文學,不要為僅僅屬於自己的傷疼發出刺耳的尖叫,我怕那樣我就會不公正,就會使作家應有的悲憫之心和道德力量受到損害。作家如果沒有悲憫之心就不要寫東西。不同的作家最後所要競爭的,不是寫作技巧,而是人格力量、道德力量。我常常這樣勉勵自己。”張一弓認為,作家的創作雖然要表現“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鳴,否則讀者沒有理由看你的作品。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張一弓才能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個人經歷的挫折中掙脫出來,深切關注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寫了30多篇、150多萬字的表現河南農村生活的中、短篇小說。評論家認為,張一弓與河南其他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共同點是,關注農民的命運,具有濃郁的河南農村的鄉土氣息。但也看到了張一弓與河南其他作家的不同,雖然他所寫人物的語言特色和行為方式,都屬於地道的河南農村,但他的作品的敘述語言和結構方式卻是屬於城市知識分子的,甚至有歐化的成分,同時也從這種“不同”中看到一個屬於城市知識階層的作者,對農民懷有的深厚情感和悲憫之心,為他們擺脫苦難的掙扎送去沉重的吶喊或含淚的祝福。張一弓承認,他受到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法國浪漫主義文學的深刻影響,但他並不擔心這會妨礙他的作品的河南特色。他十分重視而且非常喜歡在河南這塊土地上的深厚、悠久的歷史文化積澱。在《遠去的驛站》中,他寫了父親、大舅和姨父三個知識分子及其各自的家族。在他們的家族史中充分融入了發生在河南的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書中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章節的標題:《胡同里的開封》、《姥爺家的杞國》、《試論劉秀稱帝與老張家桑園之關係》、《關帝廟上的星星》,都打著真正的“河南”的烙印。還有大舅家族憂國憂民的“杞人情懷”,父親畢其一生都在尋找的南陽大調古曲《劈破玉》,已經把地域文化融入人物的生命。另外,還採用了很多愛恨情仇的傳說,也都儘可能地保持了傳說地域的原始狀態。張一弓認為,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如此豐厚的地域文化,是任何其他國家的作家都做不到的。
奇聞軼事
一根羊肉串引出一部長篇小說
 《遠去的驛站》
《遠去的驛站》《遠去的驛站》是張一弓用10年時間精心打磨的長篇小說,小說以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交匯之地為背景,以三大家族近百年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宗教、婚戀和情愛關係為主線,去描述家族的興衰和矛盾衝突,凸現出一個時代的民族生存史,展現出中國近百年的變遷。
在張一弓的構思中,這部活躍著40多個人物、貫穿百年歷史的《遠去的驛站》打算是要分三部長篇來寫的,但是,冗長的文字和複雜的結構是否會給讀者帶來閱讀的障礙?張一弓在困惑中徘徊。一日,他在街邊的小攤上吃羊肉串,羊肉串的“結構”讓他眼前豁然一亮。於是,一種新的敘事方法在張一弓筆下行雲流水般飛瀉而出——他用第一人稱“我”的經歷和視覺,把三個家族內外的各種人物串連起來,“我”在其中的位置好像是羊肉串的那根棍兒。
一個傳奇、浪漫、詩意的故事帶著濃濃的鄉土氣息撲面而來,它以古都開封為軸心,畫出了一個家族壯闊的命運。在一種複雜的敘述語調中,個人記憶如一盞燈,迅速掠過密集的事物,讓人們震驚地感受人類活動無限的多樣性。
因為“母親”被批而沉默20年
張一弓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是河大教授,母親是中學教師,家庭的薰陶培養了他的文學天賦。他說:“如果我生在一個屠夫的家庭,10歲時我學會的應該是殺豬。”
1956年,21歲的張一弓在洛陽《牡丹》雜誌上發表了短篇小說《母親》,這為他後來苦難的命運埋下了伏筆。當時他的母親剛被打成右派,他這篇文章被批為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大毒草”。口誅筆伐接連而至,一篇短篇小說竟招來了28篇批判文章。從此後,嶄露頭角的張一弓從文壇上消失了,這一沉默就是漫漫20年。
張一弓陷入了回憶之痛,他哽咽著說:“我的一生就像拳擊手一樣,我不是重量級選手,當命運要將我打倒時,我沒能力打倒它或者是不被它打倒,我只能是——被打倒了,在讀秒時——一、二、三……能及時跳起來,在艱難的歲月里靠精神活下去……”
巴金衝破阻力讓他的小說獲獎
1980年,張一弓復出文壇,以一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榮獲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這篇小說被譽為“開社會主義悲劇之先河”的佳作,張一弓從此走上了文壇。談起這部作品,張一弓向記者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是巴金先生衝破阻力給了他這個至高榮譽。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是張一弓1979年年底投給《收穫》雜誌的稿件,被編輯選中推薦給了主編巴金先生,巴金非常喜歡。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寫信揭張一弓的“老底”,認為這部小說不能發表。巴金力排眾議,不但將該小說發表在《收穫》上,而且還力薦其獲得了“首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這些內幕張一弓並不知情,事隔22年之後,去年在上海舉行的巴金99華誕聚會上,作家閻綱透露了這一細節。張一弓聽到這個訊息後,心中驚訝且感動,他說:“沒想到一位文學大師,竟暗暗地保護著我這樣的小草。”
創辦《熱風》10萬元買了一個教訓
1992年,張一弓被任命為省作協主席,那時作協沒幾個人,不管作家又沒刊物,一年經費9000元。張一弓對一個企業家朋友說:給我把米,讓我餵只文學的雞,給我們下點兒文學的蛋。
朋友給了他10萬元錢,他創辦了《熱風》雜誌。真沒想到這隻雞這么不好喂,稿費、工資、印刷費和房租都找張一弓算賬,為此,張一弓拉下臉向企業家們鞠躬拉贊助,但最終還是無力支撐下去了,只好改版。張一弓說,這次辦刊經歷讓他體驗了一次生活,買了一個教訓。
一部小說改編費只有600元
張一弓的家十分簡陋,除了幾櫃書以外別無高檔家具。記者忍不住問他:“您那么多小說都被改編成了電影、電視劇,在我想像中您可是個腰纏萬貫的人呀。”張一弓聞聽此言哈哈大笑:“說來你不信,我一部小說的改編費只有區區600元。”
張一弓的小說《張鐵匠的羅曼史》、《流淚的紅蠟燭》、《山村理髮店紀事》等已被改編成了近10部電影或電視劇。那時候張一弓的著作權意識差,有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都放映兩年了他才知道,他拿到的改編費很少,最多的一次也只有600元。
後來,張一弓應邀到美國訪問,別人都以為他是個富翁,問起他的收入,他總是笑著說:“男士的錢包和女人的年齡一樣是個秘密。”別人讓他到酒店請客,張一弓怕“露餡”,自己買菜給他們做了一桌飯菜。
對於別人的侵權,張一弓總是淡然一笑:“我們這代人有自己固執的價值觀,自己的作品被偷偷改編,如同自己的孩子被別人抱走,心裡當然很不是滋味,但自己的作品能夠被認同,我感到這是一種幸福。”
一個人靜享生活的孤獨
“我是一個孤獨的人,10年來我已經漸漸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面對記者的提問,張一弓緩緩地說。他說,這是第一次在記者面前談起自己的家庭和婚姻。
10年前,張一弓和愛人平靜地分手,從此就再也沒有走進“圍城”之中。說起那段婚姻,張一弓說:“這不存在誰對誰錯的問題,我的婚姻好像是把第一個扣子扣在了第三個扣眼上,也許是命運的捉弄,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我們彼此理解地分開了。”
“緣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我從來不會去刻意追求它。所以我寧願去享受這種孤獨,它能使我心無旁騖地去寫作……”
張一弓告訴記者,他對兩個兒子管教不多,他們從小到大從來沒有沾過自己的一點光。兩個兒子自食其力,開了一個小超市,目前都還沒有成家。大女兒考上博士以後在解放軍藝術學院任文學教授,二女兒在一家公司上班。兒女們經常和他電話聯繫,有時會給他送純淨水或買些東西,但更多的時候,他總是把自己關在屋裡,守在筆記本電腦旁敲打著,敲打著日復一日的孤獨與寂寞。
他辭去了一些應酬,謝絕了採訪,“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他過著隱士般的生活。
這時,張一弓接了一個電話,是長江文藝出版社打來的,說10萬元獎金馬上就要兌現,扣除稅費,還有8萬元是屬於他的。
張一弓說,這次獲獎給了他繼續寫作的勇氣。他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30年獻給了新聞,而現在,他想重新開始,“作為一棵錯過開花結果季節的樹,我只想把秋天以後的時光重新安排,我的青春要從68歲開始……”
談起將來的寫作計畫,張一弓說他正在寫姨父的長篇傳記,依然是一個關於家族的故事,但這個故事更加真實和驚心動魄。目前他已經寫了25萬字,這將是他煥發二次青春的又一力作。
著作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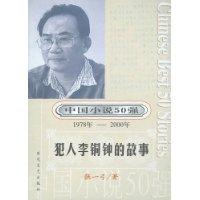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使(中、短篇小說集)1982,百花
流淚的紅蠟燭(中篇小說集)1983,四川人民
火神(中、短篇小說集)1985,花城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篇小說集)1986,中原農民出版社
張一弓集(中篇小說集)1986,海峽
死吻(短篇小說集)1988,長江
張一弓:(1935~ )生於開封。曾長期從事新聞工作。1956年開始發表小說。新時期以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張鐵匠的羅曼史》、《春妞的她的小嘎斯》分獲全國一、二、三屆優秀中篇小說獎,《黑娃照相》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曾任河南省作家協會主席,現為河南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出版有中短篇小說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紀實散文集《飄逝的歲月》,《遠去的驛站》等。 劉思謙:評論家。
著名作家張一弓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今天下午2時59分在省人民醫院逝世,享年81歲。
![張一弓[中國內地作家] 張一弓[中國內地作家]](/img/c/9c2/nBnauM3X3MzM4UjNyczM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3MzLxY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