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背景
譜名運鏜,字任叔,號愚庵,筆名巴人等,浙江奉化區 大堰鎮人。父業農,粗通文墨。任叔8歲上學,13歲參加全縣國小統考,作文名列前茅。
1915年考入大學,五四運動中任寧波學生聯合會秘書。
1920年畢業,先後執教鎮海、鄞縣、慈谿、奉化等地國小。其間,參加奉化進步團體剡社。
 王任叔
王任叔1922年5月始發表散文、詩作、小說,由鄭振鐸介紹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4年10月任《四明日報》編輯,主編副刊《文學》。是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任縣立初級中學教務主任,主編剡社月刊《新奉化》。同年11月,小說《疲憊者》在《小說月報》發表,引起文化界重視。
1926年7月去廣州,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秘書、代科長,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其間常將機密材料向黨組織匯報。
1927年3月任寧波中山公學、第四中學教師,一度負責中共寧波地委宣傳部工作。6月被捕,由莊崧甫保釋。是年,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監獄》出版。
1928年執教上虞春暉中學。翌年1月去日本,研究社會科學與普羅文學,自學日語,翻譯《蘇俄女教師日記》及日本長篇小說《鐵》。10月,日本當局逮捕中國進步留學生和共產黨人,被迫回國。
1929年,在上海參與發起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一度擔任中共曹家渡區委負責人,領導大夏大學黨支部。
1931年4月,第二次被捕,被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與黨組織失去聯繫。
1932年,去武漢執教。翌年1月任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司科員。1935年因《娜拉》案牽連,第三次被捕,鏇由毛思誠等保釋。次年7月在上海參與發起中國文藝家協會,參加營救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活動。
1937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秘書長、《救亡日報》編委。翌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江蘇省委文委委員。8月始以巴人筆名發表文章。是年,與,許廣平、鄭振揮、胡愈之等共同編輯《魯迅全集》,主編《譯報·大家談》、《申報·自由談》、《公論叢書》等。
1939年春任文化中心小組召集人,領導“孤島”上海文藝工作。至次年夏,撰寫、出版《文學讀本》、《邊鼓集》和劇本《前夜》等。
1941年3月,奉命去香港,7月赴新加坡,執教南洋華僑師範,與胡愈之、郁達夫等領導文化界開展反法西斯鬥爭。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任星(新加坡)華戰時工作團宣傳部長。
1942年2月,與雷德容等飄泊到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輾轉先達、棉蘭等地。
1943年,遭侵印尼日軍通緝,隱居原始叢林中泅拉巴耶小村,以刀耕火種自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參加蘇島華僑民主同盟,主編《前進周刊》、印尼文《民主日報》,寫成大型話劇《五祖廟》。
1947年7月,被荷蘭軍隊逮捕,經組織營救獲釋,10月到香港。
 王任叔
王任叔1948年8月,奉命去河北省平山縣,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第三室綜合研究組組長等職。翌年出席全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1950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尼西亞特命全權大使。
1952年1月卸任回國,任外交部黨組成員、政策研究委員會委員。1954年《文學論稿》問世。同年4月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總編輯,1957年任社長兼黨委書記。
1959年康生點名批評巴人,指出巴人和蔣介石是同鄉,且巴人曾在國民黨任職,從而導致巴人作為文學界的代表人物,與史學界的尚鉞,經濟學界孫冶方開始共同受嚴重批判,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剝奪文學創作權利後,他轉向史學研究。
1960年,在“反右傾”運動中受批判,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翌年起,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東南亞研究所編譯室主任。
1966年初完成160萬字史學專著《印度尼西亞歷史》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中遭批鬥、隔離審查。
1966年被抄家,受盡折磨。1968年開始有大字報宣傳巴人是郁達夫被害事件中向日本人告密的叛徒,使得巴人遭到更嚴重的迫害。
1970年3月被遣返家鄉,安置在村西頭的兩間舊茅屋裡,嚴重的摧殘使得他精神崩潰。
1972年7月25日病逝。
1979年6月平反,恢復政治名譽。
政治生涯
 王任叔
王任叔 王任叔
王任叔王任叔,1901年生,浙江省奉化縣人。早年畢業於寧波第四師範,做過幾年國小教師。1925年在奉化中學教書時,在他二哥王仲隅影響下加入共產黨。王任叔博學多才,愛好文學,青年時代已在上海報刊上發表小說雜文等。1926年9月,已當上北伐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親自寫信邀請王任叔去廣州,想利用他的文才,介紹他進北伐軍後方留守處機要科擔任中校代科長。他徵得組織上同意,去了廣州。蔣介石與留守主任李濟深密電來往,都經過機要科。1927年2月間,王任叔發覺蔣介石密謀“清黨”,立刻將訊息告訴尚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同志。他自己在廣州留守處已待不下去了,經組織上同意回到浙江。名義上在寧波第四中學教書,實際擔任黨的地委宣傳科長。“四·一二”事變爆發後,王鯤、楊眉山等同志被捕下獄。一個多月後,在上海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的劊子手楊虎、陳群奉蔣介石密令來寧波“清黨”,到寧波的第二天就從獄中提出共產黨員王鯤和楊眉山砍頭示眾。腥風血雨中,王任叔也被捕了。他堅不吐供,自忖必死無疑,寫下遺書。經浙江省府委員莊崧甫老先生出面營救,王任叔才被保釋。他的二哥王仲隅逃往武漢,幾年後在外鄉病故。王任叔去了上海,潛伏了一段時間後,開始露面。他積極參加左翼文學活動,創作中短篇小說,也寫寫雜文。他還在歐陽山主編的《小說家》任編委,很快成為公認的進步青年作家。他接受過魯迅先生的多次教誨,參加了宋慶齡、蔡元培、林語堂等人主持的“自由大同盟”,他還擔任上海海員總工會黨團委員,是滬上一位活躍人物。他的住所在上海虹口(當時是日本租界區)附近,是田野樹叢間的農家出租屋。不久,由於有人檢舉王任叔參加策劃上海海員的反帝大罷工,租界工部局捕房要抓他,還行文警察局請求配合。王任叔得到好友通風報信,化裝後逃離上海,去武漢的二哥處避風,在武昌的漢江中學當教員。後又經友人介紹去南京的中央交通部當科員,兩年多後才回到上海,以賣文為生。他得知在他離開上海後不久,上海就發生了有名的“東方旅社”事件,不由心中陡生疑雲,他為慘遭敵人屠殺的同志而深感悲痛。同時,他很想弄清這事件的真相。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後,王明(陳紹禹)、李竹聲等留學蘇聯歸國後的青年幹部在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將李立三趕下台,奪取中央領導地位,宣稱“終結了立三路線”,但他們又推行更左的路線,搞什麼“飛行集會”,自我暴露力量,導致許多黨、團員被捕被殺,損失嚴重。王明的路線遭到黨內很多同志的堅決抵制。1932年1月26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歐陽立安等三十六名中高層幹部在上海東方旅社三樓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商討寫信要求第三國際糾正王明路線的錯誤,挽救中國革命,會議絕對保密。不想,會議開到一半時,大批國民黨軍警特務團團包圍了東方旅社,與會者全部被捕。事情發生得極為突然!次日滬上各報頭條均刊發了這驚人的訊息。人們議論紛紛,何孟雄等同志堅貞不屈,沒有一人招供。很快,經蔣介石下令,被捕者中二十三位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圍牆外的荒野。這是一個大血案。後來的中共黨史上都稱這是由於叛徒的出賣。但究竟是哪個叛徒所為,一直說法不一。
 王任叔
王任叔王任叔有個同鄉好友竺正信,是國民党進步人士,他在偽淞滬警備司令部擔任秘書。王任叔回上海後,有次在街頭與竺正信邂逅,在嚴峻的白色恐怖氣氛下,王任叔一點不了解竺的情況,寒暄一番,未深談就分手了。他對“東方旅社”事件感到困惑:國民黨軍警特務究竟是如何獲得確切情報的?左聯的戰友成仿吾、鄭振鐸都曾懷疑這一事件與黨內鬥爭有關,重點懷疑李竹聲和當時化名趙蓉的康生。王任叔在搞創作的同時暗中致力於調查“東方旅社”事件的真相,漸漸地,他將疑點集中於康生身上。康生原名張宗可,山東膠南人,1898年生。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勞動大學擔任過支部書記。“四·一二”以後他轉入地下工作,歷任滬中、閘北、滬西區區委書記,還擔任過江蘇省委委員(當時上海屬於江蘇省)。王任叔與康生只見過幾次面,並不熟。在回上海後,他了解到在王明上台掌權後,康生丟棄了他竭力吹捧過的李立三,效忠於過去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在1931年底當上中央組織部長,抓住不小的實權。康生與李竹聲的關係更是密切,亦步亦趨。他們在黨內推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政策,將不少反對他們意見的黨員幹部送往張國燾掌大權的鄂豫皖蘇區“分配工作”。其實,這是使的“借刀殺人”之計。因為這些同志幾乎都被張國燾加上“改組派”、“反黨中央”等罪名殺害了。王任叔了解到竺正信確實是同情共產黨之後與他恢復交往。一次,竺正信悄悄地告訴他:“東方旅社”事件發生前約三小時,刑偵處長宣鐵吾忽接到一個神秘的告密電話。匿名打電話的人是山東口音,鼻音重,他說有一夥共產黨重要頭目準備在東方旅社三樓開會,要抓他們宜快,宜立即部署行動,並嚴加保密。因為他知道警備司令部內至少潛伏有三名共產黨情報員。起先,宣鐵吾不太相信,但再想想這會不會是對方內出於派系鬥爭或路線鬥爭而意在借刀殺人,誅除異己呢?於是他調集大批軍警特務,迅速採取搜捕行動,果然馬到成功。為此,他受到上司的重獎,還官升一級。王任叔每思考這個問題就心情沉痛而憤慨,他將懷疑集中於康生。1935年6月,他在上海的《大美晚報》上化名“屈軼”發表過雜文《謹防小人》和《對奸人的棒喝》等,著重指出:“小人是無所謂原則也無所謂人格的一種人渣,只要達到目的而不計手段。”“‘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有的同志慘死在敵人屠刀下,實是被自己陣營的同志所暗中出賣,這才是最可悲哀的事。”
王任叔在他的其他雜文中也集中火力抨擊他心目中的陰險歹毒之徒。魯迅先生對他的雜文頗有好評,讚賞他嫉惡如仇的精神。可見魯迅與他的同鄉後輩的心靈是相通的。王任叔卻怎么也沒料到,他對“東方旅社”事件的關注與議論及其一些雜文為二三十年後康生報復他埋下了伏筆。
 王任叔
王任叔 王任叔
王任叔1933年至1935年春,王任叔在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任科員,其間常化名給《南京人報》、《新民報》,上海《大美晚報》、《申報》等報紙的副刊投稿,以寫雜文、隨筆為主,偶或也寫些反映下層民眾悲苦生活的短篇小說,其雜文文風犀利,思想深刻,於平白通俗中透出直面世風人生的戰鬥精神,每每被人們認為出自魯迅之手筆。其實,當時魯迅極少給南京報刊寫稿,蓋因他在上海的寫稿編書任務就已極為繁重,除應付多方約稿還得打筆戰。王任叔於1935年秋重返上海,常為《申報》副刊《自由談》寫稿,仍以雜文為主,幾次有幸見到魯迅並親聆其教誨。上海匯聚了以馮雪峰、王魯彥、曹聚仁、王任叔等人為主體的浙江作家群。他們都追隨魯迅或與這位已患重病、形神憔悴的大文豪保持互為信任的關係。1936年初,“左聯”解散。同年6月,王任叔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從事抗日活動和寫作,先後編輯《每日譯報》、《譯報周刊》、《譯報副刊》“大家談”和《申報》副刊“自由談”,並與許廣平共同主持《魯迅全集》編輯工作,是留在租界“孤島”內堅持鬥爭的卓具膽識的進步文藝家。那時上海已淪陷,但驕橫兇惡的日寇的鐵蹄還未踏入租界,他們主要靠浪人流氓和漢奸在租界內開展種種破壞活動,受到抗日力量的堅決反擊,雙方鬥爭從未停止過。王任叔那時還擔任江蘇省(舊時上海歸江蘇管轄,為特別市)文委委員,在租界裡為抗日救亡做了很多工作,茲不贅述。那時就在進步文化界內部也出現過分歧和論爭。如在魯迅逝世三周年之際,原太陽社主將阿英(錢杏邨)在他主編的《譯報》“大家談”副刊發表了紀念文章《超越魯迅》,大意謂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是民族抗日統一戰線的時代,我們不應停留在模仿魯迅風格的雜文的階段,一定要超越魯迅,要戰鬥的,不要諷刺,要明快的、直接的……總之,是要創造,不要模仿。當時王任叔正兼職主編《申報》“自由談”副刊,他立即撰文反擊,對熟人老友阿英的觀點逐一駁斥,連寫六篇文章,廣受關注。這令阿英很有些下不了台,他發現滬上文化人士中很多人支持王任叔,就連從江陰家鄉到上海一家照相館學徒的上官雲珠(後來很快成為滬上電影女明星,她一向愛好文學寫作)居然也投稿報社,聲援王任叔(巴人)。阿英兩次提出欲與王任叔去一茶樓小敘交換意見,但均被拒絕了,而《申報》大老闆馬某卻對王任叔很不滿,認為他破壞了《申報》不搞論爭的傳統,托人暗示讓他辭職。王任叔辭職後,索性與文友唐弢等人合辦起《魯迅風》周刊,以弘揚魯迅精神為己任,這家周刊在租界內外被人們廣為傳閱,產生過不小的影響。“孤島”時期迄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王任叔先後在上海和香港出版了《生活·思索與學習》、《橫眉集》、《邊鼓集》等四部雜文集,堪稱魯迅精神的主要傳承人之一。而且,最令滬上文化界人士震驚的是,接替阿英主編《譯報》“大家談”副刊,並也參與和王任叔打筆戰的錢納水在蘇德戰爭爆發後竟離職投靠汪偽,出任偽《中華日報》副主編,領取高薪,?顏事敵。這令阿英為之齒冷。同時他也對自己的觀念作了反省,意識到自己在《超越魯迅》一文中的一些提法固然有道理,但卻被別有用心之人所利用。阿英為此給王任叔寫信,坦承自己有考慮不周之處,希望保持團結,共同對敵。王任叔表示接受。
歷史冤案
1941年9月,王任叔從上海去新加坡,在南僑師範任教員,領導文化工作,同時協助胡愈之做些統戰事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侵占新加坡。王任叔去了印度尼西亞,在蘇門答臘參加人民反法西斯同盟,搞宣傳工作。他很快學會了印尼語,擔任地下抗日報紙《火炬報》的主筆。當時的印尼又稱荷屬東印度,印尼人民對荷蘭殖民軍和日軍同樣的憎恨。日軍當局曾懸賞通緝王任叔,發起過大檢舉運動。他兩次死裡逃生,在一印尼農民家隱蔽下來,以耕田種稻為生。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然而,在舉國歡騰的印尼,發生了一起血案。與王任叔一同從新加坡轉移到千島之國的郁達夫在1945年9月17日被日軍憲兵秘密殺害於丹絨革岱。這個案子後來竟將王任叔莫名其妙的牽扯進去,使他冤上加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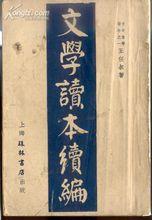 王任叔
王任叔郁達夫是“左聯”主將之一,為著名作家,著述甚多,擁有較大的影響。他流亡新加坡時任過《星島日報》主編,後又兼《華僑周報》主筆,還是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名氣很大,無人不知。流亡印尼後,郁達夫於1942年6月定居在蘇門答臘小鎮巴爺公務,化名趙廉,開了一家小釀酒廠,還與當地一土著女子結婚,育有一子一女。他的日語很好,一度擔任當地日軍憲兵隊的翻譯,其間又竭力為被捕的僑胞和印尼人開脫說情。郁達夫文人氣息很濃,為人自信曠達,自認為隱蔽得很好,也就疏忽了,沒想到日軍憲兵們已對他的真實身份產生懷疑,懷疑他就是郁達夫。日軍擔心他日後會寫文章揭露其在印尼犯下的野蠻罪行,遂將他秘密綁架殺害。王任叔這時已擔任印尼華僑聯合會的顧問。他又投身於印尼人民反抗荷蘭殖民者的鬥爭,號召華僑青年們參加蘇加諾領導的印尼光復軍。得知戰友郁達夫被害的訊息已是月余後。他很悲痛,撰文悼念,主張嚴懲兇手,但戰火又燃起,此案也就不了了之。荷蘭殖民軍於1946年初將王任叔逮捕,投入牢房。經印尼各界人士抗議、聲援,三個月後,荷蘭當局被迫釋放了王任叔。
1951年,新中國和印尼建交。蘇加諾總統很快向周總理提出希望能選派王任叔擔任中國駐印尼大使。中國政府同意了。王任叔在兩年任期內為保護華僑權益、增進兩國友誼做了不少工作。但外交工作畢竟不是他所長,他一再向周總理提出還是想搞文藝創作。1954年,王任叔回到北京,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和副總編輯。其後,他組織出版了《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和《古典文學十大作家集》等書。
他的理論著作《文學論稿》於1957年出版。王任叔愛憎分明,談話愛發議論,著文喜涉褒貶,容易得罪人。從1956年到1958年,他出於批判官僚主義作風,寫了《況鐘的筆》、《“魯迅風”話舊》等若干篇雜文,也對文藝創作中存在的條條框框多,以及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寫了若干篇短論,如《真人的世界》、《論人情》等,文筆犀利,廣為流傳。他沒想到的是,康生那時已在著手準備收拾他,報復他。
 王任叔
王任叔康生對王任叔當年竟然暗中調查“東方旅社”事件真相併寫過幾篇抨擊“內奸、小人”的雜文之舉一直耿耿在心。他可說是隱藏在黨內很深的巨奸,怪的是幾十年來他一直左右逢源一帆風順。康生在1933年7月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一年後,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仍追隨王明路線。王明垮台後,康生全力擁戴毛澤東,痛批他昨日還矢志效忠的王明。1937年,康生從蘇聯回延安,當上中央社會部和中央情報部部長。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中,康生一手製造了一連串冤案,大抓“內部敵人”,刑訊逼供,搞得延安人心惶惶,給共產黨的事業造成很大的損失。解放後,康生一度頗為失意,長期在杭州、青島等地休養,韜晦之餘,故作風雅,寄情於書畫印章,自取藝名“魯赤水”,儼然與大畫家齊白石分庭抗禮。1958年以後,康生重新活躍起來,以極左面目出現,興風作浪。他首先盯上的便是王任叔。1959年10月,康生在中宣部一次會議上點了王任叔的名,稱王的思想右傾,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對黨總是不滿,還別有用心地兩次指出王任叔與蔣介石是奉化同鄉,還在蔣的手下當過官,要查查其歷史,查清他是如何混進黨內的。在當時的特定形勢下,周楊等人也只有遵命行事,發動一些人對王任叔進行批判,又派人去奉化、上海等地內查外調,但根本查不出王任叔有任何政歷問題。1960年3月,王任叔被撤銷黨內的一切職務,一降三級,分到文學編輯所當主任。王任叔受此打擊迫害,從此沉默多了,心情抑鬱,他明白是禍躲不過,便加緊編著百萬字的《印度尼西亞史》,一心想多做些工作。1964年,康生又躍升為中央理論小組組長。王任叔的日子自然更不好過了。他沒料到,又一頂“大叛徒”黑帽子自天而降。
驚雷陣陣,神州蒙冤,滅頂之災終於來了。“文革”浩劫之初,王任叔就被首都文藝界造反派揪斗、抄家,受盡磨難。“禍不單行”,1968年2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校園內某造反組織聯合浙江大學“紅暴會”貼出一組聳人聽聞的大字報,誣稱王任叔是“出賣革命作家郁達夫的大叛徒”,說當年正是王任叔向日軍憲兵隊長告密才導致郁達夫的身份暴露而被處決。大字報中還說什麼當年“蘇加諾總統要求中國派王任叔出任駐印尼大使是出於對他的酬勞,因為蘇加諾為了趕走荷蘭殖民軍,曾通過王任叔與戰敗投降後仍滯留在印尼的日軍總司令後藤中將密談,謀求軍火與軍力的支持並取得成功”云云,分明都是捕風捉影的不實之詞。已調北京兼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張春橋回上海活動時,見到老婆李文靜收集來的此份大字報抄件,如獲至寶,因為這可以用來向康生討好,亦可以作為收拾他素所嫉恨的王任叔的致命武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他從山東流落到上海灘,賣文為生,至多算是三流文人而己。他曾因投靠同鄉、主持《新晚報》的中統文化大特務崔萬秋,籌劃組織“法蒂文學社”而受過王任叔的雜文的抨擊。張春橋明知國內已有幾本研究郁達夫的專著指出郁的被害與王任叔毫無關係。日本學者鈴木善清的《郁達夫傳》也指出郁達夫被害是憲兵隊查出了他的身份,不存在有人告密。但張春橋認為機會已來了。果然,康生讀了那份大字報抄件,欣喜若狂。在中央文革小組接見外省市造反派代表的會議上,他再次點了王任叔的名,重複了大字報抄件上的流言,煞有介事地誣稱王任叔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雙料大叛徒”。
不久後,王任叔被強行遣返浙江奉化家鄉。他已身患多種疾病,又得不到良好的醫治。而且,他忍受不了精神上的壓抑與摧殘,竟然被逼瘋了。1972年7月25日夜,王任叔死在寂靜的山村里,享年七十一歲。曾瘋狂地迫害過王任叔和許許多多忠良的巨奸康生在三年後也死了。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康生的罪行全部暴露,1980年,他的骨灰盒被清除出八寶山革命公墓。而在1979年,王任叔(巴人)的冤案就得到平反昭雪。八十年代初,他的代表作《巴人雜文選》、長篇小說《莽秀才造反記》及《印度尼西亞史》等相繼出版。這對已長眠於家鄉無名青山下的王任叔是最好的紀念。因為作家的生命是通過其有價值的作品而得以延續的。
1970年,王任叔被強行遣返原籍浙江奉化。有關機構在他的遣返書中,對他強行規定了三條:一、不準參加民眾大會,不準參加一切社會活動;二、不準隨意聽收音機;三、不準出縣外就醫。
這三條等於給王任叔定了性,他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一切對階級敵人進行專政的手段,都用在了他的身上。
王任叔剛回到老家時,在家鄉侄兒夢林的帶領下,他背著自己僅有的一床棉被,邁進了自己幼年居住過的那間空空蕩蕩的小木屋。他面對此景,十分感慨。50年前,他為了拯救那破爛不堪的社會,不怕殺頭、不怕坐牢,捨命投入政治鬥爭中,赤手空拳離開了他的小木屋。而到最後,他已年過古稀,卻仍然是赤手空拳、孤伶伶一人,被遣回這間小木屋。
但是,王任叔是位久經風雨的老人,在感慨之餘,在一種美好期望支撐下,他一時忘了怨言、忘了埋怨,也忘了不滿,他把自己那間幽暗的木屋打掃一下,將隨身帶回的被褥和一條毛毯,鋪在一張破舊的木床上。然後拿出他帶回來的一箱印尼歷史的手稿和資料,拍去旅途中積累的灰塵,規規矩矩地擺在了自己的木床前。就這樣,便開始了他艱難的晚年生活。
可以看出,這位百折不撓的老人、這位出版過500萬字著作的作家,不管自己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他一直堅持自己的寫作。永不停筆已經成了他終身的嗜好。當他整理乾淨自己的木屋後,便立即投入修改這部為之奮鬥了幾十年的印尼歷史一書。
通常人們都會說,意志堅強的人不會被困惑所壓倒。這句話,用在王任叔身上,也不為過。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剩下的時間不多的老人了。在王任叔一生到最後、僅剩下不多的日子裡,讓他繼續在小木屋裡忍受生活孤獨、政治壓抑的折磨,不是不可以,讓他以寫作寄託自己思想壓力和內心的怨氣,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擔心自己被無辜陷害的冤情得不到平反,就離開人世。
王任叔越想越苦惱,他苦惱到了極點,他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應。他十分絕望,多次寫信給北京要求回北京、要求去幹校、要求給他平反,卻沒有人理他。他想找人談談自己的苦悶,也沒有人聽。他日益焦慮,沒有多久,身體有些不支,老年性的心腦血管病不時地發作。他的精神開始全面崩潰,他的神經錯亂了,他瘋了。
王任叔瘋了以後,常常深夜跑到大街上吼叫,跑到四鄰去敲人家的門,甚至,在嚴寒的冬季,他常常不穿衣服在街上亂跑。
王任叔曾兩次被送到醫院都沒能治好他的病。到1972年,他的病情再次惡化,又不得不被送進醫院。不久,這位叱吒風雲的文人,孤寂地離開了人世……
個人作品
短篇小說
《監獄》(短篇小說集,又名《淒情》)1927,光華
《破屋》(短篇小說集)1928,上海生路社
《鄉長先生》(短篇小說集)1936,良友
《龍厄》(短篇小說集)1986,文化藝術
《阿貴流浪記》(長篇小說)1928,光華
《殉》(短篇小說集)1929,泰東
《在沒落中》(小說、散文集)1930,上海華東圖書公司
《捉鬼篇》(短篇小說集)1936,上海新城書局
《五祖廟》(小說、話劇集)1986,花城
《皮包和菸斗》(短篇小說集)1940,光明
《佳訊》(短篇小說集)1940,商務
《霧》(短篇小說集)與茅盾、巴金等合集,1943,上海地球出版社
《靈魂受傷者》(短篇小說集)與人合集,1941,上海三通書局
《巴人小說選》1983,人文
《印尼散記》(散文、小說集)1984,湖南人民
中篇小說
《證章》(中篇小說)1936,上海文學出版社
《一個東家的故事》(中篇小說)1942,上海未明社
《衝突》(中篇小說)1983,黑龍江人民
《任生及其周圍的一群》(中篇小說)1950,海燕
長篇小說
《死線上》(長篇小說)1928,上海金屋書店
《某夫人》(長篇小說)1935,武漢日報社
《女工秋菊》(長篇小說)1986,北方
《莽秀才造反記》(長篇小說,又名《土地》)1984,人文
雜文
《流沙》(小說、雜文集)1937,商務
《文藝短論》(雜文集)1939,上海珠林書店
《橫眉集》(雜文集)與孔另鏡等合集,1939,上海文匯有限公司
《邊鼓集》(雜文集)與唐韜等合集,1939,上海文匯有限公司
《論魯迅的雜文》(理論)1940,遠東
《生活、思索與學習》(雜文集)1940,香港高山書店
《邊風錄》(雜文集)19卑3,讀書
《學習與戰鬥》(雜文集)1946,上雜
《鄰人們》(雜文集)3950,三聯
《從蘇聯作品中看蘇維埃人》(理論)1955,中青
《遵命集》(雜文集)1957,北京
《點滴集》(雜文集)1982,浙江人民
文學論文
《窄門集》(文學評論集)1941,海燕
《常識以下》(文學論文集)1936,上海多樣社
《巴人文藝論文集》1984,人文
話劇
《兩代的愛》(話劇劇本)1941,海燕
《前夜》(話劇劇本)1940,海燕;又名《費娜小姐》,1949文學讀本(理論)1940,上海珠林書店;又名《文學初步》,1950,海燕;《文學論稿》,1954,新文藝
理論
《淡<青年近衛軍>》(理論)1959,文藝
《魯迅的小說》(理論)1956,新文藝
《文學讀本續編》(理論)1940,上海三通書局
回憶錄
《旅廣手記》(回憶錄)1981,人文
史學
《印度尼西亞史》
翻譯書目
《從社會見地看藝術》(理論)法國居龍著,1933,上海大江書鋪
《鐵》(中篇小說)日本岩騰雪夫著,1939,上海人民書店
《和平與麵包》(長篇小說)美國德萊塞著,1941,世界
《賽跑》 《爪哇現代史》
《荷屬東印度史》
《印度時代》
《女教師日記》
《彌爾塞的幻象》
《一個行路者死了》
《十二個犧牲者》
《耶奴朗斯之死》
後世紀念
在大堰村北面瓦屋山腳的巴人墓重修,墓碑上刻著老友胡愈之題的“王任叔巴人同志之墓”大字。 2001年10月19日紀念王任叔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召開。
![巴人[原人民出版社社長] 巴人[原人民出版社社長]](/img/f/8dd/nBnauM3X1QDO1IzNxATM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wEzL1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